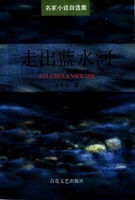任何孩子都有爹,他没有爹。美丽的娘因为美丽而世上一切东西都想做他的爹,娘终于在一次采菌子的时候于树林子贪睡了一会儿,娘就怀孕了。他的爹是树精?还是土精?这始终是个谜,待他生出来的时候娘就羞耻地死去了。
儿子长大,逐渐忘却了身世,与村中顽童在夏日的艳阳下捉迷藏,他的影子特别深重。他肯定不是一位年迈精衰的老头的野子,因为精疲力竭所留下的孽种是没有影子的,但他也不是哪一位年少者的种子,他的影子的浓黑为人罕见。这一切也还罢了,奇怪的是他的影子还有感觉。偶然一次,一个孩子踩住了他的影子,他立即尖锐地痛叫,并且不能行走,待那孩子松了脚,他一个踉跄就扑倒了。这一秘密被发觉之后,他从此就不自由了。他常常进门后随手关门时影子就夹在门缝,像夹住了尾巴。他在树林子里追捕野兔时,树杈和石头就挂住了影子。恶作剧的人便要在他不经意地行走时突然用木楔钉住他的影子,他就立即被钉住,如拴在了木桩上的一头驴,然后让他做什么就得做什么,大受其辱。
他想逃脱他的影子,逃不脱。他想挽袍子一样要把影子挽在腰间,挽不成。他开始诅咒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害怕一切光亮;阴雨连绵的白天和三十日的夜晚是他最欢心的时期,他在雨地里大呼小叫地奔跑,在漆黑的晚上整夜不睡。
但是,太阳和月亮在百分之九十的日子里照耀在天空,生性已经胆怯的儿子远避人群,整晌整晌寻找着那个火球,他要向他的娘诉苦。火球却一次未被他寻见。
有一次他听村人议论,说很远了的“文化革命”时期,有一群人从城市里逃到太白山的黑松峡去避难。不知怎么,他总觉得他应该到那里去,那里似乎有他的爹,娘的灵魂的那个火球也似乎是从那里常来到村中的。他独自往黑松峡去,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终于在一片黑松林子里发现了一些倒坍的茅舍和灶台,一块巨石上斑驳不清地写着“逃□村□”字样。但没有人。他住下来,捡起茅舍中已经红锈了的斧子和长锯砍倒了松树伐解成木板要背负到山下去换取米面油盐。当他伐解开了木板,木板中的纹路却清晰的是一个完整的人形。他吃惊地伐解了十多棵树,每一棵树里都有一个人形纹。他明白了黑松峡里为什么最后还是没有人的原因,骇怕使他把斧子和长锯一起丢进了深不见底的峡谷去。
村人都知道他出走了,良心使他们忏悔了对这个丑陋人的虐待,他们没有侵占和拆毁他曾居住的那三间房子,企望着他某一日回来,但他没有回来。只是空荡的房子里,屋梁上有了一只很大的蝙蝠,白日里便双爪倒挂,黑而大的双翼包裹了头和身,如上吊的丑鬼,晚上就黑电一般地在空中飞动。
少女
这一个冬季,太白山还不到下雪的时候就下雪。下得很厚,又不肯消融,见风起舞濛濛,只好泼上水冻一夜,结一层一层冰块,用锨铲到阴沟去。年关将近,还不曾停止。有人蓦地发现雪不是雪,没有凌花,圆的方的不成规则,如脂溢型人的头屑,或者更像是牛皮癣患者的脱皮。人们就惊慌了:莫非是天在斑驳脱落?
天确实在斑驳脱落。
脱过了年关,在二月里还脱,在四月里还脱。
害眼疾已失明了一目的娘在催促着儿子,没日子了,快去山顶寨求婚吧。后生把孝顺留下,背着娘的叮咛,直往山顶寨去。
三年前,后生相中了山顶寨的一个少女,在山屹崂里两人亲了口。当少女感觉到一个木橛硬硬地顶住她的小腹时,一指头弹下去,骂道:“没道德!”戴顶针的手指有力,木橛遂蔫下去,原是没长骨的东西。后生却琢磨了那三个字,便正经去少女家求婚。但少女的娘掩了门,骂他是野种,你娘是独目难道也要遗传给我个单眼外孙?甚至还骂出一句不共戴天。
现在,天要斑驳脱落了,还共什么天呢?
勇敢的后生来到寨上。正是晚上,一群鸡皮鹤发的年迈人在看着天上的星月叹息,说天上的月亮比先前亮得多了,也大得多了。原来月亮是天的一个洞窟,一夜比一夜有了更多的星星,这是已经薄得不能再薄的天裂出的孔隙了。后生知道年迈人已无所谓,他没有时间参与这一场叹息,只是去找他的少女。但寨子里没有一个年轻人,打问之后方得知他们差不多于一个晚上都结婚了,这个还算美好的夜里,不愿辜负了时光,在寨后的树林子里取乐。他一阵心灰,却并未丧气,终于找到了少女。少女披散着长发,长发上是一个腊梅编成的花环,妖妖地在树林子里骑着一头毛驴,一边唱着情歌,一边焦急地朝林外探询。他们碰在对面的时候,都为着对方的俊俏而吃惊了。
他说,你是结婚了吗?
她说当然是结婚了。
他没了力气地喃喃,那么,你是在等着你的丈夫了。
是等我的丈夫,她说,也是等所有爱过我的人。说罢了,又诡秘地笑,同时后生听到了一句“我知道你也会来的”。仅这一句话,后生勃发了狼一样的无畏,他们在毛驴的上下长长久久地接吻了。
后生高兴的是少女毫无反抗,当看见她首先将外衣脱下铺在地上,还说了一句“能长在手心多方便,一握手就是了”,他倒微微有一些吃惊。世上最急不可待的莫过于此了,但她却一定要他使用她带来的避孕套,他不愿意,他希望不合法的妻子能为他生出一个儿子来。她严肃异常,谁还生儿子,让自己的儿子降生下来受罪吗?这么争执着并没有结果。其实一切都发生了,他们几乎是昏过去几次,几次又苏醒过来。在少女的头脑里,满是一圈一圈的光环,她在光环中出入,喝到了新启的一罐陈年老醋,吃到了上好的卤猪肉,穿着一双宽鞋走过草地。她说:我的花骨朵儿绽了,我不亏做一场人人人了了了……声音由急转缓,高而滑低,遂化作颤音呻吟不已。
从此后生被安置在树林里,少女天天送来吃的,吃饱了他的肚子,也吃饱了他的眼睛,吃饱了他的心。不免要想起那个古老的故事,说是一个男人被劫进女人的宫中,享受着王子一样的待遇,最后却成为一堆药渣。现在的后生没有药渣的恐惧,倒做了一回王子。他在树林子里跳跃呼叫,如一头麝,为着自身的美丽和香气而兴奋。他甚至不再忧天,倒感念起天斑驳脱落的好处,竟也大大咧咧地走到寨子里,不害怕了少女的娘,还企望见一见少女的那一位小丈夫。寨子里的人并不恨他,并且全村人变得平和亲热,不再殴斗和吵架,忏悔着以前的残酷是因为制造了钱币。钱币就弃之如粪土了。善心的发现,将一切又都看做有了灵性,不再伐木,不再捕兽,连一棵草也不砍伤。
天继续斑驳脱落,肤片一样的雪虽然已经不大了,但终还是在下。
少女日日来幽会,换穿着所有的新衣。在越来越大而清的月亮下,他们或身子硬如木桩,或软若面条,全然淫浸于美妙的境界。他们原本不会作诗,此时却满腹诗意,每一次行乐都捡一篷槲叶丛中,或是一株桦下,风前有鸟叫,径边乱花迷。后生在施爱中,看见雪似的天之肤片落在少女的长发上,花花白白地抖不掉,心中有一股冲动,想写些什么,便用她的发卡在桦皮上写道:
谁在殷勤贺梨花
昨也在撒
今也在撒
他还要再写下去,但已经困倦之极没一点力气,他软软地睡着了。少女小憩后首先醒过来,她没有戳醒后生,她喜欢男人这时候的憨相,回头却瞧见了桦皮上的诗句,竟也用发卡在下面写道:
假作真来真作假
认了梨花
又恨梨花
末了便高望清月,思想哪一日天不复在、地壳变化,这有诗的桦皮成为化石,而要被后世的什么什么动物视为文物了。
不知过了多久,后生听见深沉的叹息而醒了,身边的少女,亲吻时粘上的那节草叶还粘在额上,却已泪流满面,遂拥少女在怀,却寻不出一句可安慰的言语。
咱们数数那星星吧。后生寻着轻松的事要博得少女的欢心。这夜里只有星月,他不说明那是天斑驳后的孔隙。
两个人就数起来,每一次和每一次的数目不同,似乎越数越多,他们怨恨起自己的算术成绩了。
后生的想像力好,又说起他和老娘居住的房子,如何在午时激射有许多光柱,而每个光柱都活活地动。少女却立即想到了房顶的窟窿,没有笑起来,却沉沉地说:你要练缩身法的。
是的,他的一切都是她所爱的,惟独怨恨的是他的个子,他的个子太高了。后生并不解她的意思,自作了聪明,说不是有个成语,天塌下来高个子撑吗?她狼一样凶恶地撕裂了他的嘴,咆哮着说不许再胡说八道,因为寨子里人都习练这种功法了。
后生自此练功,个子似乎萎缩下去。而不伐的树木长得十分茂盛,不捕的野兽时常来咬死和吃掉家畜家禽,不砍伤的荒草已锈满了长庄稼的田地。老鼠多得无数,他一睡着就要啃他的脚丫子;有一次帽子放在那里三天,取时里面就有了一窝新生的崽仔。后生有些愤恨,它们在这个时候,竟如此贪婪!这么想着,又陡然添一层悲哀,或许将来没有了天的世界上,主宰者就是这些东西吧?
一日,少女再一次来到树林子,他将他的想法告诉了少女。少女没有说话,只是领他进寨子里去。寨子里再没有一个人,巷道中、墙根下到处是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他疑疑惑惑,少女却疯了一般地纵笑,一边笑着走一边剥脱一件件衣服,后来就赤条条一丝不挂了,爬到一座碾盘上的木板上,呼叫着他,央求着他。等后生也爬上去了,木板悠晃不已,如水石滑舟,如千秋送荡,他终于看清碾盘上铺着一层豌豆,原是寨中人奇妙的享乐用具。他们极快进入了境界,忘物又忘我,直弄翻了木板,两个人滚落到碾盘下的一堆乱石上。乱石堆的高低横侧恰正好适合了各种杂技,他们感到是那样的和谐,动作优美。他说,寨中的人呢,难道只有咱们两个人在快活?她说他们就在身下,在快活中都变成石头了。后生这才发现石头果然是双双接连在一起的。他想站起来细看,少女却并不让停歇,并叮咛着默默运作缩身的功法。后生全然明白了,于是加紧着力气,希望在极度的幸福里昏迷而变成石头,两个在所有石头中最小的连接最紧的石头。
天仍在斑驳脱落。斑驳脱落就斑驳脱落吧。
后生和少女已经变化为石头了,但兴奋的余热一时不能冷却。嘴是没有了,不能说话,耳朵仍活着并灵敏。他们在空阔的安静的山上听到了狼嚎和虎啸。听见了天斑驳脱落下来的肤片滴沥,突然又听到了两个人的吵架声。少女终于听出来了,那不是人声,是鬼语。一个鬼是早年死去的老村长,一个鬼是早年死去的副村长。他们两位领导活着的时候有路线之争,死了偏偏一个埋在村路的左边,一个埋在村路的右边,两个鬼就可以坐在各自的坟头上吵,吵得庄严而有趣。
少男
一个人出去采药再没有回来,以为已经滚坡横死,他却在一个晚上给村里人托梦:他是在鸡肠沟的瀑布崖上作仙了,让村里的人忘记他的好处,也让他的家妻忘记曾嫌弃过她的坏处。第二天,村人都在议论这个梦,那人的家妻却忘不了丈夫,哭天嚎地,央求人们帮她去找回自己的男人。
村里的人就一起去鸡肠沟。鸡肠沟乱石崩空,荆棘纵横,他们以前从未去过,果然在一处看见了那个崖。崖很高,仰头未看到其顶,长满了古木,古木上又缠绕了青藤。此时正是黄昏,夕阳映照,所有的男人都看见了崖头有一道瀑布流下来,很白,又很宽,扯得薄薄的如挑开的一面纱,风吹便飘。从那古木青藤的缝隙里看进去,却是许多白艳的东西,似乎是一群光着身子的人在那里洗澡,或者是从水中才沐浴出来坐卧在那里歇息。如果是人,什么人能有这么丰腴、这么白艳呢?托梦人说他是成了仙,仙境里没有这么多丰腴、白艳何以称做仙境呢?天下的瀑布能有这般白这般柔?于是,男人们的神色都变化,一时沉醉于非非之想中,样子发憨发痴。男人的变化,女人们觉察到了,但并未明白他们是怎么啦,因为她们未看懂隐在古木中的东西。但她们体会最深的是自己只有一个丈夫,当男人们一步步往崖根下走时,她们各自拉住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个。
一位勇敢的少男坚持往前走,他是新婚不久的郎君。他往前走,新娘往后拖,郎君的力气毕竟大,倒将新娘反拖着越来越走近崖根,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远远站定的男女看见他们在崖根下的那块青石板上,突然衣服飘动起来,双脚开始离地,升浮如两片树叶一样到了空中,一尺高,三尺高,差不多八九尺高了,但他们却又定止了一刻,慢慢落下来。落下来也不容新娘挣扎,再一尺高,三尺高升浮空中,同样在七八尺的高度上定止片刻再落下来。这次新娘就一手抓住了石板后的一株树干,一手死死抓住丈夫的胳膊,大声呼救;帮帮我吧,难道你们看着我要成为寡妇吗?村人同情起这新婚的少妇,她虽然并不漂亮,但也并不丑到托梦人的那个家妻,年纪这么轻,真是不忍让她做寡。并且,男人们都是看见了古木内的景象,那是人生最美好的仙境,而自己的妻子已死死阻止了自己去享乐,那么,就不能允许和自己一样的这个男人单独一个去,况且他才是新婚,这个不知足的家伙!于是乎,所有的男人在女人的要求下一人拉一人排出长队拖那崖根的夫妇,将那郎君拉过来了。新娘开始咒骂他,用指甲抓破了他的脸。他们在劝解之中,真下了狠劲在郎君的身上偷击一拳或暗拧一把。
少年郎君垂头丧气地回来,从此不爱自己的新妇。每日劳动回来,脱光了衣服躺在床上抽烟,吆喝新妇端吃端喝,故意将自己的那根肉弄得勃起,却偏不赐舍。新妇特别注意起化妆打扮,但白粉遮不住脸黑,浑身枯瘦并不能白艳。有时主动上来与他玩耍,但只是灰不沓沓,偶尔干起来,怀着仇恨,报复般地野蛮击撞,要不也一定要吹灭了灯,满脑子里是那丰腴白艳的想像。
这少男实在活得受罪了。
他试图独自去一次鸡肠沟,但每次皆告失败。村中所有的女人都在监视着自己的男人,所有的男人也就在监视着其他的男人。这少男的行动每次刚要实施就被一些男人发觉,立即通报了新娘。新娘就越发仇恨那个已经作仙的男人,她联合了村中的女人,用灰在村四周撒一道灰线,不让那作仙男人的灵魂到村中游荡;各自将七彩绳儿系在自己丈夫的脖子上,以防作仙男人托梦诱惑。而且,她们仇恨仙人的遗孀,唾她,咒她,甚至唆使自己的丈夫去强奸她,使她成为村中男人的公共尿壶,而让那作仙男人的灵魂蒙遭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