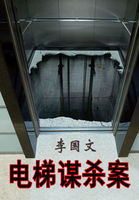这人说这就好了肯定掉到池边了我帮你去找。
两人跑到池边把每一块石头都翻了,每一片草都拔了,没有头。掉到池里是不可能的,因为水鸟不允许有杂物落进去,要掉在池里水鸟会衔出来扔到岸上的。两人又往来路上往回找,仍是没有头。回到厢房那人又哭,这人瞧见那人哭,也觉伤心,后来就也哭起来。哭着哭着,那人却不哭了,反倒笑了一声,还劝慰这人也不要哭。
这人说你没头了你还笑什么呀?
那人说你这么帮我让我感激不尽我还从来未遇过你这好人我怎能也让你哭我没头我也不找了我不要我的头了!
那人说罢,头却突然长在了肩膀上。
丈夫
过了馒头疙瘩峁,漫走七里坪,然后是两岔沟口穿越黑松林,丈夫挑着货郎担儿走了。走了,给妇人留一身好力气,每日便消耗在砍柴、揽羊,吆牛耕耘挂在坡上的片田上。
货担儿装满着针头线脑,胭脂头油,颤悠,颤悠,颤颤悠悠;一走十天,一走一月。转回来了,天就起浓雾,浓得化不开。夜里不点灯,宽阔的土炕上,短小精悍的丈夫在她身上做杂技,像个小猴猴。她求他不要再出去,日子已经滋润,她受不得黑着的夜,她听见猪圈里猪在饿得吭吭。他说也让我守一头猪吗?丈夫便又出门走。丈夫一走,天就放晴,炸着白太阳。
又是一次丈夫回来,浓雾弥漫了天地,三步外什么也看不见,呼吸喉咙里发呛。雾直罩了七天七夜,丈夫出门上路了,雾倏忽散去,妇人第三天里突然头发乌黑起来,而且十分软,十分长,像泻出黑色瀑布。她每日早上只得站在高凳子上来梳理。因为梳理常常耽误了时光,等赶牛到了山上,太阳也快旋到中天了。她用剪刀把长发剪下,第二天却又长起来。扎条辫子垂到背后吧,林中采菌子又被树杈缠挂个不休。她只得从后领装在衣服里,再系在裤带上,恨她长了尾巴。
丈夫回来了,补充了货品又出门上路。妇人觉得越来越吃得少,以为害了病。却并不觉哪儿疼,而腰一天天细起来,细如蜂腰。腰一细胸部也前鼓,屁股也后撅,走路直打晃,已经不能从山上背负一百四十斤的柴捆了。天哪,我还能生养出娃娃吗?
丈夫在九月份又出动了。妇人的脸开始脱皮。一层一层脱。照镜子,当然没有了雀斑,白如粉团,却见太阳就疼。眼见着地里的荒草锈了庄稼,但她一去太阳光下锄薅,脸便疼,针扎地疼。
丈夫一次次回来,一次次又出去,每去一趟,妇人的身子就要出现一次奇变。她的腿开始修长。她的牙齿小白如米。脖颈滚圆。肩头斜削。末了,一双脚迅速缩小,旧鞋成了船儿似的无法再穿,无论如何不能在山坡上跑来跑去地劳作了。妇人变得什么也干不成,她痛苦得在家里哭,哭自己是个废人了,要成为丈夫的拖累了,他原本不亲热我,往后又会怎样嫌弃呢?
妇人终在一天上吊自尽。
丈夫回来了,照例天生大雾。雾涌满了门道,妇人美丽绝伦地立于门框中。丈夫跑近去,雾遂淡化,看见了洞开的门框里妇人双脚悬地,一条绳索拴在框梁。丈夫嚎啕大叫,恨自己生无艳福,潸然泪下。泪下流湿了脸面,同时衣服也全然湿淋。将衣服脱去,前心后背竟露出十三个眼睛。
公公
夏天里,长得好稀的一个女人嫁给了采药翁的儿子。采药翁住在太白山南峰与北峰的夹沟里,环境优美,屋后有疏竹扶摇,门前涧水潺潺。傍晚霞光奇艳,女人喜欢独自下水沐浴,儿子在涧边瞧着一副耸奶和浑圆屁股唱歌,老翁于门坎上听着歌声,悠悠抽烟。八月份的第七个天,儿子去主峰上采药,炸雷打响,电火一疙瘩一疙瘩落下来撵。儿子躲进三块巨石下,火疙瘩在石头上击,儿子就压死在石头下。女人孝顺,不忍心撇下公公,好歹伺候公公过。
公公是个豁嘴,但除了豁嘴儿公公再没有缺点。
夜里掩堂门安睡。公公在东间卧房,女人在西间卧房,惟一的尿桶放在中间厅地。公公解溲了,咚咚乐律如屋檐吊水,女人在这边就醒过来。后来女人去解溲,当当乐律如渊中泉鸣,公公在那边声声入耳。
日子过得很寡,也很幽静。
傍晚又是霞光奇艳,女人照例去涧溪沐浴。涧边上没有唱歌人,公公呆呆在门坎上抽烟叶,抽得满口苦。黎明里,公公去涧中提水,水在他腿上痒痒地动,看见了数尾的白条子鱼。做了钓竿拉出一尾欲拿回去熬了汤让女人喝,却又放进水。公公似乎懂得了水为什么这么活,女人又为什么爱到水里去。
公公告诉女子他要到儿子采过药的主峰上去采药,一去没有回来。女人天天盼公公回来,天天去涧溪里沐浴。女人在水中游,鱼也在水中游,便发现了一条娃娃鱼。娃娃鱼挺大,真像一个人,但女人并不觉得害怕。她抱着鱼嬉戏,手脚和鱼尾打溅水花,后来人和鱼全累了,静静地仰浮水面,月光照着他们的白肚皮子。
女人等着公公回来告诉他涧溪中有了这条奇怪的娃娃鱼,但公公没有回来。十个月后,女人突然怀孕,生下一个女孩来。孩子什么都齐全,而嘴是豁唇。女人吓慌了,百思不解,她并没有交接任何男人,却怎么生下孩子来?且孩子又是个豁嘴?!女人在尿桶里溺死孩子,埋在了屋后土坡。
又十个月,女人又生下一个豁嘴孩子。女人又在屋后的土坡埋了。再过了三个十月,屋后的土坡埋葬了三个孩子。三个孩子都是豁嘴。
公公永远不会回来了吗?或许公公明日一早就回来。
女人已经极度地虚弱了,又一次将孩子埋在屋后土坡时,被散居于沟岔中的山民瞧见。他们剥光了她的衣服,用鞋底扇她的脸和她的下体。然后四处寻觅采药翁,终在溪边的泥沙中发现采药翁的药镢,哀叹他一定是受不了这女人的不贞而自溺。山民便把女人背负小石磨坠入涧溪。水碧清,女人坠下去,就游来了许多鱼,山民们惊骇着有一条极大的似人非人的鱼。
自此,娃娃鱼为太白山一宝,归于重点保护。
村祖
山北矻子坪的村里,一老翁高寿八十九岁,村人皆呼做爷。爷鸡皮鹤发,记不清近事能记清远事,爱吃硬的又咬不动硬的,一心欲尿得远却常常就淋在鞋上。因为年事高迈,村人尊敬,因为受敬,则敬而远之,爷活得寂寞无聊,兀自将惟独的一颗门牙包镶的金质牙壳取下来,装上去,又复取下。
过罢十年,算起来爷是九十九岁。一茬人已老而死去,活上来的又一茬人却见爷头发由白转灰,除那颗门牙外又有槽牙。再过罢十年,一茬人再皆死去。另一茬活上来的人见爷头发由灰为黑,门牙齐整。如果不是镶有金牙,谁也不认为他是那个爷的。不能算做爷,村人即呼他伯。又过十年,又是一茬人见他脸色红润,叫他是叔。又又十年,又又又十年,八十年后,他同一帮顽童在村中爬高下低,闹得鸡犬不宁。一个秋天,太白山下阴雨,直下了三个月。一切无所事事,孩子们便在一起赌钱。正赌着,村口有人喊:公家抓赌来了!孩子们赌得真,没有了耳朵,只有凸出的眼泡。他已经输尽了,同伴欲开除他的赌资,他指着口里的那枚金牙,这不顶钱吗?执意再赌。抓赌人到了身边,孩子们才发觉,一哄散去。他又输给一顽童,顽童要金牙。他赖着不给,再赌一次,三求二赢。顽童说没牌了怎个赌?划拳赌。抓赌人在后边追,他们在前边跑,口里叫着拳数。抓赌人追不上不追了,他却还是又输一次。输了仍不给金牙。两人就绕着一座房子兜圈子。忽听房子里有妇人在呻吟,有老妪将一个男人推出门,说生娃不疼啥时疼。他忽地蹲上那家后窗台,不见了。追他的顽童撵过墙角不见人。瞧瞧树,树上卧只鸟儿。掀掀碌碡,碌碡下一丛黄芽儿草。猛地转过身,身后也没有。顽童呆若木鸡。恰屋里又扑地有响,产妇呻吟声止,老妪喊生下了生下了。这顽童骂过一句,烦恼忘却,便爬后窗去瞧稀奇。土炕上血水汪汪,浸一个婴儿,那婴儿却不哭。老妪说怎个不哭,用针扎人中,仍不哭。用手捏嘴,嘴张开了,掉出一枚金牙壳,哭声也哇地出来了。
多少年后。
这个村一代一代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村祖还在活着,却谁也不认识。自此他们没有了辈分。人人相见,各生畏惧,真说不得面前的这位就是。
领导
县上领导到太白山检查工作,乡政府筹办了土特山货,大包小包的堆放在办公室,预备领导走时表示一点山区人民的心意。不料竟失盗。紧张查寻,终于捉到小偷,欲让派出所拘留时,小偷请求立功赎罪,问如何立功,说是身怀特异功能,能数十米外知道屋中人的活动,若能饶恕,往后可协助派出所缉拿别的罪犯。领导生了兴趣,同意明日一早来验证。
明日,领导收了礼品,马上坐车要返回了,记起那个小偷,提来问道:“你既然有特异功能,我问你,我昨夜一更天做什么事?”小偷说:“回答领导,昨夜一更天领导没有休息,还是抓紧时间和妇联主任谈工作。领导是坐在床上的,后来不小心掉到床下。”领导说:“胡说!我一个大人,怎么会掉到床下?”小偷说:“那我怎么听见妇联主任说:‘上来,上来。’这不是领导掉到床下了吗?”领导想想,点了头,说:“那么,二更天我干什么了?”小偷说:“二更天领导吃夜宵,吃的是螃蟹。”领导说:“胡说,我从不吃夜宵,我的肠胃不好,吃了睡不着觉的。”小偷说:“那我听见领导说:‘掰腿。’这不是吃螃蟹是干什么呢?”领导想了想,嗯了一声,说:“那三更天我干什么了?”小偷说:“三更天是领导为了进一步了解山区群众生活状况,特意请来了妇联主任的母亲问情况。”领导说:“真是胡说!白天我了解情况了,晚上压根没请妇联主任的母亲。”小偷说:“我听见妇联主任叫了一声‘哎哟妈呀’!”领导不言语了,问:“那四更天呢?”小偷说:“四更天领导谈工作谈累了,用凉水洗脸,清醒头脑哩!”领导说:“又在胡说了!根本未洗脸!”小偷说:“如果没洗脸,领导怎么说:‘你擦了,给我擦一下。’”领导若有所思地咕嘟了数语,说:“五更天,五更天干什么?”小偷说:“五更天工作谈完,领导真会调剂生活,与妇联主任下起棋了。”领导说:“胡说胡说!什么时候了还下棋?”小偷说:“我明明听见领导说:‘再来一回,再来一回。’这不是下棋吗?”领导嘎地笑了起来,说:“还行,有特异功能,我让派出所免你的罪了!”
自此,小偷被太白山派出所器重,据说协助参与了几起破案工作。
饮者
太白山北侧有一姓夜人家,娶妻欢眉光眼,智力却钝,不善操持,家境便日渐消乏,夜氏就托人说情租借了桠树坳一块门面开设饭馆。因要生意顺通,自然不敢怠慢地方,常邀乡政府的人来用膳。
中秋之夜,月出圆满,早早掩了店门,特摆酒菜与乡长在堂中坐喝,两人都海量,妻就不住地筛酒炒菜。吃过一更,乡长脖脸通红,说:“你也是喝家!让我老婆替我几盅。”便趴在桌上,手蘸酒画一圆圈。圆圈中出来一个妇人,肥壮短脖,声明用大杯不用小盅,随之一杯,仰脖灌下。夜氏吃了一惊,也用大杯。连喝五杯,妇人醉眼矇眬,摆手说:“我喝不过你呢,你却不是我儿子的对手!”遂也蘸酒画圈,出来一个青年,英气勃勃,言称闷酒不喝,吆喝划拳。夜氏甚精拳术,划毕常拳,又划广东拳,复又划日本拳,老头拳。青年善饮,但败于拳路,喝得脸色煞白,说:“让你瞧瞧我妻弟的拳吧!”又画圈出来一少年。少年腿手奇瘦,肚腹便便,形若蜘蛛,说:“让我先吃些菜垫底。”低头一阵狼吞虎咽。夜氏妻就又一番烧火炒菜。两人对过一杯,相互要检查杯底里是否干净,规定滴一点罚三杯,一来二往竟将桌上三四瓶酒喝完。又启一罐,少年举杯过来要碰,酒杯哗啦落地,已立站不稳,说句:“我服你了,你敢与我小姨子对杯吗?”酒圈刚画毕,人就呕吐。夜氏也早头重脚轻,待要去扶少年,却见一个窈窕少女已坐在了桌边,笑吟吟地说:“你不陪我吗?”夜氏说:“几杯淡酒,怎能不陪的,姑娘你喝好!”少女说:“咱不划拳,联连成语定输赢。”夜氏应允,无奈肚中文墨欠缺,少女说“恭喜发财”,夜氏说“财源茂盛”,少女说“盛情难却”,夜氏却连不上来,输酒便喝了。如是一个盹时,输喝十杯,醉倒桌底,说:“失礼了,失礼了。”不省人事。少女笑道:“我喝酒还没有人能陪到底的。”兀自入了酒圈不见。又,少年入了青年酒圈不见,青年入了妇人酒圈不见,妇人也入了乡长的酒圈不见。乡长笑眯眯对夜氏妻说:“在咱这儿开饭馆,没酒量不行哩!”邀其再喝。
天明,夜氏酒醒,见满屋酒瓶,倏忽记得昨夜事,忙呼叫其妻。妻未回应,却见一人跳窗而走,似乎是乡长的身影。翻坐起视,妻竟沉醉床上,被褥狼藉,不觉心中森然,掀开被子看时,果然床上留有一脱壳之物,尖硬如牛犄角。便打醒妻子,令其速去屋后阴沟里小解。妻去一会儿回来,喜悦说:“尿出来了,尿出来了,果然是个小乡长!”夜氏去阴沟查看,阴沟的一块松沙被尿水冲开一坑,正有一只螃蟹往外爬,行走横侧着身子,口吐泡沫,似乎还有酒气。夜氏一石头将螃蟹砸烂,用沙埋了叮咛妻子不能外漏,遂返回店去,一身轻快。
儿子
山北侧的沟里磨了四十年的寡,熬到独儿长大了读书了干事了做上某县的一个主任了,跟儿享享福去啊,城市中呆半个月却害红眼,口舌生疮,大便干燥,还是回居太白山。太白山的空气可以向满世界出售,一日绿林里出一个太阳,太阳多新鲜。
孝顺的主任叹一口气,送回来一只波斯猫为娘解闷。
猫长至数月,本事蛮大,或妖媚如狐或暴戾如虎,但不捉鼠。大白日里要叫春,声声殷切,沟中人家的鸡和狗就趋来,乱哄哄集在门口,猫却懒坐篱笆前作洗脸状,遂以后爪直竖,蹒跚类似人样,倏忽发尖利之声。鸡狗则狂躁安静,一派驯服,久而悄然退散。娘初觉有趣,而以后鸡狗常来便生厌烦,知道这全因了猫叫春的缘故,遂将猫挑阉作兽中寡。但鸡狗依然隔三间五日必来,甚至来了,狗要叨一根木棒鸡要生一颗热蛋。木棒枯黑,分明是从哪儿的篱笆上弄的,鸡常常小步跑来将鸡蛋生在路上,是特意要来贡献的。娘好生奇怪。木棒拿去烧了饭,蛋却不敢吃,提着去沟中人家问谁家鸡不在家中生蛋,竟所有的都荒窝,遂计算日期退还蛋数。娘博得贤惠人缘,沟中人家无事要来聊天,每有妇人抱了小儿,小儿拉屎,猫则立即去舔屁股。狗舔屎,猫怎的也舔屎?娘顿生恶心,不让它再跳上案板去吃剩饭。到后来,有大人去茅房,猫竟也去舔,被一巴掌打落进茅坑。这是什么猫呀,该猫干的不干,尽干不该猫干的,避!娘夜里把猫关在门外,猫哀叫了一夜,娘不理睬,狠心嫌弃。猫到第三日就发疯,狂叫不已,且咬断屋檐下吊笼绳,一笼豆腐坠落灰地。将院中的花草捣碎。在厨房的水瓮中撒尿。娘终于大怒,把猫用裤带勒死。
丑人
儿子常常发呆,寻找着那个火球。
娘是凶死的,村人看见她站在凳子上,将脑袋套进了绳圈里,凳子就蹬翻了。那绳圈套的正是地方,舌头没有伸出来:灵魂遂出了窍,是一个火球,旋转着进了树林子。后来在很长的日子里,火球就出现,或在谁家的院墙头,或在巷口的碾盘上,或在树梢上,坐着像一只鸟。人们都在说,娘是挂牵着她的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