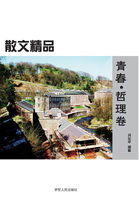有人命中注定要过平庸的生活,默默无闻,因为他们经历了痛苦或不幸;有的人却故意这样做,那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幸福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卡尔维诺《烟云》
我疲态摆出、浑浑噩噩地趔趄着步子,感到浑身不自在。我的心情糟透了,我还在为答应“哥哥”拿到那笔钱而深怀愧疚。不过,我已经没有兴趣考虑那些来自过去的馈赠,因为疲倦,我拖沓着双腿,希望就这样躺在路边。
很快我就熟悉了周围的老环境:寒夜的路灯在我的头顶忽闪着,让我喉咙干涩的秋季气候,因为无人关注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的几只飞虫……我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房东太太的家门。进门后,换了双拖鞋,然后,慢慢吞吞的将行李箱靠在鞋柜上。我决定明天早上再洗澡。那是因为,我已经无法克制自己的睡眠了!我甚至没有脱下大衣就倒在了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只过了1个小时,我就被一声巨响惊醒,随后,一阵噼里啪啦,就像跟着摔碎的瓷罐子撒落一地的弹珠。我警觉地从沙发上坐了起来,由于别扭的睡姿致使我的脖颈僵直疼痛。几秒钟后,我开始用目光搜寻噼啪声音的来源。我敢肯定它是从厨房传来的,就在我的潜意识里浮出这个粗略判断的同时,厨房里飘来了黑色的浓烟。基于这个明显的情形,我的头脑里猛地弹出了一个词汇:火灾。来不及恐惧,也来不及为我的正确判断感到庆幸,烈焰已经先一步发现了我所在的客厅,它像一个无孔不入的盗贼从厨房破门而入。我急急忙忙在客厅的墙壁上搜寻警报按钮。又突然记起它被安在了厨房的侧壁上,而原来搁在客厅桌上的电话机也不翼而飞。我亲爱的朋友,这情形糟透了:客厅的腐朽的木地板干燥老迈,就像一片干枯的树叶,一点就着,火焰又像爬梯子一样,顺着屋里插满的菊花枝登梁上瓦,据我几米远的旧报纸堆也像事先被涂好焦油一样,烧成一团。
我随手扯起了该在沙发上的条纹毯子,披在了身上。正当我恐惧而慌张地大喊着房东太太名字的时候,厨房隔墙的那边又迸发出了一声巨响,很明显这是一声巨大的爆破,我及时地趴下才避免被飞向四面八方的残骸击中。我的上帝,当我慢慢抬起头时,那面墙已经行将坍塌,墙壁被炸开了一个足有窗户那么大的豁口。透过豁口,我看到缠绕在一起的电线像爆米花机一样炸出兴奋的火花,它们伴随着电光的刺啦响声,激烈地飞溅在火堆中。随之,更浓的烟雾涌入了客厅。天顶开始剥落碎末。我知道,如果不尽快撞门而出,一切都将轰塌、付之一炬。
于是,我以最迅捷的速度朝楼梯的方向扑去,手脚并用的我放开了音量大声唤着房东太太。就在这时,这女人,才慢吞吞地出现在了二楼楼梯的拐角。但是,好像一个瞬间就能够进入角色的演员,她几乎是从楼梯口滚了下来。她哭叫着:“上帝啊,天啊、瞧,我的家啊……”我不顾一切地拽着她往门口撞去。这时,一条水龙从火焰的封锁中穿墙而入,火同水随即玩起了捉迷藏。这一幕就像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一样,我们踩着沾湿、焦化的地板撞开门,将火焰和恐惧撇在身后,当我们冲破浓烟的封锁时,我突然想到了贝壳,我的旅行箱,它还靠在鞋柜的旁边,里面装着我的手机、工作记录以及我在底特律收获的一切。正当我打算转身取出包裹的时候,礼炮般的响声从我身后传来,这声音造成地面的颤动,甚至引发了一场小区域的轻微的地震。随即,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物坠入了石灰堆,从而掀起了一片白色的烟雾一样,尘埃、余烬、燃烧的木屑、闪烁的火星拼劲全力向空中逾越、飞舞。我的眼睛再度闭上了,而这一次,我试图虚掩着眼皮,好像一个对于眼前的情景既害怕又好奇的孩子。真实情况并没有同我的猜想格格不入,我需要摆出一副困窘的诗人作派,宣告自己怀揣的那一点点希望的破灭。不得不宣告,有关我过去的材料终于随着房屋的坍塌、火焰的溢出成为了压抑的灰烬。就算它们躲过了“叔父”的火把,也难逃这场火灾,是命运而不是火焰碾碎了一切!
后来,我只记得,我在猛烈的咳嗽,就像一个肺病患者。当单架将我送上救护车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身旁的房东太太,她绝望地躺在单架上,氧气罩让她显得瘦小、憔悴,像一位刚刚遭受挫败、输得血本无归的老赌婆。她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昏暗的车顶,低低的呜咽声和眼泪将此时的她刻画得真实而悲伤,让我感到庆幸的是,房东太太的表现并不像一个刚刚死里逃生的人所应有的那样,希望大于恐惧。然而,她不断传递着一些能够继续存活下来的启示,她终于开始反思缔造这一切灾难的源头。它也不是火焰,而是冲破理智的性情。
这是一周以来我第二次来到了医院的病床上,虽然,我坚持自己没有什么异常状况,可是,院方还是强行将我留在了医院,他们说我需要作进一步的留院看护。我需要休息,而这样多余的护理唯一提供的好处,就是能够借给我一个暂时睡觉的床位。房东太太在这一点上也许能够跟我达成共识。因为,她被分去女性病房,所以,我不能适时地安慰这个正经历悔悟的女人。我知道,没有什么比房子塌了、家当全都变成废墟更让她伤心欲绝的了。不过,我无法推测她的心态。正如我无从估计赤道城市的气候变化一样。
有必要说的是,我的思考有时会极其努力地靠近我在底特律病房时所构思的过去。借助那么多往事的碎片,我能够顺着一条有些腐烂,但是依旧粗粝的绳索来到我灵魂期盼已久的岸边。我一直是这样想的,那些我昔日的专利:我的签名、笔迹、图画、有些发黄的胶片、成长的影像、瞳孔微弱的光线、生动的造型。就算它们被我忘却了这么多年,我仍能够在心底,捧出一把曾经供它们生存的土壤。而当一切都郑重其事的在我眼前重新展开时,我猛然醒来。好像心底那片干枯、龟裂的土地突然迎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我热切的期盼还原它们,我像从前写政论文章那样断章取义,像透视我和伊怜的情感那样推心置腹。在病房里、在去机场的路上、在返程的飞机上。我填补着自己的空白,极尽贪心又唯唯诺诺。我在打我自己的主意吗?还是,我在继续困扰着自己,让自己变得像蓝一样,忧郁、孤僻?
难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把戏?这把火,难道是他善意的警告。他难道在说,“你永远留不住它们,我亲爱的孩子”?他是在给我机会,还是在测试我的记忆力?可惜,我不能做到过目不忘,我相信,没人能够做到。因为我曾亲身经历过,也曾亲身遗忘!
现在,我的文档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它们像焦炭一样随着烟雾弥散。我也没必要叹息什么,也许就像一位诗人曾说过的,它们错过你,那是它们不属于你,或者,你没必要再记住它们。对此,我更相信后者。延续着这样的思维,我慢慢觉得,我只是遗失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心疼几天,也就不以为意了。
我开始下床活动,这是前几天禁令所不允许的,今天,也就是火灾后的第三天,我被默许出门晒晒太阳了。屋外,初秋的阳光细腻而温顺,它暖烘烘地晒在我的衣服上,使残留的酒精得以挥发。医院的对街就是唤醒花园,即使在万物消沉的秋季,那里也萦绕着生机,好像活在了春天的记忆里。
也许是外面的一丝寒意,我将手伸进了大衣的口袋里,我知道这么做会让它们暖和一些。摸索着口袋,我感到它的内侧有两个坚硬的卡片状东西。出于好奇,我伸入大衣内侧,掏出了两张卡片。当我发现这是银行存折和密码条时,我猛然记起了它的由来——是“哥哥”塞入我大衣口袋里的,它没有化成灰烬。哦!父亲的遗产,不,是他赞助给我事业的资金。那张存折是那样的灼热,以至于我的心咯噔一声,好像舶船触礁。
我不该挥霍我父母未尽的人生!这是我曾经用以拒绝“哥哥”好意的理由。但是,那时的我却无力拒绝他,因为按照他的说法,我是在救赎他,那么,如果我用了这笔钱,谁又来拯救我?我愤然将存折揣在了兜里。我在同我自己赌气。难道,这就应该是我的命运吗?记忆、生活、遗产、背叛,我成为了一个载体,一个通灵法师。因为,我始终不能借助自己的思想摇撼人生,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人生是一场从被动到主动的挣扎。
走累了,我静静地坐在了医院围栏下的石凳子上,我的目光懒散游弋在四周:灌木被细心的园艺人员剃了个平头,它们平整而步调一致;枯萎的藤条像楼房紧绷的脉络,它们正干渴地等待着生命的莅临;医院灰色的门诊部大楼同两座附楼连成一体,仿佛一件被扯开的过季夹袄;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者,面容僵持,目光呆滞,他的嘴唇歪向一边。平静的表面下涌动着精神的痛苦挣扎。一名年轻的护士陪着他散心,她似乎在对他说些什么,这位小脑偏瘫的患者努力的颤动着右手手指,艰难地做着无声的回答;一位同我年龄相仿的男人,从远处走来,迈着小碎步的他可能刚刚探望完医院里的朋友。我朝这个陌生人挥了挥手,他迅捷地回应了我,仓促地返回一副笑脸。然后,掠过了我朝大门走去。我的心情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