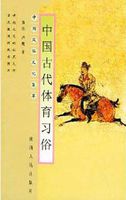王先霈
“和谐”这个概念引入文学艺术之中,非常自然。从发生学上来说,文学艺术生于和谐,没有和谐就没有文学艺术。而有了文学艺术,有了好的文学艺术,又能增进社会的和谐。人类的远祖为了求得劳动中群体动作的和谐,抬木头的时候,“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杭育杭育”,于是有了最早的文学。后来的文学艺术也被用于增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地域人群的和谐。
和谐与斗争,相对立又相补充。古今中外许多文学艺术作品是斗争中的呐喊,是斗争中的匕首和投枪;而斗争的目的,是求得更高层次的、公平正义的和谐。经过斗争,得到新的和谐。
有一段时期,过于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教育功能;其实,文学最常见的功能,是对人心灵的调节。即使纯娱乐型的、休闲式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是很有价值的,在快节奏、高竞争性的当代,尤其如此。
前年,我在丽江石鼓镇参加调研,这里一星期之前遭遇了百年难遇的水灾,并不富裕的农民依然用纳西鼓乐表演欢迎客人,那也是他们自我的心灵安顿。十多位老人那么专注、纯真、安详,我觉得他们的幸福指数很高,让人羡慕。去年,一批世界知名导演应邀参与“国际导演拍北京”活动,拍奥运会专题片,意大利导演吉赛贝·托纳多雷见到北京的一些公园里有很多人在跳舞。这些舞者神态自若,完全陶醉其中。他为之感动,又疑心是接待方刻意安排的,后来知道在中国许许多多地方随时可以看到同样场景。老百姓内心的宁静与和谐,是谁也“安排”不了的,是极高的审美境界。
文学艺术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也应该构成和谐的关系。作家、艺术家是社会的良心,在思想上、道德上应该高于普通人,但同时要从普通老百姓身上汲取营养。不止是创作的材料,还有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还要受老百姓的道德感化,使自己具有高尚和正义的情操。创作者与接受者良性互动,社会底层和高层的良性互动,达到文学艺术活动的和谐、社会的和谐。
文学艺术还要求审美形式的和谐,要求均衡,端庄、圆转,意蕴内含,不过于外露。古希腊以来的西方雕塑,往往具有和谐的结构。著名的《拉奥孔》,人物身体上的极端痛苦“表现在面容和全身姿势上,并不显出激烈情感”,“身体的痛苦和灵魂的伟大仿佛经过衡量,均衡地分布于全体结构”。中国的佛教造像,既体现了宗教精神,同时也寄托了艺术家的人间理想。最好的佛教造像,都表现了和谐之美。中国佛教造像最先从古印度传来,例如,北魏时期建造的云冈石窟,佛像明显地具有犍陀罗艺术的特征。犍陀罗在今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东部接壤的喀布尔河中下游地区,建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五世纪,曾经被马其顿亚历山大王统治,艺术风格受到古希腊和波斯的影响,所以,也可以说,中国早期佛教造像间接地受到过希腊雕塑的影响,但又继承了中国上古造型艺术的传统。云冈石窟佛像就吸收了汉画像石的手法,也参考了当时南朝顾恺之等人画风,人物身体浑圆,秀骨清像,神采飘逸,好像“佛性”均匀地分布在塑像的全身。特别在衣纹的处理上,既有西方雕塑影响的痕迹,更有江南美术装饰化作风。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南朝美术家戴逵,铸造、雕刻佛像,如果“开敬不足动心”,就要不厌其烦地修改。可见,创作主体把思想、心理的静穆放在首位,又不忽视技术的处理,因为线条以及结构安排等形式因素对佛教精神的表现也是至关重要的。瑞典汉学家喜龙仁对中国佛教造像有很高的评价,他在其中体味到的正是静穆:
那些佛像有时表现坚定自信;有时表现安详幸福;有时流露愉悦;有时在眸间唇角带着微笑;有时好像浸在不可测度的沉思中,无论外部的表情如何,人们都可以看出静穆与内在的和谐。
他认为这些佛像超过了欧洲文艺复兴的造型艺术,他说:在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中是变化复杂的坐姿,突起的肌肉,强调动态;而在龙门大佛那里则是全然的休憩,是整体平静的和谐。
请注意,外衣虽然蔽及全身,但体魄的伟岸,四肢的形象,仍然能够充分表现出来,散射着慈祥而平和的光辉。或许是在近现代的欧洲文艺中,静穆甚为稀见,便有许多西方人士对东方艺术中的静穆格外向往。
在文学的表现方式上,陶渊明为和谐、静穆建立了范本,他避免了同时代人的两种偏向,弃绝了玄言诗的枯淡,又迥异于谢灵运的华赡。明代陆时雍评六朝诗说,左思的诗,“抗色厉声”,读了使人畏惧;潘岳的诗,“浮词浪语”,读了使人生厌;唯有陶渊明的诗,素净而又绚丽,读起来像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有悠然之致。宋代曾说,“陶公诗,语造平淡而寓意深远,外若枯槁,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也。”明代钟惺说,“古人论诗文,曰朴茂,曰清深,曰雄浑,曰积厚流光。不朴不茂,不深不清,不浑不雄,不厚不光——了此,可读陶诗。”以上这些评语,既是对陶诗的描述,也是对静穆的审美境界的描述。领会他们所说的内与外的关系,才能领会静穆。不朴之茂,不是真茂;不深之清,不能久清。读者要从朴素中读出它的华茂,从清澄中读出它的深邃。钟嵘说陶渊明“文体省净”、“风华清靡”,这很接近于文克尔曼说的“没有任何杂质的水最好喝。同样,最单纯、没有任何华丽、拘泥和装模作样的美质是完善的。”试从具体文本来体会文学中的静穆,可以举陶诗《时运》的第一段为例: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余霭,宇暧为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本来,四言诗距离今天人们的阅读习惯已经很远,人们比较习惯五言和七言等奇数字的句子,偶数字的四言诗每一句词语的组合,节奏的起伏,较难造成变化,虽然如此,这首诗仍然给我们流畅和平易的感觉,诗语在平实中隐含了精巧。开头两句用叠字,而“迈”和“穆”两者又是双声,颇似诗人一面在晨风里缓步徜徉,一面自语、微吟。迈迈,是不停息地流逝;穆穆,是宁静、静默、凝止,两者构成对比。英国新批评派的学者燕卜荪,在他的《朦胧七型》里,对这首诗的头两句有长篇分析。在滔滔不息的时间之流里,短暂的转瞬即逝的晨光却让人感觉静止,这是宁静、永恒和流逝、变迁的汇合。五六两句是对称性的句子:夜露洗去烟霭,山谷里留下几缕如带的宿雾;云朵在天空彼此追逐,衬托得天空更蓝。清风轻拂禾苗的叶片,好像是它们张开了翅膀,迎接阳光与朝露。一切是那样地平和,一切又是那样的生机勃勃,这些诗句是那样地清丽,同时,又是那样地渊深。这就是静穆,这就是和谐。
王先霈,湖北省作协主席,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