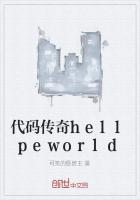自从我把那封信交给女孩以后,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明显比以前减少了很多,特别是一起打游戏的时间,他对乒乓球的热情也一下从珠穆朗玛峰(世界最高的山峰)降到了马里亚纳海沟(世界最深的海沟),每当看见他坐在女孩前面的位置上胡侃神聊的时候,我都好怀念把乒乓球直接打出墙头外面的日子,就在他讲的兴起时,我就会主动走上去,握着他那双抓过乒乓球拍又同时抓着馒头的手,激动的涕泪横流“玮柏,你还好吗?”
“玮柏,再和我去打一场乒乓球吧?”
“玮柏,我是你的铁杆粉丝,铁杆乒乓球粉丝。”
他会抬起眼皮看一下我,这个稍纵即逝的眼神里饱含着太多的千言万语,这一刻,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汇成了我在游戏厅第一次见到他时听到的那句话“你,谁啊?”
他这样对我,我不会怪他,更不会生气,仍旧微笑着看着他,三十秒过后,我会站在教室门口的长廊上,冲着走廊尽头的办公室大声疾呼“王—老—师,您快来看看吧,刘家佛正在和,,。”
不到三秒,刘家佛就会冲上来捂住我的嘴,连愧疚带道歉的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去拿乒乓球拍,你等我,你一定要等着我。”
那个酷似潘玮柏的背影里轻轻摇曳着女孩干净的笑声,像一只悠扬的风笛,吹动满湖的水,吹来一阵阵伶仃。
他每天都要来我们教室,一天一百多遍的来,听着他偷偷摸摸又痴心不改的脚步声,一种深深的惆怅感从大马路上翻过墙头爬了上来,爬进了我那颗想要为祖国的体育竞技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的心里,熊熊燃烧的那把火被兜头浇灭,我也只能仰天长叹,质问苍天“报国无门乎?报国无门兮!”
时间如匹奔腾的马,呼啸而过到彼岸,多少和它一起奔跑在同一条路上的人被甩在了身后,它不会伤心,也不会难过,更不会停下来,因为它不是人,是畜生。
毕业后我和他去了不同的城市,他去那里的原因很简单,女孩去了那里,他还要给她讲笑话听。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追求,不同的梦,很难再找出一些相同的事情来,所幸的是,还有一年半载最多一次的相见,在维系着曾经拥有的感情,在世俗的滚滚浪潮中相互珍惜着前行。
如果有人问,你想要什么?你会回答说,你想要的有很多,那个问你的人听后就会笑笑,笑完之后告诉你,那些东西都很好,可惜都不是真的,你也会跟着笑笑,笑着把那些你想要的东西都扔掉,扔的一干二净后就会操着那个人的口气问“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刘家佛。”
“我想顺顺利利毕了业,拿到毕业证。”
“想找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想有个安稳的家。”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比很多人做的都要好。
“嗨,哥们,今晚有空吗?出来聚聚吧。”
接到刘家佛打来的电话才知道,他也来到了这个城市,跟以前一样,他并没有多少改变,我看着坐在他身边的女孩,半开玩笑的说“我当时要把那封信拿去上厕所,我们现在还能在这里坐着吗?”
女孩和他都笑了,女孩的脸红了,像那天她递给我那封信时一样,看着刘家佛脸上泛起的笑和身旁有着同样笑容的女孩,我又情不自禁想起了去年他们结婚时的那一幕来: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女孩穿着修长的旗袍,面对着照相机,留下了两个长长的微笑,热闹的人群外,下着漫天的大雪。
我们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他说要好好工作,攒钱,买房,买车,我望着已经把长长的刘海减掉的他,怎么看怎么像二十年前的潘玮柏,像二十年后的潘玮柏,就是不像几年前的那个潘玮柏了,那首让我不想上岸的歌他不会再对我唱了,但是在他心里,仍一遍又一遍在唱着:
“开心不开心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快乐不快乐的都跟我来,美丽而神圣的时光不等待,,。”
回去的路上,我又想起了刘家佛给我说起过的那个理想:
“刘家佛,你将来的理想是什么?”
“理想?大的小的?”
“大的小的?你的理想到底有多少个?”
“有很多,比如说考试能及格,乒乓球永远打不坏,赵云能刀枪不入什么的。”
“就这些?”
“还有,我什么时候能够取个媳妇。”
“这都不是理想。”
“你说理想是什么?”
“理想就是……理想就是……”
我抬起头,便看到了理想,站在对面公车的站台上,正在冲我挥着手,又高又瘦,真的很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