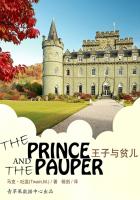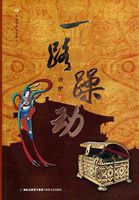一.乌鸦坟的枪声
提起乌鸦坟,郭辖村的百姓就谈坟色变。
乌鸦坟原本叫郭辖山,位于郭辖村的北部。自从有了童养媳七娃的传说后,就没有人再叫郭辖山了。
据村上的老人说,很早以前,郭辖村有一个孝顺而聪颖的七娃,六个姐姐先后饿死。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不满十岁的她过着艰难的生活。母亲死后,才十二岁的七娃不愿看到母亲的尸首暴露荒郊,便决定卖身葬母。于是,她成了郭财主家大少爷的童养媳。郭财主父子对其百般虐待和凌辱,她不堪忍受,在十五岁那年逃了出去。不料被郭家抓了回来,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被扔在了一个地窖中。几日后,打开地窖盖子,一只全身长满黑色羽毛的大鸟腾地一下飞了出来,径直朝着村北的郭辖山飞去。当日,夜幕降临后,一只黑乌鸦落在郭辖山一个高高的坟顶上不停地“苦哇、苦哇”地叫着。夜间,又从山上传来七娃那悲惨的哭声。那乌鸦便是七娃的化身。从此,常有乌鸦落于此坟,乌鸦坟因此而得名。
乌鸦坟神秘的传说,给郭辖村人罩上了一层恐惧的面纱。直到现在,村里无论有多大胆的人,也不敢夜间路过乌鸦坟。据说村里的“张大胆”一次与人以一口猪打赌,硬着头皮也只走了三里多地,还不到乌鸦坟边,吓得掉头就往村里跑,一路上叫爹喊娘的,大病一场数日不起。如此恐怖的乌鸦坟,逯迦飞在这次侦查中已有所耳闻。然而,她虽然是个女侦探,却胆量过人。今晚执意要只身独闯乌鸦坟。她撇开了合作的老搭档顾函,是想独自欣赏在乌鸦坟上演的独幕话剧《掘墓声声》。
夜已很深,但并不全黑,百米之内的坟墓和树木依稀可辨。逯迦飞腰里别着家伙,趴在一个高坟上,注视着周围的动静。远处,不时传来猫头鹰的叫声,着实令人毛骨悚然。鬼也好,神也好,猫头鹰也好,这些对于一个有着近20年侦探生涯的逯迦飞来说,倒不在话下。因为在她前方几十米处便是两座新坟。左边坟里葬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叫韩山霞,是郭辖村郭光义之妻,死于心脏病。紧挨着右边的一个小坟是韩山霞之子郭圈圈,先亡于母,死于非命(爆炸)。这两个冤魂仿佛就在逯迦飞的身边呻吟,但她并不害怕。或者说正是因为他们母子俩的悲惨遭遇才壮了逯迦飞的胆。要说使她感到挠头的,还是炎热的天气和过于亲近她的蚊子和草虫。
逯迦飞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助手顾函说过,要当一名优秀的侦探,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清楚自己的能力,又了解对手的特点;既要有勇猛的精神,又要有足够的智谋,方能比自己的对手技高一筹。她就像当年借箭的孔明,预测某日定有大雾而巧借曹操的箭一样,推断今晚定有“客人”光顾乌鸦坟。她信心十足地等待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果然,在前方有一黑影朝她走来。这黑影是一个彪形大汉。他左手提着一个黑箱子,右手拿着一把铁锹,来到两座新坟处停了下来。他放下箱子,朝四周环顾了一遍不见动静,就在郭圈圈坟墓的西侧掘起土来。逯迦飞屏住呼吸,仔细看了看那人的体态和动作:“没错,就是他!”那大汉掘了一个并不很深的坑后,打开了箱子,用手抓出一把纸样的东西向郭圈圈的坟上撒着,一把又一把。然后,趴在坟上嚎啕起来。这哭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乌鸦坟也在哭声中震颤。逯迦飞的心情说不上是个啥滋味,好像心里钻进了一条毛毛虫一样的难受。她极力克制着自己。
戏还要往下演,她在等待着最佳时机。
她以左脚为支撑点,前倾着身子,右手紧紧抓着腰间的家伙,注视着前方。那大汉从坟墓上站了起来,走到箱子旁,伸手从箱中摸出一个东西,伫立在坑前,抬头久久地望着天空。他在寻找那颗熟悉的星,他要把心里话全告诉她。可是,看了南边看西边,看了北边看东边,怎么也不见那颗星。他失望了,刚失望地低下头,眼前闪现出两对绿色的小灯。
“啊!是狼。”这乌鸦坟常有狼出现,他再清楚不过了。这时,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下意识地扔下了手里的东西,迅速抓起插在地上的铁锹,凭借韩山霞的坟墓与狼决斗。一眨眼的工夫,一只狼就猛地向他蹿来。他举起铁锹砍下去扑了个空。狼从他右侧擦身而过,险些将他撞倒。他又举起铁锹,第二只狼又向他蹿了过来。逯迦飞拔出手枪,几次想击发却人狼混在一起无从下手。她挪了挪地方,调整了角度,瞅着时机。第一只狼在调转头来再次攻那大汉时,他的铁锹已砍中第二只狼的头部。那狼发出了号叫。他一回头发现前方又有好几只狼奔来。第一只狼一个猛扑,在他闪身的一刹那,砰的一声枪响,狼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把他震蒙了,几只狼也吓得掉头就跑。他稍稍定神,双手握着铁锹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逯迦飞。他又朝着躺在地上“嗷嗷”叫的狼砍了一锹。这狼的号叫声像是求救的信号,将几只跑开的狼重新召了回来。
“老子今天拼了,也不能让狼活活咬死。”他只有这么个念头。他紧握着铁锹,歇斯底里般地叫着:“来吧!狼崽子,老子拼了!”他挥舞着铁锹,朝进攻的狼乱砍一阵。逯迦飞瞅准了目标又砰砰地开了两枪。
“是谁?”他这才意识到身边有人。
“你这个笨蛋,我已在这儿恭候你多时了。”逯迦飞迅速向他跑去。
“你……你……你……”她的出现,既使他感到愕然,又给了他得救的希望。
“小心,狼又上来了。”逯迦飞话音刚落,又是一枪。毫无疑问,这只狼同样成了她的枪下鬼。一阵激战,他身上见了红,她也挂了彩。
一只狼又向他疯狂地扑了过来,由于他站在逯迦飞的前面,她无法开枪。逯迦飞急中生智,猛地一脚将他踹到了坑里,而自己的身体却成了狼扑咬的对象。她往右一闪,朝着狼开了一枪,接着又朝站在坟头上的狼开了一枪。凭感觉,膛里的子弹快打完了。她将枪换到了左手,腾出右手想到腰间摸弹夹,可是,弹夹刚取出来,一只狼又向她发起了攻击。就在狼撞击她身体的同时,左手扣动了扳机,狼是被击中了,自己却也被狼撞倒在地,左额磕在了一个树桩上。
她昏了过去,右手还紧紧握着弹夹。
他从坑里爬了上来,不见逯迦飞。地上躺着的,他也分不清哪是狼,哪是人。他慌了,又大喊起来:
“逯侦探——!你在哪里——?”
他转过身来,朝北望去,有两只狼向远处逃遁。渐渐地,两个黑影消失在夜幕中。他将远处的目光收回眼底,才突然发现躺在自己左侧的逯迦飞。
“逯侦探!逯侦探!”他一边喊着,一边去拉她。地上露出一个一尺多高的树桩。这树桩告诉了他,逯侦探伤到了要害处。
他轻轻地放下了逯迦飞,望了望尚未天明的夜空,一种自责感冲到了自己的脑顶。这茫茫黑夜该怎么办?如果逯侦探真有个三长两短,就是死一千次也抵不了自己的罪孽!他憎恨自己,也憎恨这该死的狼。
“无论如何也要想法救活逯侦探。”他只有一个念头,“背也要把她背到医院去。”
他把手上的血在自己的衣服上蹭了几下,背起了逯迦飞,朝着公路走去。
逯迦飞脸上的血还在流着,和汗水一起把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他摔倒了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倒,再爬起来,走着……向前艰难地走着……
公路就要到了。他浑身是劲,一鼓作气把逯迦飞背到了公路上。他轻轻放下了逯迦飞,想歇息片刻,却意外地发现路的北面有一束灯光。
“车!”
他惊喜不已,“有车就有救,”他心里在说。
灯光越来越近,他赶紧把逯迦飞放到路的中间,想拦下这辆车把她送往医院。然而,当车快要到来时,他又害怕起来,迅速闪到路旁,“不行,万一司机不管怎么办?”他又往回走了几步,“不行,逮着我怎么办?”他又退到了路边。
“吱——!”车在离逯迦飞三四米处停了下来。他躲在路旁窥视着,见面包车上下来两个当兵的,心头一喜:“有救了!”
两个当兵的向车周围扫了一眼,就迅速将逯迦飞抬进了车内。车向南疾驶着……
他双膝跪在地上,双手捂着胸口,朝着车去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他抬起了头,望着南去的车,对逯侦探的命运是吉是凶真不敢往下想。他还是久久地跪在那儿。他在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车约莫跑了五十多公里,山路的颠簸把逯迦飞从昏迷中颠醒了。当她有了意识的时候,仿佛自己是在梦中。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而眼前的一切使她感到惊讶。她并不明白自己是怎样到这车上来的。
“快停车!”
她突然大叫一声。这是她苏醒过来后的第一句话,把两位军人吓了一跳。
“同志,你是?……”一个上尉军官问道。他根据逯迦飞腰间挂着一个快枪套的情况,判断她可能是个警察。但在没有搞清她确切身份之前,不得不用这种试探性的口吻。
“我是公安局的。上尉同志,请马上停车。”她请求道。
开车的司机是个中士军衔,在没有得到上尉指令的时候,并没有停车的表示。他打开了车内的灯。上尉看了看坐了起来的逯迦飞,不解地问道:“你这是?……”
逯迦飞这才看了看自己的身上,衣服也破了,满身是血。又摸了摸仍在疼痛的额头,血沾在了手上。她似乎没有理解上尉的意思,答非所问地说:“车是在往哪里开?”“往市里。”上尉答道。逯迦飞用手拨开玻璃窗,把头伸向外面,天还没有亮。她缩回了头:“上尉同志,我有紧急情况,请马上调转车头,开往乌鸦坟!”
“乌鸦坟?”上尉并不知道这地名,十分关切地说:“你的伤太重,还是先去医院吧!”他把自己的手绢递给了逯迦飞。
逯迦飞接过手绢擦了擦额头:“不!来不及了。请你配合一下,不能再往前走了。”
“那你的伤?”
“不要管我,没关系的。”
他执拗不过,命令中士:“调头!”
中士的动作十分麻利地将车调转过来,以七八十公里的速度前进着。“快!再快点!”逯迦飞催促道。她心急如焚!
这条通往郭辖村的公路,她是多么的熟悉。从市里到郭辖村,从郭辖村到乌鸦坟,往返多少次连她自己也记不清。郭辖村的家家户户,郭辖村的每一个堤塘河坝,田头地角,山林果园,都留下过她的足迹。这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
她把历史的时钟往回拨了一圈又一圈……
二.爆炸发生在子夜
郭辖村的东头,有一家砌有院墙的独户。这就是韩山霞的家。这家的户主叫郭光义,原是县供销合作社的一名普通职员。八年前辞职到南方打工去了,至今杳无音信。对他的传说可是不少。有人说他在外发了大财,有人说他到香港去了,还有人说他扒火车摔死了。总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家里只有妻子和一个才15岁的低能残疾儿郭圈圈。母子俩相依为命。虽说郭圈圈是个低能残疾儿,却成了韩山霞生活的精神支柱。韩山霞疼爱照顾残疾儿子的许许多多感人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因而,在郭辖村方圆几十里,没有不认识韩山霞的。她是公认的贤妻良母。为了给儿子治病,她省吃俭用,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但是,儿子喜欢吃的,她总是最大限度地去满足一个残疾儿的要求。前些天,郭圈圈吵吵着要吃黑鱼(南方也称才鱼)。9月2日这天,她大清早跑了十几里山路,到街上高价给他买了一条三斤重的大黑鱼。晚饭时,圈圈几乎没吃主食,有滋有味地吃了一顿妈妈做的清炖黑鱼。看着圈圈吃的那香劲,韩山霞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天晚上,韩山霞按照往常的习惯,把圈圈安排在床的里侧,等他入睡后,自己方在外侧安歇下来。今晚圈圈睡得格外的甜,渐渐地,韩山霞也进入了梦乡。
子夜时分,韩山霞起解。刚下床就隐隐约约听到房内有“嘀嗒嘀嗒”的声音。可静心地听了一会儿,就是听不出这声音来自何处。“大概是自己的幻觉吧!”她揉了揉眼睛,到猪圈解手去了。解毕,她刚走几步,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剧烈的爆炸和震动,使她跌倒在墙边。当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不顾一切地向房里冲去:“圈——圈——!”
房内的衣被燃烧起来,浓烟滚滚。无论她怎么叫喊,就是听不到圈圈的声音。
爆炸的碎物“噼噼啪啪”地落了下来,她全然不顾,还是一个劲地哭着、喊着:“圈——圈——!”
一个抛落物重重地砸在了她的身上,她昏死了过去。
爆炸声、哭喊声惊醒了村里的人们。
“不好啦!光义家着火啦……”
“快来人哪……”
“……”
村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小媳妇大姑娘,不一会儿工夫挤了满满一院子的人。上房掀瓦的,提水传递的,灭火的,救人的,指挥的,喊叫的,围观看热闹的,喧闹非凡。从村南到村北,从村东到村西,里里外外,鸡鸣狗叫,响声震天。
最先冲进屋里的人救出了韩山霞。可是,由于烟大,怎么也没找到圈圈。待火扑灭后,人们才发现圈圈。把他抬到院子里一看,头发全无,四肢弯曲,躯体蜷成一团。尸体已炭化。
韩山霞被人送到乡卫生院抢救,是死是活乡亲们都悬着一颗心。
在韩山霞家斜对面有一个小山坡,山坡上蹲着一个黑不溜秋,长着一身懒肉的汉子。他是刚从救火现场来到山坡的。他赤着双脚,光着脊背,身上只穿着一件肥大的裤衩。脸上除了一对眼珠外,再也找不到一处干净的地方。他用一双呆滞的目光痴痴地望着韩山霞的家。谁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他姓车,名九斤,是村里出了名的懒汉,至今光棍一条。因他长得浑圆,村里人都叫他车轱辘。韩山霞家一出事,作为光棍的他自然脱不了干系。因为他曾多次光顾过韩山霞家。
探长逯迦飞带领她的侦查、技术人员赶到现场时,郭圈圈的户口已被村里迁到了乌鸦坟。
逯迦飞的到来,给郭辖村带来了一分神秘感。村民们里三层外三层,把逯迦飞和她的同行们紧紧地围在中间。他们要亲眼目睹当代中国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女神探逯迦飞的风采。
看上去,逯迦飞与普通的女子并无两样。她三十出头,一米七的个头,一头齐肩的乌发,把一张圆圆的脸庞儿包在了中间。双眼皮下,只有一双明亮的眸子,才显示出她那侦探的特性。因为她那张嘴和脸庞是随着眸子的变化而变化的。当眼睛发出温柔的目光时,脸庞和嘴是微笑的;当眼睛发出咄咄逼人的目光时,脸庞和嘴就是眼睛的卫士,足以使犯罪分子望而生畏。这就是她的神秘感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神秘感体现在她的智慧之中。她决断问题有一种固定的“三段式”,即了解事物的全貌,调查分析问题;找出内在联系,进行归纳推理;果敢决断,定下结论。一旦决心已下,“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今天她也不例外。到达现场后,先听情况介绍,从不先入为主。她拨开人群,围绕现场环视了一周,思索片刻,一个工作方案在脑子里形成。她决定兵分四路,齐头并进。吩咐她的助手顾函带一个人立马赶到卫生院,对韩山霞进行询问;由马法医带人到乌鸦坟,对郭圈圈进行开棺验尸;两名侦查员在村里开展调查访问;自己和几名技术员、摄像师勘查现场。她就像一个出色的导演,本案的侦查工作在她亲手导演下,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这是一个遭到严重破坏的现场,勘查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从上午到中午,从中午到下午,连续10个小时他们没喝过一口水,肚子没进过一粒食。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村里的郭主任带人送来一桶混汤面条,他们饥肠辘辘的肚子才得以填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