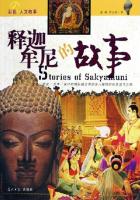一天下午,突然传来隔壁难友老朱的哀号痛哭之声,金诵盘和蒋公谷连忙过去探望,老朱泪流满面,哀伤不已地诉说着。原来他的老父70多岁了,因年纪大留在家里死活不肯离开,谁知日本鬼子一来就把他杀死了。老朱来到安全区以后,天天惦念着父亲,终于听到了父亲被日本鬼子杀死的消息,不得已,他只好恳请金陵女大美籍教员魏特琳小姐陪同前往探视。来到家附近,远远地只见一群日本兵正在他家中高歌狂欢,父亲的尸体横陈在屋檐下。看到日本兵一个个狰狞恶煞的样子,老朱不敢近前去殓尸,只好饮痛而归。老朱哭诉说:“人已经死了,还不能收殓,这是什么世道啊!”金诵盘他们劝慰了一阵,这才回到自己房间。
没过几天,另一边又传来邻居全家号啕痛哭的声音,金诵盘和蒋公谷连忙走了过去。这一家难民男的因为面色特别黑,大家都叫他黑子。黑子的弟弟流着泪告诉说,今天早上他和哥哥一道回家拿东西,在路上碰到日本鬼子,鬼子兵立即抓住黑子不放,一口咬定黑子是中国兵,捆绑起来放倒在地上,然后举起刀来乱砍。黑子痛极了号叫着蹦跳躲避,一跃好远,跃到路边的塘里淹死了,他自己侥幸逃得性命回家报信。家里一听便像开了锅的粥,母亲哭得昏死过去,嫂子哭得在地上翻来覆去打滚,不停地用双手捶打着自己的胸脯,说是千万不该让黑子回去,否则就不会有此惨祸。一岁多的侄女也跟着大声号哭,景象惨不忍睹!金诵盘他们听了,连连叹息不已。
大使馆内原来是住有两名美国人的,但美国大使馆撤离人员乘坐的“巴奈号”兵舰在芜湖被日本飞机炸了,不少人受了伤,接到消息,大使馆的两名新闻记者匆匆赶往芜湖探望。美国人一走,难民们都好像失去了保障似的,空气愈加紧张了。日本兵是三天两天进来洗劫,窗外每天都可以看到一队队被捆绑的中国人被押往屠场。最残酷的杀戮是活埋,那凄厉悲惨的哀号—人类生命中最后挣扎出来的一种尖锐、绝望的呼唤,抖散、波动在瑟瑟的寒风里,时不时地从窗外隐隐地传来,叫人骨寒心碎,终身难忘。
一天下午,美国大使馆侍役崔品三神情紧张地来到金诵盘房里说,有人向大使馆公事房报告,说你们几位是军人,恐怕是有奸人告了密,若传到敌兵耳朵里,那就太危险了,你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为好。大家听罢,仓促间也来不及多加考虑,便匆匆离开了美国大使馆,踏着凄凉的脚步,在寒风凛冽的街头瑟缩,踯躅,寻找着一方可以求生避难的地方。在街头正好又遇见美国大使馆厨役何海清,双方擦肩而过,何海清也紧张地说:“使馆已在调查你们,千万不能回去了!”说完便匆匆走开,好像敌人就跟在他身后似的,可见事态已相当严重了。
金诵盘3人再也不敢回美国大使馆,只得在街头奔走、流浪。作为中国人,竟然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找不到一隅安身之所,不禁悲愤交加,百感丛集。直到夜幕将临的时候,才在惊惶中侥幸于金陵女大收容所友人徐子良先生处找到一个暂时避难的场所。第二天又经朋友帮助,在汉口路9号住了下来,这才得以稍稍安息。
日子就这样在血腥的恐怖中一天天地度过,天天都有坏消息从外面传来。电厂、自来水厂的工人都被敌人杀光了,水电一时也难以恢复,所有的水塘里都浸着忠魂,大家也只有饮用这样的塘水。到一月中旬,子良告诉他们说,红十字会已着手掩埋尸体多日了,就在金银巷金大农场,挖了很深的狭壕,把尸体重叠着埋入,掩土了事,听说编号登记的,已经有12万具了。大家听罢,嗟叹不已,深深感受到做亡国奴的灾难、痛苦和悲哀。
一天,金诵盘和蒋公谷外出时,意外遇见了野战医院尤院长,问起沦陷以后的情况,尤院长说他现在已化名叫洪少文,就住在附近颐和路。大家来到尤院长住处,这是一座漂亮的楼房,里面陈设华丽,一点也没有日寇洗劫的痕迹。大家正感诧异的时候,尤院长却告诉他们,他现在和自治会孙会长住在一起,且有两位女友同居,一点也没有受到日军的威胁,说着,露出颇为得意的样子。
金处长一听,脸色骤变,当即告辞回来,并约他以后到自己住宅再见。过了几天,尤院长来到金诵盘处所,又谈起沦陷以后,孙淑荣如何卫护着他、帮助他脱离险境,他内心是如何地感激,现在孙淑荣又如何要他到自治会当卫生组长等等,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套,毫无羞耻之感。
金诵盘一直脸色严峻地听着,待他说完,便两眼投去锐利的目光,声色俱厉地问道:“那你是准备去当汉奸罗?!”
尤院长一愣,知道自己得意忘形,说走了嘴,便一声不响地待着,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金诵盘继续斥责道:“我们都是中国人,你可不要忘了本,因为一点小惠而乱了大节,造成终身的遗恨啊!”
尤院长支支吾吾地应着,稍顷,告辞离去。蒋公谷望着他的背影,叹息说:“这个人贪生怕死,见利忘义,我料他汉奸是做定了的!”
金诵盘也叹息说:“疾风知劲草,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注重气节。沦陷以后,我们救护处许多弟兄惨死在敌人屠刀下面,没想到却出了这么一个败类!”
转瞬到了1938年2月下旬,敌人的血腥屠杀渐渐缓和,金诵盘、蒋公谷经过打听,知道许多难友已脱险离开南京,所走路线大概有三条:一、托人花钱买到敌特务机关或兵站的通行证,可以乘敌人兵车,直达上海,但盘查极严,到了上海,也不容易进到租界;二、出通济门路行,可以到苏州、无锡一带,再搭船赴上海,但中途时遭抢劫,也很危险;三、由上新河渡江到北岸,经和县、含山等处可以到达汉口,但其间也有红枪会等组织盘查或劫掠,要有熟人带路才能通过。
打听清楚以后,金诵盘、蒋公谷就开始商量逃离南京的具体步骤,首先与教导总队南京便衣人员联系,准备走过江去武汉的路线,但几经周折,没有走成。正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件危险的事情,一天中午,一个名叫中山的日本便衣突然来到他们住处,徐子良赶紧出来和他周旋。那中山两眼不停地往屋内打量,一边不怀好意地问道:“你们中国军官留在南京的很多,你有认识的吗?你可以指出来告诉我吗?”
徐子良只装听不懂,磨蹭半天,才慢慢听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回答说:“我是一向在上海做生意的,因为战争才回到无锡老家,后来又携带家属逃到南京来的,哪里认得什么军队的人啊!你问的事,我可是一点也不明白。”说着徐子良又连忙把妻子和儿子叫出来,以表示自己是普通的经商人家。中山看捞不到什么,这才悻悻地走了。
中山一走,大家都捏着一把汗说,这匹狼狗既然已经嗅到了味道,决不会就此罢休,这里是万万不可再住下去了,必须尽快离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2月25日,终于托人弄到了敌人兵站乘车证九张,金诵盘一行九人决定分两批离开南京。27日凌晨五时,金诵盘等四人来到车站,站内敌兵罗列,气氛紧张,每一棚车内由四名敌兵把守,荷枪实弹,如同押解囚犯一般,把他们押出了南京。沿途断垣残壁,人烟绝迹,一片凄凉!
下午到达无锡,又经过一番盘查才得以下车离站,沿江行约半里路,竟没有一幢完整的房屋。在江边雇了一只小船,过黄婆墩,又经过敌人关卡的搜查,于下午四点多钟到达曹家桥徐子良家中,登堂拜母,合家欢欣。
这里是敌我交接区,已处于无政府状态,白天日军常常下来掠取财物,夜间又有土匪抢劫。大家都提心吊胆,故稍事休息两日后,便开始设法觅船离开。3月4日凌晨三时上船,同行的已达20余人,因沿途多处驻有敌兵,船只绕道而行,不仅耽误时间,而且造成搁浅。至下午三时方过汤岐,突然两岸出现许多持枪的便衣,大声吆喝停船。大家一看不好,遇上劫匪了,于是频频催着摇船的拼命前进,岸上人见不肯停船,枪声大作。行不及半里,至钱木桥,江面一排枪虎视眈眈地架着,不得已,只好停船上岸接受检查。相互询问这才知道拦路的并不是劫匪,而是地方游击队,大家方才松下气来。当晚到达长寿,又经过几日艰苦的行程,于3月8日到达上海,在上海租界区休整了半个月。24日,由金处长率领蒋公谷、徐子良等一行人搭乘荷兰轮船“芝沙丹妮号”南下,经香港绕道于4月9日回到武汉,这才完全恢复自由,重新走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捍卫中华民族生存的伟大战场。
拉贝的愤怒
15日夜晚,大批日军士兵闯入金陵大学校舍,当场强奸妇女30人,有几名妇女甚至被六人轮奸,在安全区其他一些地方,当晚也发生同样的事情。
另一支日军来到一个收容所,宣称有6000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军人进入了安全区,必须把他们搜索出来。于是青壮年人人过关,穿军服的,当过兵的,自是在劫难逃。即使是平民百姓,只要手上有茧,肩上有趼,也难逃厄运。日本兵把他们从人群中抓出来,甩绳子缚着,每100人圈在一起。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正在煤油灯下召开会议,听到报告,拉贝带着委员们急忙赶了过来。他气喘吁吁地向日本军官交涉、争辩着,但是无济于事。费区在队伍中急忙地穿来穿去,他想寻找到昨天向他交枪的四个小个子广东士兵,他们是怀着满腔报国之志来到抗日前线的,壮志未酬,实在不愿意放下武器,说话时眼睛里还燃着熊熊的火焰。还有一个大个子的北方军官,他曾满怀惆怅地向费区倾诉了战败后的痛苦和遗憾,那一双深深凹陷的失望的眼睛,令他毕生难忘。他想找到他们,哪怕再看上一眼,哪怕稍稍表示一下自己无能为力的痛苦和遗憾。但是他找不到他们,也许他们早已被圈进被缚的人群中间去了,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死神的咆哮和狰狞。
1300多人被全部捆绑完毕,日本人命令他们排着长队向马路上走去。刺刀的寒光在星月下闪耀着,没有叹息,没有哭泣,1300多人在马路上缓缓地移动,只有痛苦和悲哀深深地压在人们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