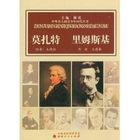胡文秀看着女儿把戒指和万金油盒子,用手巾包成一个小包,亲手递到她手上。胡文秀更觉得奇怪了,不知道女儿打的是什么注意。但她抬头一看,心里就明白了。
只见刚才和胡兰说过话的那个复仇队员金川子,引着两个端枪的阎匪军耀武扬威地走过来。敌人走过来,吓得人群向两边拥挤,引起一阵骚动,但谁都没有出声。
金川子指了指胡兰说:“这就是刘胡兰。”
一个匪军见到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刘胡兰,不怀好意地看了看,自言自语道:“嗬,好漂亮。”
家里人见敌人来抓胡兰,大家不由得挤得更紧,把胡兰围在中央。爱兰吓哭了,胡兰拍了拍爱兰肩膀说:“不要怕,别哭。”
敌人一下推开了家人,动手要拉她。胡兰瞪了他们一眼,严厉地说:“别拉扯,我自己会走。”说完,把头一扬,大踏步向观音庙里走去。
两个来抓胡兰的敌人和金川子先是惊奇地愣了一下,然后就端着枪紧紧跟着胡兰,好像她要长翅膀飞了似的。
胡兰走上观音庙的台阶,对趴在那里号哭的李薏芳说:“别哭了,敌人不会可怜你。“边说边走进门去。
一进庙内,押解胡兰的敌人让她站住。金川子抢先跑进西房去了。胡兰站在院里一看,只见正殿廊檐下有几个先后被捕的人,有的蹲着,有的坐着,有的耷拉着脑袋,有的怒视着端枪监视他们的匪军。石三槐和石六儿被五花大绑着。石三槐头发乱蓬蓬的,身上的衣服被撕裂了许多口子,多处露出了棉花,撕破的衣服条条缕缕,风一吹飘摇着,透出无限凄惨之情。石六儿满脸血污,有一只脚上鞋袜都没了,踩在冰冷的地上,让人感到寒气逼人。他们用吃惊的目光看着胡兰,胡兰向石三槐和石六儿投去敬佩的目光,并向他俩微微笑了笑,用一笑表达了革命同志之间深切的问候。
这时东房里传出拍桌子打板凳的声音,和敌人的叫喊声。猛地传来一个非常清脆的耳光声,只听金香哭喊道:“我不知道,我实在不知道呀!”
“不知道,枪毙你!”这是敌人的声音。
胡兰朝东屋望了一眼,她多么希望金香坚强点,能经得住这个考验。
这时,金川子从西屋走出来,他拉开风门对胡兰说:“特派员请你进去。”接着他又向胡兰低声说道:“他问你什么,你说什么,保你没事。反正你不说,人家也知道。石五则全都‘自白’了。”
胡兰没有答理他,站在门口定了定神,然后神态自若地迈步走进了西屋,毫无惧色。
观音庙的西厢房,原来是村里各团体联合办公的地方,一切摆设还是那个老样子,靠窗台处放着张快要散架的破办公桌,桌上摆着一方打了角的砚台,旁边扔着几支秃头毛笔,另外还有几个粗瓷茶碗。桌子后边放着张古旧的圈椅,靠近门口的地方,摆着一条长板凳。可现在敌人将它作为审讯室了。
屋子里只有阎匪军特派员张全宝一个人。这个人岁数不大,却留着长长的大胡子,胡子油光黑亮。左腮上有指头大一块黑痣,上面长着一撮黑毛,与五官搭配在一起,自然多了几分凶悍。他挺直了腰板,坐在圈椅里,两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双腿向外分开,脚上穿着一双翻毛皮鞋,脸上露出不可一世的霸气,抖出一种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样子。他看到刘胡兰气定神闲得稳步走进来,不由得愣了一下,他压根没想到刘胡兰是个文文雅雅、漂漂亮亮的姑娘,也没有想到如此年轻,更没想到刘胡兰脸上没有一丝恐惧的表情。刘胡兰一进门就直挺挺地站在办公桌前面,两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那种目光有种天然的穿透力一样,盯得大胡子心里有些发毛,他想,这哪像一个来接受审讯的人,倒像是来审讯他的人一样。于是,心虚的他下意识站起身来,提高了自己的视线,想用目光压制对方。其实张全宝本来是想见面给胡兰来个下马威,他一见胡兰这个样子,觉得拍桌子打板凳瞪眼睛这一套不会起作用,说不定适得其反。可是他也不知如何开头才好,他便装腔作势,假作镇静地掏出一支烟,慢条斯理地点着,吸了几口,然后沉着脸才明知故问道:“你就是刘胡兰?”
刘胡兰响亮地回答:“我就是刘胡兰,怎么样?”
“你是八路军的区妇女干部?”
“不,我是民主政府区妇联干部。”
“反正都一样。”
“你给八路军干过什么事?”
“只要我能办到的,什么都干过。”
张全宝听了,真没想到刘胡兰回答得这么干脆,他以为这是刘胡兰“自白”开始了,使他简直欣喜若狂。没料到审讯开头进行得如此顺利,他忍不住站起来,笑嘻嘻地说道:“好,好,好。我就喜欢这种痛快人。”张全宝假惺惺地指了指摆在门口的那条板凳说:“请坐,请坐,咱们坐下来谈。”他见胡兰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又说道:“我只是奉命找你来聊聊,没啥大不了的事。别怕,别怕。”刘胡兰知道这是假话,冷冷地说:“我根本就不怕。”
一句“我根本就不怕”听得张全宝发愣,他停了停继续问道:“那么你们村长是谁杀的?”
“不知道。”
“你们区上的八路军都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张全宝一连碰了几个钉子,再也沉不住气了:“你,你,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刘胡兰镇静地回答:“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张全宝想发作,突然,贼眼一转,威胁着说:“现在有人供出你是共产党员。”
刘胡兰知道自己被坏人出卖,她把头一扬,自豪地说:“是。我就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怎么样?”
“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
“以后你还会为共产党办事不?”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干到底。”
张全宝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的一个小女孩,竟如此厉害。见硬的不行,就换软的,他奸笑着哄骗说:“自白就等于自救,只要你自白,我就放你,还给你一份好土地……”
没等他说完,刘胡兰轻蔑地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
张全宝恼羞成怒,他收起阴险的笑脸,敲起桌子嚎叫:“你小小年纪,嘴好硬啊,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刘胡兰逼近一步,斩钉截铁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员!”
张全宝无可奈何,站起来无耻地说:“刘胡兰,只要你当众说句今后不再给共产党办事,我就放了你。”
刘胡兰坚定地说:“那可办不到。”
张全宝听了刘胡兰的话,觉得这是块硬骨头,随即他话中带刺地说:“那好,那好。”说完,他不服地瞄了刘胡兰一眼,一屁股坐到圈椅上。他见刘胡兰愤怒地望着他,他觉得这话会刺激刘胡兰,于是,忙改口说:“你给共产党做过什么事?”
“什么事都做过。”
“嗯,你们区上除了你,还留下哪些人暗藏在这里?不,不,拿你们的话说,就是还有哪些人留在这里坚持工作?”
“就我一个。”
“你们村还有谁是共产党员?”
“就我一个。”
“不能,不能。”张全宝胸有成竹地说道,“共产党的事我清楚,有小组,有支部。还能就你一个人?我明告你说吧,有人已经向我们‘自白’了,谁是共产党,我们全知道。”
“你全知道何必问我。”
张全宝见刘胡兰不好对付,有些生气,但他为了获取更多情况,往肚子里咽了一口唾沫,忍了忍问:“你最近和区上通过信没有?”
“通过啦,你也不知道。”
“你和他们见过面没有?”
“见过面,我也不会告诉你。”
张全宝“呼”地一下从圈椅上站起来,扔掉烟头,从腰里拔出手枪,“啪”的一声按在桌子上,大声吼道:“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是跟你开玩笑。你再他妈嘴硬,老子一生气就毙了你!”
“随便!”
张全宝气得脸色铁青,胡子不住地抖动,两只眼充满血丝瞪着刘胡兰,想要一口吃掉刘胡兰的样子。他又点上一支烟,抽了几口,安静了一些才说:“好吧,你不想告诉我,我也就不再问你了。”他又坐在圈椅上,慢腾腾地说道:“其实你不说,我们也都知道。我不是吓唬你!你做过的那几件事,我背都能背下来。”
接着他真的像背课本一样说开了刘胡兰的历史。什么时候去的妇女训练班,什么时候当了村妇联秘书,什么时候调到区上,什么时候入的党……说得头头是道,大体不错。后来张全宝又说:“你罪恶很大,你给八路军办了不少事情,要碰在别人手上,枪毙你一百次也够上了。不过,这次是我,看你还很年轻,正是人生的好时光,只要你能改恶从善,我就会宽宏大量,既往不咎,放你一马。这都是阎主任的恩典。”
张全宝一面说,一面用眼睛不住地窥探着刘胡兰,试图打量刘胡兰情绪有什么变化。然而刘胡兰脸色还是那样平静,没有一丝表情。张全宝想了想,又说道:“我绝不为难你,等一会儿开民众会,只要你向民众‘自白’,就是承认你是共产党员,这个你刚才就承认了。你再向民众‘自白’,说你年轻不懂事,受了共产党的欺骗,误入歧途,叫民众不要像你这样再上共产党的当,从今往后,用你们的话说,就是保证不再给共产党做事。天大的事就算完了……”
刘胡兰还不等张全宝说完就说:“办不到!”
“小姑娘,别那么犟。”张全宝这时就像知心朋友一样劝说道,“你是个聪明人,你想想看,不‘自白’能过得去吗?‘自白’才能‘转生’,不‘自白’只有死路一条。你死了不要紧,你爹妈多悲伤,白白养你这么大,你不替自己想,也要为家里人想呀!”
刘胡兰根本没听张全宝说什么,两眼望着顶棚,一句话也不说。
张全宝继续说道:“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穷小子们的党,那是一帮穷疯了的人,尽干缺德事,分人家房,分人家的地。你们家的境况不错,不缺吃,不缺穿,何必跟上那些穷小子们胡捣乱,何必跟上他们受这些连累?你看看,我们一来,你们当官的,不,不,就是你们的领导干部全跑上山里躲起来了,留下你们当替死鬼,他们面都不敢露了。你替他们白送命,这是何苦?这是何苦呀?你好好想想,两条路,由你挑!”
刘胡兰还是两只眼望着顶棚,一声不吭。她清楚:这时最好的反抗就是不说话。
张全宝站起来,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神色焦急。可他还是平和地说:“你年轻,不懂事,全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欺骗。共产党就是能说,什么事一到他们嘴里就变戏法一样说得天花乱坠。什么闹革命啦,土地改革啦……革谁的命?改什么土地?都是些胡扯淡的事。”接着张全宝给刘胡兰长篇大论说起来,一面污蔑共产党,一面吹捧阎锡山。后来又劝刘胡兰,说只要她“自白”了,不仅不咎过去,而且要在“兵农合一”、“编组分地”的时候,专门分给她一份土地。村里可以派人耕种,收下的粮食完全归她所有,可以荣华富贵地过一辈子。最后又说:“你看这还不够便宜,天下哪儿能找这种好事,这是多少人做梦都想的好事呀!”
在张全宝劝降刘胡兰的时候,二连长许得胜进来了,他一屁股坐在板凳上,拿着皮带,轻轻拍打着自己的两腿,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他见张全宝说完,胡兰一声也不吭,抬着眼,没当回事的样子。于是他气势汹汹地站起来吼道:“你他妈哑巴啦?你他妈的以为不开口就没事啦?做梦吧!”他回过头对张全宝说:“你不要和她磨牙了,白费劲,拉出去铡了她!来人!”
话音未落,进来两个匪军,拿着绳子就要动手捆胡兰。
张全宝喝道:“别动手。”随后对许得胜说道:“许连长别上火,你让她好好想想嘛。这姑娘是个聪明人,会想清楚的。”
张全宝问许得胜开会的事准备好了没有。许得胜说准备好了。张全宝转身对刘胡兰笑笑说:“我刚才的话全是为你好,为你着想,你要好好想想。看到吧,许连长可就没那么客气了。”说完,张全宝见刘胡兰依然一脸的无畏,便对两个匪军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将胡兰带了出去。
胡兰出去之后,许得胜不满地对张全宝说道:“特派员,用得着那样和她磨牙费嘴?她愿意‘自白’就出去‘自白’,不愿‘自白’,就咔嚓一刀完事了。让石五则去‘自白’不一回事?”
张全宝说:“当然不一回事,石五则在民众当中,已经身败名裂,他‘自白’民众会想,这是他有意在说共产党的坏话,没有一点儿号召力。师部之所以对此案重视,兄弟认为刘胡兰是目前抓到的唯一一个区干部,而且是共产党员。如果促使她出面‘自白’,则可在这一带让共产党声名扫地,从而提高我方的威望,在政治上打个大胜仗!你想想,一个共产党员的区干部‘自白’了,各村那些‘伪装分子’势必效法。这样一来造成一种‘自白’的风气,不用兴师动众,就可破获共匪组织,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而我方则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这也是师部指示的英明之处。”
许得胜若有所悟地说道:“哦,是这样,你们到底是玩政治的,肚子里道道就是多,真高明。”停了一下又问:“你看她能不能在大会上‘自白’?”
张全宝满有把握地说:“我看没问题,她毕竟是个黄毛丫头,嘴硬点骨头软。再说她还不知道血是红的还是黑的。一会儿先铡了那几个,做样子给她看着,她还不吓得瘫过去,这不就开口了吗?”张全宝又自言自语恶狠狠地说:“他妈的共产党员,我倒要看你是铁打的还是钢铸的!我就不信能翻出了我手心!”
张全宝完全自信,他一定能够降服刘胡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