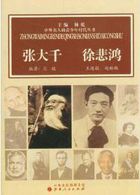胡兰和金香还在睡觉,忽然一阵敲门声惊醒了她们。由于怕是敌人来了,两人显得非常机警,不约而同地问道:“谁?”
“是我,快开门呀!”她们从门外人答话的声音,听出是金香妈李薏芳回来了。两个人立即爬起来穿好衣服,出去开了院门。
李薏芳一进门,带进一股冷气。她脸上冻得通红,呼出的热气遇冷后把眉毛和嘴边的围巾都染上了一层白霜。她又是搓手,又是跺脚,屋里暖和些,她的清鼻涕直往下流,她不住地揩,边活动,边都哝说:“真是冷死了,浑身冻僵啦!脚都不像自己的。”
胡兰问道:“你怎么这么早就往回跑?”
“我老是担心金香和你,所以后半夜就搭上了一个拉炭车往屋里赶。”
听妈妈担心自己,金香就说昨天晚上陈照德带着武工队路过,说形势越来越坏,要让他们上山。李薏芳忙问:“什么时候走?”
金香说,打算今天下午走,陈照德告诉她们先到北齐村去,那里有人接应,再送他们到山上去。
胡兰把火生好,就叫李薏芳去烤火。李薏芳走到火炉边伸出手烘着,嘴里不住地说:“好好好,快走吧。这年月,在村里担惊受怕的真不好活!上山我就放心了!”随后又说:“山上比村里冷,你们一定要多带点衣服。”
她们说三道四,水已经热了。胡兰洗完脸,又梳了梳头,急着要走。李薏芳叫她留下在家吃早饭。胡兰说,不了,要赶紧回家收拾东西。说完往外走,走了几步,她又转过身对金香说:“你可别把东西带多了,爬山路又不是走平川,东西多了就走不动路。”说完就往家走。
街上冷冷清清,看不到一个人影。天空阴沉沉的,看上去很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西北风吹得“嗖嗖”地响,冬天的树已没了枝叶,风一刮树枝“哗啦啦”干响。天气冷得厉害,风吹到脸上,像小刀割破了肉一样。刘胡兰把两手藏在袖筒子里,一溜小跑着回家去。
回到家的时候,家里人也刚刚起来生火做饭。她把要走的消息告诉了妈妈。胡文秀长出了口气说:“那太好了,早点上山就安生了。”
家里人听说胡兰要上山,也都赞成她快点走,离开这是非地。只有不太懂事的妹妹心里不太乐意。她见姐姐忙着收拾东西,撅着嘴问道:“你走了还回不回来?”
胡兰笑着说:“当然要回来,这是我们家。”她停了一下接着道:“当然,要等环境好了才行。”
爱兰愁眉不展地说:“现在到处都是匪军,什么时候他们才走呀?”
“他们走只是迟早的事,你看今天的天灰蒙蒙的,但是太阳总是要出来的。”胡兰坚定不移地说。
接着又嘱咐爱兰,她走后,要像过去那样多帮妈妈干活儿,爷爷老了要多照顾他。还说爷爷那么大岁数了,每天还是照样搂柴拾粪,一天到晚不闲着,他为的是让家里过上好日子。爱兰听着姐姐的话不住点头。
爱兰说:“姐姐,这些事我能做,你不要操心。”
姐妹俩正谈得亲热,金香慌慌张张跑进来了,一进门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坏事啦,匪军又来村里了!”
胡兰急忙问道:“来了多少,在哪儿?”
金香气喘吁吁地说:“不知道。我只看见敌人把村口把了,只准进,不准出。不知道这些狗日的们又要干啥。胡兰姐,你快去躲躲吧!”说完匆匆忙忙走了。
爱兰撒腿就往外跑,边跑边说:“我出去看看。”
爱兰越来越懂事了,胆子也大起来了。每当出现什么情况,她就像侦察员一样到处跑着打探消息。这回她跑出去不久就回来了,她说自己看见有一伙敌人捆绑着几个人到庙上去了。胡兰问她有哪些,爱兰说有石三槐、石六儿他们。
“坏了!”胡兰一惊,不由得替他们担心起来。正在这时,爷爷和大伯慌里慌张跑回来了。胡兰大伯是一个遇事很沉着冷静的人,但这次却是那样慌手慌脚,他一进屋,东张西望地只顾瞅胡兰,差点儿一脚踢翻了放在地上的洗衣盆。他神色慌张地告诉胡兰说,阎匪军正在村里抓人,他看见把陈照德伯父陈树荣老汉,石世芳哥哥石世辉,还有退伍军人张年成都抓起来了。
大伯说:“我看你赶快躲一躲吧!还是小心为好。”
胡兰觉得大伯说得对,应当避避风险。她在一块干毛巾上擦了擦洗衣服的湿手,打算到双牛大娘家去。这时,听到街上响起了锣声,锣点敲得特别响而密,接着就听到叫喊声:“全村民众,不分男女老少,赶快到观音庙上去开会。无故不到,查出来要按私通共产党办理!”
全家人听到锣声和叫喊声,大气不敢出,都为胡兰担心,都劝她赶快躲一躲。可是究竟躲到哪里去?万一敌人要挨家挨户搜查又怎么办?躲到别人家也不保险呀!胡文秀好像想起了什么,向胡兰说道:“到金忠嫂家躲一下去吧。我看那倒是个好地方,她刚生下小孩四五天。万一敌人要查问,就说是伺候月子的。”
虽然也不是万全之策,可眼下出不了村,也只有如此了。胡兰点点头,她觉得这个主意还是不错的。
爱兰见姐姐要到金忠嫂家去,慌忙跑到街上去看情况。胡兰走出街门,她爹在地上蹲着抽烟,胡兰清楚爹是在为她望风。胡兰感激地望了一眼爹,也没说话,就准备走。她向街上望了望,街上到处是三三五五的阎匪军。有的端着枪,有的握着皮带,在敲打临街的门户,叫喊着,催屋里的人出去到庙上集合。
胡兰三步并成两步跑到了南场里,看到爱兰在墙豁口处向她招手,她连忙跑过去,一跃跳过豁口,见街上没有敌人,赶快奔到金忠嫂家。
金忠嫂家门环上挂着一块红布条,房门紧闭着。挂红布条这是一种民俗,表示这家女主人生了孩子,不得打扰。胡兰拍了拍窗棂,轻声问道:“金忠嫂,我进去行吗?”
屋里金忠嫂说:“是胡兰子吗?不要紧,进来吧!”
胡兰推门进去的时候,只见屋子里已有四五个人了,看来都是到这里来躲藏的。胡兰进来和金忠嫂问了几句孩子的事,这时又从门外跑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来。胡兰认得这是金忠的姐姐,她是嫁到大象的。她一进来就说道:“你看这不得好死的匪军,又召集开会了。昨天下午,他们在大象开会,用铡刀铡死了两个人,差点没把我吓死。我只说连夜跑回娘家躲几天,没想到逃出狼窝又落入了虎口。这些狗日的们又扑到这里来了。”
接着她就说大象铡人的事:昨天在大象铡的两个人,一个是曾在区政府当通讯员的贺二和;另一个是县游击队员牛二则。他两个都是南辛店人,因为身体不好,不能上山,在家休养。被复仇队的抓起来百般拷打,宁死不屈。这村地主石庆华害了噎食病,不知谁说吃了人血馒头就能治好,于是便找吕德芳给想办法。石庆华的儿媳妇是吕德芳的亲姐姐,为了弄到人血,所以吕德芳就决定杀了这两个人蘸人血。为了配合“自白转生”运动,这天下午,他强迫大象群众开会,在会上宣布了牛二则和贺二和的死刑。吕德芳用筷子扎着热气腾腾的馒头准备蘸人血,可是复仇队的那些人你推我靠,没一个敢出来用刀砍人头。吕德芳急了,看见旁边干草垛里搁着副铡草刀,便逼着复仇队的人一齐动手,用铡刀把两个革命战士给铡了。
金忠的姐姐讲着脸上失去了血色,听的人也害怕极了。她说:“像铡草一样铡人,哪见过那么狠毒的事,当场看的人都吓软了,有几个都吓瘫了。”
正说到这里,街上又响起了第二遍锣声,叫人们马上到观音庙上去开会。说是谁家要是还躲着不去,或隐藏外人,查出来立马处死。这一来,满屋子的妇女慌成一团,金忠的姐姐说:“就是死,我也不敢去开会了。我就在这里伺候月子。”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屋子里充满了恐惧气氛,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胡兰刚进来的时候,见有这么多人都想在这里躲藏,就觉得自己在这里不太合适,她想自己是区上的干部,万一敌人来搜查,那就会说她们隐藏共产党的干部,大家都会受到连累。刚才听到敌人三令五申地喊话,不准私藏外人,更觉得自己躲在这里不合适了。她见人们都不说话,就站起来说道:“金忠嫂,我走了,另外找个地方去。”说完抬脚就出了门。
只听金忠嫂不解地喊:“你——”
胡兰知道金忠嫂想留她,但情况紧急,于是她还是坚决地走了。
她想还是躲到双牛大娘家去,可是谁知道她从胡同走到街上的时候,这条街上已满是匪军,有的正挨家挨户搜查人,有的正赶着一群男女走过来。匪军们见到胡兰,不问青红皂白,挥着皮带吼叫道:“去开会,去开会!”胡兰意识到再也走不开了,只好从容地挤进了人群中,和大家一起朝观音庙走去。
当他们走到观音庙跟前的时候,只见庙前边的空场子上已站了好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场子四周站满了端着刺刀的匪军,护村堰上摆着两挺机关枪。一些穿着便衣的复仇队队员,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东瞅西看,不知他们在寻找什么。胡兰突然在人群中发现了爹、妈、和大娘,爱兰、大伯也被赶来了。她忙从人群中挤过去,站在自家人跟前,家里人看见她都很吃惊。妈妈低声问道:“你怎么也来了,匪军到你金忠嫂家搜查了?”
胡兰说:“躲在她家的人太多,万一查出来,我就会连累她们,我想换个地方,走到街上已经来不及了。”
爱兰拉着姐姐的手低声说:“姐,你站到爹后边来吧。”
正说着,有一个人分开人群,径直向胡兰这边走来,胡兰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人是金川子。金川子是大象的民兵,胡兰在大象土改见过他。
这时金川子已挤到她跟前,假惺惺地向胡兰说道:“胡兰,我跟你说点事。等一会儿,要开始‘自白转生’大会,到时候你上台去把给八路军办过的事都说说,说了就算‘自白’啦。”
胡兰没想到这家伙现在叛变了,竟然给地主当起了狗腿子,成了复仇队员。胡兰心里暗暗骂了一句:“狗叛徒!”接着狠狠瞪金川子一眼说:“我没什么可说的。”
金川子道:“反正你不说人家也都知道。识相点,不‘自白’就要乱棍处死,你听见没有,要乱棍处死!‘自白’了也就没事啦!你看看我,不是啥事也没有?!”
胡兰说:“我的骨头没那么下贱!”
金川子本来是奉命来劝胡兰的,他以为刘胡兰是个闺女家,也许先吓唬,再一劝就成了,自己也可以在吕德芳面前立一功,没想到一来就碰了一鼻子灰。这时胡兰把脸转向一边连看都不看他一眼,金川子就生气了,恼羞成怒地说:“咱们认识,看在熟人的面子上,所以我来给你透个信!不识好人心。哼!等着瞅吧,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说完气冲冲地从人堆里挤出去,跑到观音庙里去了。
匪军不断把村里的人三三五五地赶到这里来,把抱着娃娃吃奶的妇女、拄着拐杖的老太太都赶来了。躲在金忠嫂家的几个女人也一个不少都被赶来了。
正在这时,人群中忽然传来号啕大哭声,附近有人低声惊叫道:“呀!金香。”
胡兰抬头看了看,只见复仇队员白占林和温乐德,一人扯着金香的领口,一人拉着金香的胳膊,从人群中拉出去了。这两人胡兰都认识:白占林是大象的小流氓,温乐德也是个叛变了的民兵。他们叫骂着把金香一直拉到观音庙上去了。金香妈李薏芳披头散发,跟在后边哭喊着扑到庙门口,一到门口就被站岗的匪军给拦住了。她就趴在庙门口不住声地号哭起来。胡兰见金香妈在敌人面前号哭,心里就怨她,心想:在日本鬼子面前那骨气哪里去了!
胡兰家里人看到敌人抓走金香,知道敌人也一定会来抓胡兰。一个个又是担心又是怕,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但又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们自觉地围成一个圈,把胡兰围在家人中间。这时,胡兰妈胡文秀忽然觉得胡兰两手在鼓捣什么,低头一看,只见女儿手上拿着一张手巾,在翻来覆去地细看,接着又慢腾腾脱下手上的银戒指,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清凉油盒子。胡兰把这三件小东西一件件拿在眼前细看,看看这件,又看看那件。胡文秀不明白,在这么紧急的关头,胡兰怎么玩起这些东西。
其实胡文秀哪里知道,这三件不值钱的小东西,都是胡兰宝贵的纪念品。
那张小手巾是王根固临别时送给她的信物,虽然,一年多了胡兰没见过王根固一眼,但每每在她心闲的时候,或是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她总要拿出那张象征他们爱情的手巾看个够,每当她看到手巾,仿佛王根固就在她面前,他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此时此刻胡兰在想: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王根固了,手巾是他俩爱情的见证。清凉油盒子是她的入党介绍人石世芳送给她的,虽然清凉油早用完了,可她舍不得把这个盒子扔掉,特别是世芳叔生着病转移到山上以后,她更觉得这是一件纪念品了。而戒指是奶奶临终前给她戴上的,虽然奶奶没有少说她,但是奶奶教她纺线织布,教给了她勤俭节约的好作风,一个小小的戒指包含了多少世间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