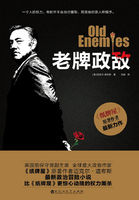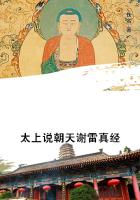1830年1月3日,星期日
(伏尔泰等人的影响;《浮士德》非同寻常,仅凭理智无法索解)
歌德给我看1830年英文袖珍本的《纪念年历》,里面印有一些精美的铜版画,以及拜伦爵士几封极有趣的信函;我像享用餐后甜点似的读了它们。歌德自己则拿起杰拉新出版的《浮士德》法译本来翻阅, 有时还像在朗读的样子。
“想到这本书还以五十年前伏尔泰统治的法语流行于世,”歌德开口道,“我不禁浮想联翩,不胜惊叹。你没法想象我心中有怎样的感想,对伏尔泰及其伟大的同时代人的意义毫无了解,不知道他们曾经如何主宰了整个精神世界。我的自传没讲清楚,这些法国人如何影响了我的青年时代,以及我费多大的劲儿去摆脱他们的影响,以便能够自立自主,并且端正我本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们还谈了伏尔泰的另一些事情。歌德给我背诵了《系统》这首诗;我由此可以看出,他在青年时代必定很认真地钻研过这类作品,把它们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上述杰拉的译本尽管大部分是散文,歌德仍称赞它很成功。他道:
“德文的《浮士德》我已不爱再读;然而在法译本里,一切又令人感到极其新鲜,极其富有朝气和睿智。
“《浮士德》可是不寻常啊,”歌德继续说,“一切试图凭理智去靠近它的努力统统白费。必须考虑到,它的第一部乃是产生自个人的某种蒙昧状态。可正是这蒙昧刺激了人类,吸引他们不断力求索解,就像人类曾为所有无法解答的问题费尽心机一样。”
1830年1月10日,星期日
(关于《浮士德》中的“众母”)
今天饭后歌德给我朗诵浮士德去寻找众母那一场,让我获得了巨大的精神享受。
情节的新颖和出人意料,还有歌德朗诵的方式和技巧,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觉得已经身临其境,像浮士德一样在听靡非斯托讲述时也不寒而栗。
故事情节我听清楚了,也体会到了,但却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因此忍不住想请歌德给解释一下。他呢,跟一贯似的显得很神秘,只是睁大两眼盯着我,嘴里对我重复着:
“众母!众母!—— 听起来好生奇怪的!”
“别的我不能再向你透露什么,”他接着说,“只能告诉你,我曾经在普鲁塔克的著作里发现,在古希腊有把众母视为神灵的传说。这就是我从传统借用的全部东西,其他统统为我自己发明创造。我把手稿借给你带回家去,认真地读完它,看能不能找到谜底。”
回到家我静下心来反复研读那奇妙的一幕,感到非常幸福,并对众母的本质和作用,对她们的环境和居所,产生了如下的看法。
设若地球这个巨大的天体内部是空的,因此朝每一个方向都可以自由运动几百英里而不撞上什么物体,那么这就可能成为浮士德下去寻找的那些无名女神的居留之所。她们仿佛就生活在一切地域之外,因为在她们近旁没有任何物体;也生活在时间之外,因为没有任何星辰在她们头顶上照耀和升起落下,示意她们昼夜的轮回交替。
众母就这样坚持在永恒的晦冥和寂寥中,成为一群积极创造者的存在,她们本是创造与坚持的法则,地球表面一切有形体和生命的东西都源自她们。一旦生命停止了呼吸,就会变成精神回到她们那儿,她们于是将它保存起来,直至它再获得机会成为新的存在。在众母居所这茫茫无际的空间,一切曾经存在和将会存在的生命的灵魂和形态,都像云似的围绕着她们飘来飘去;也就是说,魔法师用法术控制了一个生命的肉体或者想让过去存在的生命还魂,都必须去到她们的王国里。
也就是说,尘世生命永恒的变异,诞生与发育、破坏与重构,便是众母永不停息终止的作为。地球上所有通过繁殖而获得新生命的过程,都是母性起主要作用,所以也有理由想象那些职司创造的神灵乃是母性的,故而尊称她们为众母便不是没有道理。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文学创作;只不过人的生活过于狭隘,不可能钻得太深走得太远,一旦有点儿什么发现,便心安理得,心满意足。我们在尘世看见一些现象,感受到一些影响,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将去向何处。我们总是把一切归结为一个精神源泉,归结为一个神灵,对这个神灵我们不甚了了,完全描绘不出他的形象,可我们不得不把他从天上拽下来,把他想象成人类的样子,为的就是使我们模糊迷茫的预感获得几分体现,变成稍许可以把握的存在。
这样,便产生了所有在各民族中代代相传的神话传说;同样地,歌德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神话。这个神话看上去至少相当地符合自然界的真实,故而也该足以与历来凭想象所创造的最佳神话媲美。
1830年1月24日,星期日
(回忆伯里施;关于《浮士德》第二部的写作)
“最近两天我收到了一封信,”歌德说,“是咱们在施托恩海姆那位著名的采盐专家写来的;信的开头很有意思,我必须讲给你听。”
“‘我得到了一个经验,’他写道,‘一个叫我终生难忘的经验。’可如此开头之后会是什么呢?是一件说小不小,至少让我们损失了一千银币的事故。那个钻了两百英尺深的土层和岩石才弄出来的矿井,他却掉以轻心没在两边加上撑子,结果松软的土壁垮塌下来,坑道里满是烂泥,要想把它清理出来现在就得花很多钱再施工。随后还得再铺一千二百英尺的金属管道下去,以防再出现类似的事故。他早就该这样做,而且也肯定这样做了,如果这种人不是那么勇敢,勇敢得叫人简直无法理解;可是也必须这样勇敢,否则便做不出如此冒险的事情。谁知道出了事故他却绝对跟个无事人似的,完全是心安理得地写什么:‘我得到了一个经验,一个叫我终生难忘的经验。’不过呢我还是要称他为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一点没抱怨又立刻干起来了,永远不会被困难吓倒。你觉得怎样,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让我想起了施特纳,”我回答,“他老抱怨,他没有很理智地利用自己的病患。”
“是有点类似。”歌德说。
“我还忍不住想到伯里施,”我继续说,“想到他教训你什么叫经验——这几天我正好又在读这一章,觉得挺开心——,说什么:‘经验嘛就是你知道你经历了你原本不想经历的事情喽。’”
“可不是嘛,”歌德笑道,“都是些老玩笑,当时我们就这么样糟蹋掉自己的时间!”
“伯里施看样子是个蛮风趣、蛮潇洒的人,”我继续说。“想想他在地窖酒馆开的那个玩笑多有意思,那晚上他想阻止一个年轻人去赴自己心上人的约会,用的手段就再滑稽不过:他把挂在身上的佩剑一会儿颠过来,一会儿倒过去,引得所有人哄堂大笑,结果那小伙子也就忘记了约会的时间。”
“是啊,”歌德说,“挺有意思;要是搬上舞台会成为极其风趣的一幕,正如伯里施其人整个儿就不啻为剧中的一个好角色。”
接着我们继续说说笑笑,又重温了歌德在自传《诗与真》里讲述的所有伯里施的奇言异行。例如他酷爱灰色的穿戴,丝绸、平绒、毛呢都一律的灰色,搭配起来只显出一点点色调的偏差而已;还有他如何煞费苦心,为的只是再给身上添加一点儿新的灰色。还有他如何写诗,如何嘲笑排字工人,同时却突出强调抄写者的尊严和品位。还讲到他最心爱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斜躺在窗台上打望来往的路人,在想象中随意改换人家的穿戴,以这种方式把他们一个个变得笑人得要命。
“还有他总喜欢跟邮差开的那个玩笑,”歌德说,“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也挺有趣?”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回答,“您的《自传》只字未提。”
“有意思极啦!”歌德说。“那我就给你讲吧。
“我和伯里施一起躺在窗口,他看见邮差从街上走来,走了一家又一家,他便像往常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钱来,放到自己身边的窗台上。‘瞧见那个邮差了吗?’他转过头来问我,‘他越走越近,马上就要上楼来了,我一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他拿着一封给你的信,怎样的信呢?不一般的信,一封装着支票的信,——一张支票!多大的支票,我不想说。——你瞧,现在他进来了。没有!不过他马上会进来。快看他又在那儿。这下!——来呀,进来呀,老朋友!进这屋来呀!——他走过去了!真愚蠢!真是个蠢货!一个人怎么能够如此愚蠢,如此不负责任呢!双重的不负责任:对你不负责任,没把他攥在手里那张给你的支票送过来;对他自己更是完全不负责任,我已经为他准备好一枚铜钱,他竟硬是不来拿,害我又得收回去。’就这样,他边说边气派十足地把那枚铜钱放回口袋,我们呢也有一阵好笑的。”
我欣赏这个玩笑,跟其他玩笑相比它毫不逊色。我问歌德,他是不是以后再不曾见过伯里施。
“我再见过他,”歌德回答,“而且在我刚到魏玛不久,大概是1776年,当时我陪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到德骚去,伯里施也已经离开莱比锡,应聘当了德骚王太子的太傅。我发现他完全是老样子,身为宫廷显贵仍不改幽默的本性。”
“你时隔不久便名满天下,他有没有说什么?”我问。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告诉过你吗?你当时不出版你的诗集,一定要等到完成了杰作才付印,不是很聪明吗?诚然,你当时的那些诗也不差,否则我就不会替你抄写啦。可如果咱们没有分手,那我也不会让你出版你另外的东西,我也会替你抄写它们,这样子照样会非常好。’你瞧,他还是老样子不是。他待在宫里很不自在,我总是到了宴会上才见到他。”
“1801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已经老了,但仍旧未改乐天的性格。他住着宫里几间非常豪华的房间,其中的一间却摆满了天竺葵,那年头儿人们都特别热衷种植这玩意儿。可是这时植物学家又在天竺葵中分出来一些个亚类,并把其中的一类取了个学名叫鹳嘴子葵。这一来老先生可不乐意啦,大骂植物学家:‘这帮子蠢货!我想我已把整个屋子种满天竺葵了,他们却跑来讲这是什么鹳嘴子葵。如果不是天竺葵,我种它干吗呀;我拿鹳嘴子葵有啥用!’就这么一次次地骂上半个钟头,你看见了,本性未改,完全还是从前的伯里施。”
随后我们谈到《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几天前歌德给我朗诵了《浮士德》这一场的开头,他说:
“想挤进来的神话人物多得数不过来;可我得谨慎行事,只收留那些形象鲜明、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现在浮士德跟马人希隆在一起,我希望这一场写得不错。只要我保持勤奋状态,过几个月就完成了《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现在可是再没有什么能使我丢下《浮士德》了;我要能活到完成这部作品,那真是棒极啦!现在第五幕差不多已经脱稿,接下来第四幕也就顺理成章,不会再费多少周折。”
接着歌德谈到他的健康,夸赞自己身体一直很好,是个幸福的人。他说:
“我之所以现在这么健康,得感谢佛格尔大夫,没有他我恐怕早就没了。佛格尔天生做大夫的料,而且是我见过的最具天才的人物之一。不过咱们别讲他多么多么好,免得他让别人给抢去了。”
1830年1月31日,星期日
(数字与世界管理)
在歌德家进餐。我们谈起弥尔顿,歌德说:
“不久前,我读过他的《力士参孙》,这部戏比近代任何一位诗人的其他作品都更符合古希腊人的精神。它非常之伟大;而作者本人也失明了,正好就帮助他把参孙的处境描绘得异常真实。弥尔顿确实是位了不起的诗人,对他我们必须怀有充分的尊敬。”
送来了各式各样的报纸。我们阅读柏林戏剧新闻,得知那儿上演了一出有海怪和鲸鱼的戏。
在法国《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歌德读到英国的神职人员薪酬奇高,数量竟超过了余下的整个基督教教会人士薪金的总和。歌德说:
“有人曾经断言,世界将用数字来管理;这下我可知道数字也会告诉我们,世界是管理得好或是不好。”
(歌德作品的版本、手稿和自绘插图)
陪魏玛大公爵的公子拜访歌德,他在书房里接待了我们。
我们谈到歌德著作的各种版本,听见他说大部分的版本他自己并未收藏,我很是感觉诧异。他讲甚至连《罗马狂欢节》的第一版也没有;而这一版里,还印了他亲自作的铜刻原版插图。他讲,在一次拍卖会上,他曾出价六个银币竞拍这个本子,然而没有拍到。
随后他给我们看《葛慈·封·伯利欣根》的初稿,完全是五十多年前他在妹妹的怂恿下,用几个星期写成的那个老样子。秀丽的笔触已显得如此地清朗、潇洒,他后来的德文书法一直没有变样,现在也没变样。手稿干干净净,读了许多页也不见丝毫涂改,使人更愿意当它是誊清过的,而不相信真是匆匆草写成的初稿。
据歌德告诉我们,他最初的作品全都是自己亲笔写成,《少年维特的烦恼》也一样,只可惜手稿已经丢了。相反后期的所有作品几乎全为口授;只有诗歌和匆匆记录下来的提纲,还留有他的笔迹。他经常想不到让人为自己的新作留一个抄件;相反常常把自己唯一拥有的稿本送去斯图加特付印,不怕自己最珍贵的作品偶然发生意外。
等我们欣赏够了《伯利欣根》的稿本,歌德又给我们看《意大利游记》的原稿。在这观察和感想的逐日记录中,我们发现仍保持了《葛慈·封·伯利欣根》的优美书法风格。整个显得坚定、沉稳、自信,没有一点涂改,可以看出,作者对所要记录的细节时刻都做到了心知肚明。没有什么变来变去,除了稿纸;稿纸是这位旅行者走到哪儿哪儿买,所以规格和颜色总在变。
在稿本的末尾,有一幅歌德随手画的钢笔画挺有意思;画的是一位穿着宽袍大袖的公务服的意大利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这老兄真是说多么逗有多么逗,他挑选的那身制服如此打眼,叫人以为他原本是要去参加化装舞会。然而一切却都是现实生活的忠实描绘。只见胖胖的演说家随意舒适地站在那儿,食指掐着拇指尖儿,伸直了其他指头儿;就这么一点动作配合他头顶着的大假发,真正叫恰到好处。
1830年2月3日,星期三
(谈到儿时的莫扎特)
在歌德家进餐。谈到了莫扎特,歌德说:
“我看见他时他还是个七岁的孩子。他途经法兰克福,开了一个音乐会。我自己差不多十四岁;他头戴假发,腰悬佩剑,一副小大人样子,我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张大了眼睛;听歌德讲他差不多长大了还看见莫扎特是个孩子,在我简直像个奇迹。
1830年2月7日,星期日
(普里马斯侯爵)
在歌德家用餐。谈了谈普里马斯侯爵;歌德说在奥地利皇后的一次宴会上,他曾不揣冒昧,为维护这位侯爵说了一句机智聪明的话。侯爵对哲学似懂非懂,绘画也是个缺少品位的半吊子,他送给郭勒小姐那幅画就是证明。他心地善良、软弱,散尽了家财,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谈了免责(Desobligeanten)一词的含义。
饭后小歌德领着儿子瓦尔特和沃尔夫走进来,他已装扮成克林索尔 ,准备好了到宫里去。
1830年2月10日,星期三
(再谈《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拿破仑的穿着)
陪歌德进餐。他真心实意地称赞里默尔为二月二号的庆典创作的贺诗。他说:
“总而言之,里默尔这人不管干什么,都拿得出手,都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