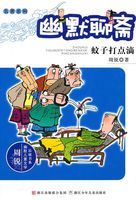1829年12月16日,星期三
(歌德解说《浮士德》中的人造人;古典风格与浪漫风格)
今天饭后歌德给我念《浮士德》的第二幕第二场,也就是靡非斯托去找瓦格纳,发现他正在实验室里用化学方法造人。实验成功了,烧瓶里出现了一个发光的小人荷蒙库鲁斯,并且立刻开始活动。瓦格纳对一些自己不理解的事情提出了问题,靡非斯托却拒绝回答,说什么他才不爱废话连篇喽,他只想行动,他迫切需要关心的是咱们眼下人事不省的主人公,他急需他的帮助。对于荷蒙库鲁斯这个人造生命来说,现实如同透明似的一清二楚,他窥见了酣睡中的浮士德的内心,发现他正做着一个幸福的美梦,梦见丽达正在一个风光秀丽的地方沐浴,突然天鹅却来与她幽会。荷蒙库鲁斯一说出这个梦,我们心里便显现出那极其迷人的情景。靡非斯托却什么也看不见,荷蒙库鲁斯于是嘲笑他,说都怪他是个北方的魔鬼。
“总的来说,”歌德道,“你会发现跟荷蒙库鲁斯相比,靡非斯托处于不利的地位,荷蒙库鲁斯在头脑清醒这点上与他旗鼓相当,但通过对美和善的追求却又远远胜过了他。还有他称他为亲爱的表弟;对嘛,像荷蒙库鲁斯似的精神的产物,他由于还没有完全变成人而未受到蒙昧和局限,可以算做灵魔一类,如此一来他俩之间就确实存在某种亲缘关系。”
“确实,”我说,“在这里靡非斯托显得是要低一个档次;只是我忍不住要想,他在荷蒙库鲁斯的产生过程中也暗中起了作用,正如我们迄今对他的了解,还有在出现海伦的那几场他都总是充当暗中起作用的角色。这样,他的地位在总体上又得到提升,在个别问题上也就可以心安理得一些了。”
“你对他的处境体会得很准确,”歌德说,“是这个样子,我也考虑过是不是在靡非斯托去找瓦格纳,看见荷蒙库鲁斯正在形成时让他念几句诗,以表明他的参与其事,也让读者心里有个谱。”
“这样做没有妨碍,”我说,“更何况也已经暗示出来了,通过落幕前靡非斯托的那句:
搞来搞去还是得依靠
咱们自己的小小创造。”
“你说得对,”歌德接过话头,“对于细心的人这差不多已经够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再加几句诗。”
“不过,”我应道,“结尾的那句非常棒,很难设想可以没有。”
“我想啊,”歌德说,“它够捉摸人一阵子的。好比一个父亲养了六个儿子,不管他怎么做,都注定落不下好。还有国王和大臣们,他们提拔了许多的人列位高权重的职务上,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想象出一点个中的意味。”
浮士德梦见丽达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以我心灵的体会,这应该是关系全局的极为重要的一笔。
“真是奇妙,”我说,“在这样一部作品里边,各个部分之间怎么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提高。通过这第二场的浮士德梦见丽达,后边的海伦那场才获得了真正的基础。在那里一再地提到天鹅和天鹅生的女儿,可这里却出现了那个情节本身;以后再带着对它的实感去看海伦那场戏,一切便豁然开朗、切实完整啦!”
歌德承认我说得对,看样子挺高兴我有此见识。他说:
“你还会发现,在前面这些场已经常响起古典和浪漫的音调,也经常提及古典和浪漫时期的人和事;这样,就好像筑了一层层阶梯,好让人走上去见海伦;在那儿两种文学风格都充分得以展现,并得到平衡和谐。”
“现在法国人也开始正确理解这些关系了,”歌德继续说,“‘一切都很好,很协调,’他们说,‘古典的就像浪漫的,问题只在于要懂得使用这些风格,善于驾驭这些形式。你也可以把两种都同时用得很糟糕,这种不像样子,那种也差不离。’我想,他们讲得有理,说得不错,这样就可以安静一阵子了。”
1829年12月20日,星期天
(文艺家成功的三个条件;如何理解和表现《浮士德》的寓意形象)
在歌德家进餐。谈到首相,我问歌德,首相旅居意大利归来有没有带给他曼佐尼的消息。歌德回答:
“他写信给我谈起了曼佐尼。首相去拜访过他,他住在米兰附近的庄园里,令我遗憾的是他身体一直不大好。”
“很奇怪,”我说,“杰出的天才人物特别是诗人,我发现他们往往都体质衰弱。”
“这种人之所以成就突出,”歌德说,“前提条件就是体质柔弱,这样才多愁善感,能够聆听到天籁之声。可如此身体素质在与社会和自然的冲突中又容易受到伤害,谁要不像伏尔泰似的既极度敏感又异常坚忍,就容易让疾病缠身。席勒也老是病恹恹的。我刚认识他时,以为他最多只能活四个礼拜。可他也具有一定的韧性;他还活了许多年,如果生活方式健康,可能会活得更久。”
话题转到戏剧,具体讲的是某次演出是否成功。歌德说:
“我看了温泽尔曼扮演的这个角色,他总是叫人看着觉得舒服,具体讲总是让人体会到那样一种精神的极度自由轻松。要知道表演艺术也跟其他所有艺术一样。演员做什么都处于一种情绪,他的作为和表演将我们带入同样的情绪。艺术家的情绪轻松自如,我们也轻松自如,反之他如果压抑拘谨,也就使我们也忧心忡忡。艺术家这种轻松自如通常都来自他对自己的事情胜任愉快,例如我们在欣赏尼德兰的油画时心情是那么轻松愉快,原因就在艺术家们表现的是自己身边的生活,对题材完全驾驭自如。一个演员要让我们感到精神轻松自由,那他就必须学习并且发挥想象力和自身的天赋以便充分驾驭角色;为此他必须使出自己浑身解数,调动自己所有的身体手段;还有他必须具备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精力充沛。缺乏想象力,仅仅学习是不够的;学习加上想象力,没有天赋仍然不够。女性大多数靠自身的想象力和性格气质取得成功,沃尔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继续着这一话题,便谈到曾经活跃在魏玛舞台上那些最出色的演员,对其中出类拔萃的几位更是称赞有加,念念不忘。
说话间我又想起《浮士德》,想起荷蒙库鲁斯,想到了最好怎样在舞台上表现这样一个形象。我说:
“即使不能使观众看见这个小人儿本身,也要让人看见烧瓶中的那点亮光。还有,该他说的重要台词,也要念得跟一个小孩不可能念的那个样子。”
“瓦格纳不能够放下手中的烧瓶,”歌德说,“因此声音必须像是从瓶子里传出来的。这个角色适合一位腹语艺术家担任;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位的表演,他肯定能很好造成不在现场的印象。”
我也想起狂欢节上的类似表演,觉得不妨尽可能地再现在舞台上。我说:
“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就像那不勒斯的年市吧。”
“那就需要一座很大很大的剧场,”歌德说,“几乎没法想象。”
“我仍然希望经历这样一次演出,”我回答,“我特别喜欢由智慧牵着的那头大象,胜利女神高高地站在它背上,疑惧和希望让铁链拴着走在它两边。这可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寓意场景啊。”
“可它并非登台的第一头大象,”歌德说,“在巴黎,曾有头大象演过一个完整的角色。一群土著人带它上来,它摘掉国王的王冠,然后给他戴上一顶新的;这肯定很棒不是。随后,在演出结尾,大象又给叫了出来,完全是独自出场向观众行礼,行完礼才又退了回去。你瞧,这就是说,咱们的狂欢节也可以这么派大象的用场。不过呢,整个场面是太大了,要求有的是一位不容易有的导演。”
“可是会异彩纷呈,效果空前,”我说,“任何剧院都不肯轻易放过这个机会。效果是怎么一步步产生,出场的人物如何越来越显赫啊!首先上场的是漂亮的男女园丁,他们既装点了舞台,又充当群众,这样接着登台的越来越重要的人物就不缺少环境和观众。随后出来的是大象,大象之后,从云雾缭绕的背景中,又见一辆龙驹宝辇飘过头顶。再往后是伟大的帕恩登场,最后则一切全让虚幻的烈火团团包围,得等到茫茫大雾和雨云终于从天而降,将烈火熄灭!这一切要是都能像您想的那样表现出来,那观众必定惊讶得目瞪口呆,不知道怎样来吸收消化眼前这么丰富的印象才是啊。”
“别说啦,”歌德道,“别提观众,我不想听到他们。重要的是把作品写出来摆在那里,世人爱拿它怎么办怎么办好了,能怎么利用它怎么利用它好了。”
随后我们谈到驾车童子。歌德问:
“浮士德装扮成了财神普路托斯,靡非斯托戴着吝啬的面具,你肯定注意到了。可谁又扮这个驾车童子呢?”
我犹豫不决,不知怎么回答。
“他是欧福良啊!”歌德说。
“他怎么可能出现在狂欢队伍里呢?”我问。“他可是在第三幕才诞生呀!”
“欧福良不是人类,”歌德回答,“而只是一个寓意形象。他象征文学,不受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和任何个人的限定。后来由他体现的同一个精神,现在表现为了驾车童子;在这点上他就如同无所不在的幽灵,随时随地可以被召唤出来。”
1829年12月27日,星期天
(靡非斯托发明纸币与普鲁士印行钞票)
今天饭后歌德给我念靡非斯托为皇帝造纸币一场。
“你想得起吧,”歌德说,“前边的帝国会议得出的结论是缺少金钱,靡非斯托答应帮助弄钱来。这个主题随后一直贯穿在狂欢的化装游行中,靡非斯托安排装扮成大帕恩的皇帝在一张纸上签了名,这张纸因此提高身价变成了钱,经过大量复制后流传开来。
“到了这一场皇帝又提起此事,自己却不知道他干了什么。财政大臣给皇帝一些钞票并说明了原委。皇帝一开始勃然大怒,在进一步看清发纸币的好处后却喜不自胜,用新印制的票子大大赏赐了身边的群臣,在下场时还随手扔下了几千克朗,立刻被胖小丑收集起来,准备把这些纸头儿变成田产。”
听着歌德精彩的朗诵,我欣喜地悟出,歌德让靡非斯托发明纸币真叫奇思妙想,神来之笔,如此这般,就联系上了时下世人主要关心的事,使其有了永恒的意义。
朗诵刚刚结束,才讨论不多几句,歌德的儿子就下楼来跟我们坐在了一起。他给我们讲他读了库珀的最后一本小说,并绘声绘色地复述了故事梗概。我们只字未提刚才朗诵的《浮士德》那一场,他自己却很快开始大谈特谈普鲁士发行钞票的事,还讲人们愿意超值兑换它。任随小歌德自己讲去,我和他父亲却相视发出会心的微笑:没想到剧中的情节竟如此地合时宜。
1829年12月30日,星期三
(歌德朗诵帕里斯和海伦现形一场)
今天饭后歌德继续给我念《浮士德》。他说:
“皇宫里的人们发财以后就想找找乐子。皇帝希望看看帕里斯和海伦,具体讲就是要通过魔法让他俩现形。然而靡非斯托跟古希腊世界风马牛不相及,无力支配这些神话人物,于是任务自然落在了浮士德肩上,浮士德也会圆满成功。可要使现形成为可能,浮士德必须做的事现在还没完成,下次我再接着给你念这一节。可在此之前,让你先听听帕里斯和海伦现形本身这段。”
我沉浸在幸福的企盼里,歌德开始朗诵。在古老的骑士厅中,我看见皇帝和大臣们纷纷走进来,为了一睹现形的奇迹。大幕升起了,眼前出现一座剧院,一座古希腊神庙。靡非斯托藏身在提词箱里,舞台上一边站着星象家,浮士德手捧着一只三脚香炉从另一边登上台来。他念了必须念的咒语,只见从香炉袅袅腾起的烟雾中,帕里斯慢慢地显现了出来。美少年一举一动都伴着妙曼的音乐,一如浮士德在一旁作的解说。他坐下来,他靠向椅背,他把一条胳臂弯在头上,就跟我们在古代美术作品中看见的造型。妇女们一见他都无比欣喜,都夸赞他的青春魅力;男人们却恨透了他,都心生嫉妒,都拼命贬低他。帕里斯睡着了,海伦随之出现。她走近酣睡者,吻了吻他的嘴唇;她离开他走了,在转身之际又回头望了望他。就是这一回眸尽显了她非凡的魅力。她迷住了男人们,正像帕里斯迷住了女人们。男人们心中燃起了爱火和赞颂,女人们心中燃起的是妒忌、仇恨和责难。目睹这自己招来的美人儿,浮士德整个儿心驰神往,忘乎所以,忘记了自己所处的时间、地点和场合,害得靡非斯托不断地提醒他:别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在帕里斯和海伦之间倾慕和默契似乎不断增多,小伙子抱住了她,想把她掳走;浮士德却想从帕里斯的怀抱里拖出她来,谁知他一将钥匙冲着美少年,便发出一声剧烈的爆炸,幽灵们烟消云散,浮士德则不省人事地倒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