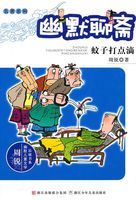接着,我们就颜色学研究这个话题谈了很多。
下莱茵地区寄的箱子到了,东西全取出来摆在了桌子上:考古发掘的古陶罐,矿物标本,教堂中的小画板,狂欢节的诗歌。
1829年2月17日,星期二
(印度哲学与德国哲学)
谈了不少《大科夫塔》这出喜剧的问题。歌德说:
“拉瓦特尔相信卡略斯特罗和他的奇迹。别人揭发他是个骗子,拉瓦特尔却声称此人才真是骗子,而创造奇迹的那个卡略斯特罗乃是一位圣人。
“拉瓦特尔这人心地善良,然而犯了许多大错误;追求严格意义上的真理不是他的事儿,他老是自欺欺人。因此我跟他彻底决裂了。最后我还在苏黎世见过他,但却没有让他看见。我乔装打扮后漫步在一条林荫大道上,看见他迎面朝我走来,便避到了道路外侧,他跟我擦身而过,却没有认出我。他走起路来像一只鹭鸶,因此便以鹭鸶的形象出现在了布罗肯山上。”
我问歌德,拉瓦特尔是不是有亲近自然的倾向,就跟他的《面相学》可能让人得出的结论那样。
“才不呐,”歌德回答,“他只倾心于伦理和宗教。拉瓦特尔的《面相学》讲到动物颅骨的部分,是从这儿贩卖去的。”
话题转到了法国人,转到了基佐、维耶曼和库辛等人讲的课。歌德十分推崇这三个人看问题的立场,称赞他们以一种自由的和新的观点审视一切,讲什么都单刀直入,有的放矢。他道:
“好比去逛一座花园,迄今人们都要走很多弯路,绕很多圈子才进得去;现在可好,这些人大胆又自由,干脆给围墙拆出一个口子,开上一道门,让人一进门立刻就到了园内最宽敞的大路上。”
从库辛又谈到印度哲学。歌德说:
“如果英国人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这个哲学就根本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相反倒是我们大家已经经历过的那些时代的重复。整个孩提时代,我们都是感官主义者;等到恋爱了,我们便把恋爱对象原本没有的品质加到人家身上,于是变成了理想主义者;随后爱情发生动摇,我们怀疑对方的忠诚,于是又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怀疑论者。余生已无足轻重,于是得过且过,我们最终转向了清静无为,就跟印度的哲人们一个样。
“咱们德国哲学还有两件大事要做。康德已经写成《纯粹理性批判》,建树大而且多,可是圆圈尚未画完整。现在必须有一位能人,有一位伟人,来写一部《感性和人的知解力批判》。此事要是很快取得成功,那我们德国哲学就没有多少遗憾了。
“黑格尔在《柏林年鉴》写了一篇关于哈曼的书评,”歌德继续说,“近些日子我反反复复读它,对它不能不大加赞赏。作为批评家,黑格尔确实很有眼光。
“维耶曼看问题同样站得很高。法国人尽管再也见不得堪与伏尔泰比肩的天才,但对维耶曼则可以说,他精神的立足点高过伏尔泰,因此可以对伏尔泰的优缺点进行评判。”
1829年2月18日,星期三
(梅尔克多才多艺,酷好艺术收藏)
我们讨论颜色学,其中谈到玻璃杯上那些不透明的花饰,它们在对着亮光时呈黄色,在对着暗处时呈蓝色,这样就让人观察到一个颜色产生的元现象。歌德就此说道:
“面对这个现象,通常人充其量只是感到惊讶;他惊讶之后便心满意足,不会有更多的想法,不会去追寻现象背后更进一步的东西;这便是极限。但是,也有些人目睹了一个元现象总觉得还不够,他们想,必须再看看;这时他们就像一些小孩,照了镜子会立刻把它转过去,看看背后是否藏着什么。”
谈话涉及到了梅尔克,我问梅尔克是否也从事自然研究。歌德回答:
“是的,他甚至有不少用于自然史研究的重要收藏。梅尔克原本多才多艺。他也痴迷于美术,迷得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发现一件佳作落到了一个他认为不懂得珍惜艺术的庸人手里,他即使倾家荡产都要搞过来,把它收入自己的藏品。干这种事情他一点不讲良知,不择手段,在没有其他办法时甚至不耻于明目张胆地进行欺骗。”
歌德举了几个有趣的例子。
“再不会诞生像梅尔克这样的人啦。”歌德继续说,“即使诞生,世界也会把他教成另外一个样子。那真是一个好时代呀,我和梅尔克年轻的时候。德国文学还是一张白纸,可以尽情地在上面绘许许多多好图画。现在它已经画得不成样子,已经遭到玷污,看着就叫人不高兴,连聪明人也不知道哪儿还可以下笔。”
1829年2月19日,星期四
(歌德痴迷于颜色学,容不得别人有异议)
和歌德单独在他的书房里进餐。——他情绪极佳,对我讲白天他遇见的一些高兴事,其中包括跟阿塔利亚和宫里成功地做成了一笔交易。
随后谈了很久《哀格蒙特》,谈了头天晚上根据席勒剧本加工的本子演出的情况;并且提到由于这次改编弄巧成拙,让剧本蒙受了一些损失。
“删掉了女君主这个人物,”我说,“从哪方面看都不对劲儿;对这出戏来说,她绝对必要。由于这位女君主的存在,不只是整个剧的性质和品位得到了提高,还有它的政治背景,尤其是跟西班牙宫廷有关的情况,也通过她跟马夏威尔的对话清清楚楚地突现了出来。”
“毫无疑问啊,”歌德说,“而且这位女君主的青睐也增加了哀格蒙特的光彩和身价,还有克蕾尔欣的形象也显得高大起来,因为我们看见她甚至战胜一帮子贵妇人,独占了哀格蒙特的爱情。所有这些都是极微妙而敏感的戏剧效果,损害它们自然不会不冒影响全剧的危险。”
“我还觉得,”我说,“有那么多重要的男性角色,女性角色仅仅克蕾尔欣一个似乎太弱啦,有些受压抑的样子。可多一个女君主,整个画面就变得平衡一些。光在剧中提到她意义不大,她自己上台才能给观众留下印象。”
“你的感觉很对,”歌德说,“当初写这个剧本,你可以想象,一切我都精心掂量过的;因此毫不奇怪,硬砍掉一个主要人物,一个着眼于全剧、支撑着全剧的人物,整个演出效果会受多大的损失。然而席勒生性倔犟,行事经常会固执己见,对所处理的对象缺少足够的尊重。”
“大家可能会骂您哟,”我说,“您竟逆来顺受,在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无条件地迁就了他。”
“我常常是太无所谓了,”歌德回答,“加之当时我正忙于别的一些事情。对公演《哀格蒙特》的事我兴趣不大,就随他去了。现在我至少有了一点安慰:剧本印出来摆在这里了,也会有一些剧院足够理智,将忠实地,不加删节地,原原本本地排演它。”
歌德随后问起了颜色学的问题,问我对他要我写一篇颜色学纲要的建议有没有进一步考虑。我向他讲了实际情况,想不到却因此与他产生了分歧。鉴于这件事的重要性,现在想再给读者报告一下。
谁要作过观察,就回忆得起:在晴朗的冬天出太阳的时候,雪地上的阴影常常看上去都是蓝色的。在他的《颜色学》中,歌德把这种现象归之于主观的现象一类,根据就是我们没住在高山顶上,射向我们的日光并非绝对的白颜色,而是穿过一片多多少少都雾气弥漫的大气层,再到达地上时便呈淡黄色;也就是说阳光照射下的雪地不完全是白色的,而是表面上染成了淡黄色,我们的眼睛却受其刺激,产生了与之相反的蓝色的印象。这样在雪地上被看成了蓝色的阴影,因此是一种索取到的颜色,歌德就以此为标题,用一整节来论述这个现象;于是瑞士博物学家索绪尔在勃朗峰上所作的观察就顺理成章,千真万确啦。
最近几天,我再一次研读《颜色学》的第一章,想看看我能否接受歌德的友好要求,写一篇颜色学纲要,碰巧赶上雪地里阳光灿烂,得以进一步仔细地观察刚才所讲到的阴影呈蓝色的现象,不想看着看着却吃了一惊,发现歌德本人的推论竟然是基于一个错觉。可我又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现在我想讲讲。
我的起居室面朝正南,从窗户望出去是个花园,花园的外边横着一座房子,冬季里太阳在空中的位置不高,房子就朝我这边投来一大片阴影,几乎遮盖了花园一半的面积。
几天前,阳光明媚,天空蔚蓝,我望着窗外,突然吃了一惊:窗前的雪地完全是蓝色的。这不可能是索取到的颜色啊,我自言自语说,因为我的眼睛没有接触任何一点阳光照射的雪地,也就不可能被唤起相反的错觉了;我所见到的确确实实是一片蓝色的阴影。可为了做到绝对有把握,免得邻近屋顶上耀眼的雪光接触到我的眼睛,我便卷了一个小纸筒,眼睛穿过纸筒再去看雪地上的阴影,结果蓝色仍旧是蓝色。
这就是说,那蓝色阴影并非什么主观的东西,对此我已坚信不疑。那颜色是独立于我之外的客观现象,我的主观对它没有任何影响。可它又是怎么回事儿呢?它确实存在着,可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再次注视窗前及其周围,瞧啊,谜底自己解开了。还能是什么呢,我自言自语说,不过就是蓝天的反光,不过就是蓝天让阴影给引诱下来,待在了阴影中罢啦?须知书里已经写着:颜色是阴影的亲属,只要一有机会就喜欢和阴影结合,并在阴影里和通过阴影呈现出来。
随后几天我又有机会去验证自己的假说。我走到田野里,没有蓝天,太阳照射下来也得穿过一层近乎于轻烟的雾气,洒布在雪地上的完全是一片黄色的光线;阳光十分强烈,阴影棱角分明,在这种情形下,按照歌德的学说必定会形成极其鲜明的蓝色。然而并非如此,那阴影始终是灰色的。
第二天下午,天空布满乌云,太阳只能时不时地透过云层照射下来,给雪地上投下鲜明的阴影。但它们同样并非蓝色,而是灰色。在两种情况下都少了蓝天的反光,就没有它来给阴影染上颜色。
我因此获得了足够的信心,认为歌德对这种自然现象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不对,他在《颜色学》里的有关章节急需修订。
对于彩色的双影现象,我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借助一支烛光,要么在清晨的破晓时分,要么在傍晚的薄暮里或者月光朗照的夜晚,都可能看见特别美丽的双影现象。歌德没有明说,那个由烛光照射成的黄色阴影具有客观的性质,属于混浊物质的研究范畴,尽管事实确乎如此;但另外一个由微弱的日光或月光照射成的淡蓝色或蓝绿色阴影,他却明确宣称是主观性质的,因为它是由蜡烛投射在白纸上的黄光,在眼睛里引发出的索取到的颜色。
现在仔细观察了双影现象,发现歌德的说法同样并非完全正确;相反我倒觉得,那从窗外射进来的日光或者月光,本身便带有蓝色色调,只是蓝的程度部分经由阴影,部分经由接受它的黄色烛光得到增强罢啦;也就是说,同样得有一个客观基础,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基础。
众所周知,拂晓时的阳光像月光一样,投来的都是苍白的光线。经验足以证实,在拂晓时和月光中人的面孔看上去都显得惨白。莎士比亚似乎已认识到这一点,罗密欧在拂晓时和他的爱人分手,走在旷野里忽然都觉得对方面色苍白,这值得注意的描写肯定也基于他上述的认识。拂晓时的阳光或月光使物体显得苍白这个现象,应该已经足以提醒我们,它本身必定带有淡绿或者淡蓝的色素,产生的效果跟一面用淡蓝色或者淡绿色玻璃制成的镜子一样。只不过还有下面这点有待进一步验证。
由精神的眼睛看到的光线,可以是纯白色的。然而经验中的、由肉眼所见的光线,却很少会这么纯净;倒是多半会受到雾霭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倾向于产生或正或负的偏移,结果就呈现为淡黄或者淡蓝的颜色。直射的阳光在此情况下明显地偏向正的方面,呈淡黄色,烛光同样如此;月光或者拂晓和薄暮的阳光都不是直射的光线,而是都经过了折射,都受到了雾气或者夜色的影响,所以都偏向消极的负的方面,看在眼里便呈淡蓝色调。
不妨在晦明时分或者月光中放上一张白纸,让它一半受到月光或者阳光照射,另一半却被烛光照着,这下子它便会一半淡蓝,一半淡黄;这样一来,在不加阴影和未经主观强调的情况下,两种光线便分别有了或积极或消极的表现。
我的观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歌德关于有色的双影现象说法也不完全正确,造成这一现象的更多是客观因素,不是他认为的相反;他所谓主观索取的法则,只能看做是第二位的。
设若人的眼睛总是那么敏感敏锐,一接触到任何颜色马上便能予以分解,变换出相对的色调,那眼睛就老是将一种颜色转换成另一种颜色,于是便会出现最令人讨厌的混杂不清的景象。
所幸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健康的眼睛倒是有这样的生理构造:它对所谓索取来的颜色要么根本视而不见,要么经过了提醒也只能勉强见识到,是啊,干这档子事甚至需要经过一点训练,有几分灵巧,否则就算条件有利也未必成功。
这类主观现象的特征原本在于,它们的产生前提是眼睛必须受到相当强的刺激,它们即使产生了也不能持久,而会稍纵即逝;我观察雪地的蓝色阴影和歌德观察有色的双影现象一样,都过分忽视了这个根本特征;因为在两种情况下,涉及到的都是一个几乎察觉不出来的染色表面,那所谓索取到的颜色,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一眼望去就立刻清晰地呈现在那儿。
可是歌德的个性决定他一旦认准某个法则就抱住不放,在其似乎隐藏起来了的地方仍然坚持,结果便容易走火入魔,在原本是别的法则起作用的地方发现自己心爱的法则。
今天他提起他的《颜色学》,问我对撰写一篇纲要的问题考虑得怎样,一开始我原本很想不说出我刚才的那些看法,因为感觉有几分尴尬,不知道怎样才能既说真话又不伤害他。
然而由于我对撰写纲要一事很认真,要想稳稳妥妥地写下去,就必须事先消除所有的谬误,谈清楚某些误解以便将其消除。
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满怀信任地向他承认,我经过认真观察后发现,在有几点上我跟他看法不同,觉得不管是他对雪地上的蓝色阴影作的结论或是他有关有色双影现象的说法,都并非完全无懈可击。
我对他讲了对这几个问题的观察和想法;只是由于我生来不善于作细致清楚的口头阐述,所以仅限于摆出我所看到的结果,没有进行深入的细节探讨,准备留待写出来时再补上。
谁知我刚开始讲,歌德原本高贵、和蔼的面孔立刻阴沉下来,我看得再清楚不过,他不容我提出异议。
“当然喽,”我说,“谁要想挑阁下您的错儿,那他可得早早儿起身;然而情况偏偏又是,成熟的人起得太早,幼稚的人捡到便宜。”
“好像你已经捡到了似的!”歌德略带讥讽地回答,“你关于有色光影的想法还停留在十四世纪,而且深深地陷进了辩证法的泥沼中。你唯一的优点就是你至少足够心怀坦荡,能够怎么想就怎么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