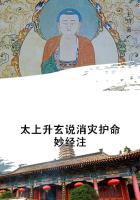1827年1月3日,星期三
(肯宁关于葡萄牙的演说)
今天进餐时我们谈起肯宁关于葡萄牙的精彩演说。
“有些人称这个演说粗鲁,”歌德说,“可这些人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他们心里藏着一种本能的渴望,那就是诋毁一切伟大的人和事。这不是反对,而是纯粹为作对而作对。他们必须有伟大的人和事作为仇恨的靶子。拿破仑还在世,他们仇恨拿破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出气筒。拿破仑完了,他们又跟神圣同盟作对;可对于人类来说,再没什么更伟大和更有益的发明啦。现在轮到肯宁喽。他关于葡萄牙的演说是伟大觉悟的反映。他清醒地感觉出了自身权威的分量和地位的显赫;他怎么感觉怎么讲,他做得对。可那些无裤汉不懂这个道理,我们其他人觉得伟大的东西他们觉得粗鲁。伟大的东西令他们不舒服,他们缺少尊重它的气量胸怀,他们受不了它。”
1827年1月4日,星期四
(谈雨果和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文学)
歌德很赞赏雨果的诗。他说:
“雨果实在是个天才,他曾受过德国文学的影响。遗憾的是他青年时代的诗风让古典派的学究气给败坏了; 可现在他已和《地球》站在一起,因而有了收获。我想拿他与曼佐尼相提并论。他富有客观精神,在我看来,他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拉马丁和德拉维尼等等先生。我对他的观察要是不错,那就算是看清楚了他和一些与其类似的青年天才源自何处。他们都承袭了夏多布里昂,承袭了这位无疑极其重要的兼为诗人与演说家的天才。可你想认识维克多·雨果的诗风,那只需读读他写拿破仑的《两座岛屿》就行了。”
歌德把诗集放在我面前,自己站到了壁炉旁边。我开始念诗。
“他描绘得精彩吧?”歌德说,“他处理起题材来是不是十分豪放?”他回到我身旁。“你只瞧瞧这一段,有多么美啊!”他吟诵闪电从下方穿透云层,照射到主人公身上的那段。“实在是美!因为场景是真实的,在山区可以目击到的;当山脚下风暴大作,闪电由下而上闪动,人看见的常常就是这个样子。”
“我赞赏法国人,”我接着说,“赞赏他们的诗歌从来不离开现实的坚固大地。他们的诗即使译成了散文,也不会丧失其诗的本质。”
“这是因为法国诗人富有学识,”歌德道,“德国的傻瓜们却想法相反,认为努力获取知识就会失去他们的天才,殊不知任何天才都得从知识吸收营养,只有这样他们的才能才可得到施展。不过随他们去吧,这些人无可救药;要真是天才肯定会走上正路。眼下在那里闹腾的年轻诗人多数根本不是真正的天才;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仅仅证明他们无能;这些无能之辈热衷写作,是受了高度繁荣的德国文学的刺激。
“法国人的诗歌创作已经摆脱陈腐之气,转向较为自由的风格,这毫不奇怪,”歌德继续说,“还在大革命前,狄德罗及其同道就试图开辟这样一条道路。随后的革命本身和拿破仑当政时期,对文学事业固然不利。还有战争年代,如果说也一样不容易产生真正的文学兴趣,也暂时令缪斯们心存芥蒂,那么,在这一时期却培养了一批具有自由精神的人士,一等到和平年代,他们便觉醒过来,脱颖而出,成为了不起的天才。”
我问歌德,那一帮古典主义者是不是也跟杰出的贝朗瑞对着干呢。歌德回答:
“贝朗瑞用的是一种较古老和传统的诗体,人们都习惯了;不过在有些事情上,他还是比他的前辈更为自由,因此也遭到了那帮守旧派的反对。”
话题转向绘画,谈到了守旧派造成的危害。歌德说:
“你自谦不是行家,可我还是想让你看一幅画,一幅咱们目前尚健在的最优秀画家之一的作品,可尽管如此,你却一眼便会发现它那些严重违反基本艺术规则的败笔。你会看见,一些细节画得很漂亮,可是整体却叫你感觉不舒服,叫你不知道如何给予评价。之所以如此,原因并非画家本人不够有才气,而是原本应指引这才气的头脑就跟其余的守旧派画家一样昏昏沉沉,结果他便忽视了真正的大师,反倒回过头去师承了那些个半吊子。
“拉斐尔及其同时代的大师们突破狭隘的风范戒条,奔向了自然和自由。现在的艺术家不是感谢上帝以这些先知先觉为榜样,追随着他们继续前进,而是转过身去捡起了那些狭隘的风范戒条。真是糟糕透顶,简直不明白他们的头脑何以如此昏聩。由于他们在这条艺术道路上无所凭借,便只好到宗教信仰和拉帮结派中去寻找依靠;因为不如此他们便虚弱得根本没法存在。
“绘画艺术贯串着一种血统传承,”歌德继续说,“每出现一位大画家,你就发现他继承了自己前辈们的优点,也正因此他才变得伟大。拉斐尔等大师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他们都立足于古希腊罗马绘画之上,立足于在他们之前完成的杰作之上。设若他们不曾效法当时的艺术先行者,今天关于他们就没多少好讲啦。”
话题转到古德意志诗歌,我提起了弗勒明。
“弗勒明颇具才气,”歌德说,“只是有些乏味,市民气重了点;现在他一点儿帮不上忙。本来嘛,”他继续说,“我可是已经有些建树,但并非我所有那些诗歌,没有一首可以收进路德的祈祷书里去。”
我笑起来,承认他说得对,心里却想,他这听起来挺奇怪的话看上去并非那样简单啊。
1827年1月12日,星期六晚上
(埃伯尔万夫人演唱《西东合集》)
晚上到歌德家欣赏音乐。出场演奏的是埃伯尔万(Eberwein)一家和乐队的几位成员。听众不多,其中有教区总牧师罗尔、宫廷顾问佛格尔和几位夫人。歌德想听一位著名年轻作曲家的四重奏,于是先演奏这支曲子。年仅十二岁的小埃伯尔万的钢琴独奏最令歌德满意,事实上也非常精彩,致使原本无可挑剔的四重奏很快成为了过去。
“令人惊讶,”歌德说,“高度发达的演奏技巧和乐器性能把时髦的作曲家领向了何处;他们的作品不再是音乐,已经超越人的感知水平,叫你根本没法靠自身的心智对它们作任何解释。你的情况怎样?我呢一切都仅仅挂在耳朵里。”
我说我的情况一样糟。歌德继续讲:“不过快板很有特点。一个劲儿地上下飞旋、蹿来蹿去,让我眼前出现了布罗肯山的魔女狂舞场面;如此说来,我到底还是给了那奇怪的乐曲一个解释。”
休息时大伙儿边谈边喝饮料。休息过后歌德请埃伯尔万夫人演唱了几首歌曲。她首先唱的是泽尔特谱写的《在夜半》,这首美妙的歌曲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不管听多少遍,”歌德说,“这首歌总是那么美。曲调有着永恒的魅力。”
随后唱了《渔家女》中的几首歌,谱曲的是马克斯·埃伯尔万。《魔王》的演唱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接下来的咏叹调《我已告诉好心的妈妈》也获得了普遍赞扬:曲子看来配得恰到好处,没有谁再可能别出心裁。歌德本人更满意极了。
成功的晚会收尾,埃伯尔万夫人应歌德的请求唱了《西东合集》里的几首歌,由她丈夫谱的曲子很有名。特别是“我愿借助优素福的魅力”的那一小节,歌德更是喜欢。他对我说:“埃伯尔万有时真是超水平发挥。”最后,他还要求唱了《唉,围着你湿润的翅膀》;这同样是一首令人十分感动的歌。
晚会散了,我还单独留下来和歌德待了一会儿。他说:
“今晚我发现,《西东合集》里的这些歌已完全不再跟我有关系。不管是其中的东方情调还是热烈情感,都终止了活在我的身心里边;它遗留在大路旁,像一条蜕掉了的蛇皮。相反,《在夜半》这首歌没有失掉跟我的关系,它仍然是我活着的一部分,仍然继续活在我的心中。
“不只这次,平时也常出现我对自己的作品完全陌生的情况。前几天读一点法文的东西,边读边想:这人讲得挺聪明,要是我自己也会这样讲。可等到仔细一看,原来是翻译的我自己的一段文章。”
1827年1月15日,星期一晚上
(谈中篇小说《Novelle》以及《浮士德》第二部的创作)
去年夏天,在完成《浮士德》第二部的《海伦》一场之后,歌德转而继续写作《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他常常给我讲他这项工作的进展。一天他告诉我:
“为了更好利用现有的素材,我彻底打散了第一卷,现在将把新老素材糅合在一起,使其变成两卷。我已安排誊抄印出来了部分,并在准备补充新内容的地方做了记号,誊写时碰到记号我就继续口授,这样我就必须保证工作不陷于停顿。”
另一天他对我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已印出的部分现在全抄完了。那些我要新写的地方夹上了蓝色纸条,这样还需做什么便一目了然。随着工作的进展蓝纸条越来越少,我呢因此也满心喜悦。”
几周以前,我听歌德的秘书说他正在写一篇新的Novelle, 于是避免晚上去打扰他,只满足于每周去他家吃一餐饭。
而今这篇Novelle已经完成一些时候了,这天晚上他便拿了头几页出来给我看。
我深感荣幸,一读就读到了那个至关重要的地方:众人围着那只死老虎站在那里,这时管理员跑来报告,狮子找到啦,正在山上的废墟中躺着晒太阳哩。
我赞叹歌德的描写鲜明生动,一切景物就连最细微的地域色彩仿佛都历历在目。出猎的队伍,古堡的废墟,途经的城市,通往废墟的田间小道,都一一展现在眼前,叫你只能完全照作者的希望去想象所要发生的事情。同时运笔又始终如此从容,如此严谨,如此有节制,让人不好对未来做任何预测,眼睛只能盯住正读着的一行。
“阁下创作这篇小说想必有个固定的情节模式吧?”我问。
“那是当然 ,”歌德回答,“早在三十年前,我已打算写这个题材,从此就一直把它藏在心里。所以现在写起来得心应手。当时我刚完成《赫尔曼和多罗苔》,马上就想用这个题材写一篇六音步的长诗,并已为此拟好了详细的写作提纲。可当我最近决定重新捡起这个题材来时,原来那份提纲却找不着了,不得不再拟一份新的,而且还随体裁样式的改变而做了改动。眼下小说已经写成,却又偏偏找到了那份旧提纲,我呢倒庆幸它没有早一些落进我手里,否则只会叫我头脑混乱,无所适从。故事和情节进展没有改动,但细节却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原来的提纲设想的是创作一篇六步体长诗,拿来写小说自然根本要不得。”
谈话转向故事内容。我说:
“有一个场面很不错,就是霍诺里奥与侯爵夫人面对面地站在已经死去的老虎跟前,这时哭喊着的妇人带着男孩赶来了,出猎的侯爵在随从们簇拥下也赶来了。这么一个稀罕的群体,画出来必定挺精彩,我真希望看见这样一幅画啊。”
“肯定,”歌德应道,“准是一幅美妙的图画,不过呢,”他沉吟片刻之后继续说,“题材的内容太丰富了,人物太繁多了,画家很难合理布局并且恰当分配光影明暗。但是稍微早一点,就是霍诺里奥还跪在老虎身上,靠在马旁的侯爵夫人还站在他面前,这一刻我曾设想成一幅画面;它倒真是可以画出来啦。”
我感到歌德说的有道理,便补充说,这一瞬原本也是随后出现的整个场面的核心。
我还谈到,我发现跟《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里的其他所有小说相比较,这篇Novelle的性质都完全不一样,写的完全是外在的事物,现实的事物。
“你说得对,”歌德回答,“在这篇作品里你几乎找不到内心的东西,而在其他作品里,这样的东西差不多可以说太多啦。”
“这会儿我已非常好奇,”我说,“急欲知道将怎样制伏那头狮子来着;我预料定会采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但究竟怎样却全然心中无数。”
“要是你都预料得到,那就不妙喽,”歌德接过话头,“我呢,今天也不打算向你透露。礼拜四晚上我给你结尾;在此之前,就让那头雄狮继续躺着晒它的太阳吧。”
我把话题引向《浮士德》第二部特别是其中的《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一场,这一场歌德还仅仅只完成了一个草稿。前些时候,歌德告诉我,他打算把这个草稿将就着拿去发表。现在我下定决心要劝他放弃这样做,因为我担心草稿一旦付印,就永远没希望再完成了。歌德想必在此期间也思考过这件事,所以马上同意我的意见,告诉我他也决定不印这份草稿了。
“这使我很高兴,”我说,“因为有了看见您完稿的希望。”
“完稿需要三个月时间,”歌德说,“可我从哪儿去找这样的清闲呢!要求我完成的日常事务太多,想离群索居谈何容易。今天早上大公爵来啦,明天中午大公爵夫人又说要来。我把这样的眷顾看做是崇高的恩典,它们美化了我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却使得我分心,我必须考虑在招待这些贵客时花样翻新,希望让他们获得符合身份的娱乐消遣。”
“不过呢,”我应道,“去年冬天您完成了《海伦》一幕, 当时您可也没少受打扰啊。”
“不错,”歌德回答,“可以完成,也必须完成,只是很困难罢了。”
“好就好在您已经有了这样一份非常详细的提纲哦。”我说。
“提纲是有了,”歌德说,“不过最难的还在后面;在实际创作时一切全靠当时的运气。《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必须写成韵文,可同时一切又得带有古典的味道。要找到这样一种诗体可不容易。再说还有对话呀!”
“未必在提纲里没有考虑到对话?”我问。
“考虑到了讲什么,”歌德回答,“但没考虑怎么讲。然后你再想一想,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夜晚,有什么不会成为话题!浮士德要说服冥后普罗瑟皮娜,求她放海伦回返人世;连普罗瑟皮娜都要感动得流下泪来,他该讲怎样的一席话哦!—— 这一切一切真是谈何容易,许多时候只好全靠运气,全得力于一瞬间的心绪和灵感啦。”
1827年1月17日,星期三
(谈席勒早年的剧作和青年的文学兴趣)
最近歌德时不时地感觉不怎么舒服,我们便常去坐在他朝向后花园的工作室里。今天又重新在所谓乌尔宾诺室里摆好了餐桌,这看来是一个好兆头。我走进屋时看见了歌德和他的公子,两人都以其惯有的自然、亲切对我表示欢迎。——歌德本人显得情绪极好,已届高龄的脸上仍富有生气,可谓喜形于色。透过敞开的房门,我看见在紧邻着的所谓顶棚室里,缪勒首相正弯腰低头地欣赏一幅大铜版画。他很快就走过来,我招呼他,说很荣幸能与他一道进餐。小歌德夫人还没有到,我们先入了席,谈话中对那幅铜版画十分赞赏。歌德告诉我,这是巴黎著名画家杰拉尔德的作品,前几天他送给了他这件礼物。
“抓紧过去瞧几眼吧,”他补充说,“趁现在汤还没有上来。”
我既满足他的愿望也遂了自己的心意,高高兴兴地欣赏起那件值得一看的作品来,特别令我高兴的是他那向歌德表示敬意的签名和题词。我没能欣赏多久,小歌德夫人就进来了,我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怎么样?”歌德说,“很了不起吧?想看出它丰富的内涵和完美技巧,得研究上好几天甚至几个礼拜。这你就改天再做吧。”
席间很是活跃。缪勒首相谈到一位巴黎大人物的来信,说此人在法国占领时期当过驻魏玛公使的要职,自那以后便与魏玛保持着友好关系。他在信里提到了大公爵和歌德,称赞魏玛是一个天才能与最高权威亲密相处的幸福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