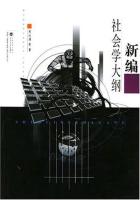我们在这里尝试用康德的“人是目的”这一命题进行新的解释,并以人类的历史活动产生的人道主义和人权理论这些反映人的本质、本性要求的思潮来作印证,以期避免“道义论”之过“虚”和“功利论”之过“实”,在这两者之间保持理论的张力,并以此为出发点,顺理成章地引出一系列生命伦理学的原则与准则。
2.生命的含义
以维护生命权利为内核的生命伦理学,促使我们对人的“生命”作一些深入的思考。生命问题,固然要从生物学的视角去把握其本质,但人的生命并不单纯是生物构造体,质言之,其复杂性及内在奥秘,仅靠科学的眼光是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诸如哲学、文学的智慧作综合性的探索。
生命是什么?奥地利著名的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V.Bertalanffy)作过这样的表述:生命表现为无数种植物和动物的形态。这些形态展现为一种从单细胞到组织、器官,再到无数细胞组成的多细胞有机体的独特的组织体系。生命活动的过程是所有生物都在其组成的物质和能量连续交换中保持自身。它能以活动的方式,尤其是以运动的方式对外界的影响即所谓刺激做出反应。事实上,在没有任何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它也经常显示出运动和其他活动,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在无生命和有生命的东西之间作出明显的、虽然不是断然的对比:前者仅仅由于外力作用而发生运动,而后者能够表现出“自发”的运动。除此之外,还有遗传、结构、功能的合目的性,有序的活动,保持同一性等等。人的生命显然具有上述生命活动的所有特征,但生命本质特别是人的生命本质却远不是这样的表述所能解答的。贝塔朗菲自己就很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很难由生物学家用精确的语言来表达,但是又不是不可言说,生物学只能陈述其表征或某种规律,而真正的本质可以由人类的直觉,运用神话、诗歌、哲学等重要符号去尝试和把握,他甚至还引用了歌德(J.W.Goethe)的一首名为《常变中的永续》的诗作为佐证:
就让太阳留在我的后方!那穿过岩隙奔腾直下的瀑布,使我越看越欣喜若狂。它一叠一叠地翻滚,化为千般,然后又分作千万道激流奔涌,向空中喷溅出无数飞沫细珠。可是从这种飞泉形成的彩虹,拱成千变之不变是多么悦目,时而分明,时而消逝在空中,在它和周围散成空蒙的凉雨。彩虹反映人类的努力上进。细心揣摩,你就会更加领悟,要从多彩的映象省识人生。
贝塔朗菲不愧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与思想者,他对人的生命的思考,既代表着自古以来多少人对此不倦的探索,同时又给今天的人们以很好的启示。
人类自古以来就一直期盼着对人的生命有深刻的认识,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各种宗教与哲学也以研究生命主题为己任。近代科学的产生,使人们得以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手段去研究生命与人的奥秘。当物理学率先趋向成熟时,就出现18世纪拉美特利(J.O.deLaMettrie)“人是机器”的名言;当生物学在物理学基础上成长起来时,又出现了20世纪40年代薛定谔(E.Schr■dinger)运用物理学量子理论与定律解说生命现象与特征,并把“基因”这一生命的物质基础视为“原子的集合体”。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基因理论再次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大热门,科学家们正试图在分子层面上揭示人的生命奥秘之所在。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L.Tolstoy)睿智的头脑同样思考着生命的奥秘,他对生物学的探索甚不以为然,他说“:如果说生命的秘密只有当研究进入无限小的领域才能被揭示的话,那就等于说,永远也不能揭示。人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问题必须在无限小的领域里才能得到解决,那么这就无疑地证明了,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托氏的见解虽然有其片面性,但确实不乏深邃之见。其片面之处在于否认了对人的生命的认识可以有不同层面与视角,其中,从生物学意义上对人的生物结构、形态、功能进行研究也是甚有价值的,它是人类认识自己的生命体及其活动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与环节,也是借此了解人这一生命体与其他生命体之异同和相互依存的理论基础,越是进入到细微的领域,可能对上述方面的认识越清晰。正如目前通过人类基因组的研究,人们惊讶地发现,人类与其他生物在基因层面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与相关性,从而增强了人类应该具有的与其他生物保持平等关系与亲和性的观念。然而,即使是就生物研究而言,托氏的见解也是极为深刻的。人的生命是一个整体,以分析的还原的方法企图去穷尽其细小、单一层面的研究,终究无法掌握与表达生命的整体状态与本质。当今的人类基因工程研究,之所以不仅要了解人类基因组的排序,还要了解每一个基因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不仅要研究人类基因组,而且还要研究人类基因组的多样性;不仅要了解人类基因组的多样性,还要将其与环境基因组等研究同步发展,正印证了这一思想的深刻性。同样,当人们为试管授精等人工生殖技术之成功引以为自豪时,是否考虑到体外受精成功的胚胎还必须放入妇女的子宫之中,在适宜的子宫环境与身心状态中,才能发育成胎儿并顺利分娩。人的生命诞生同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只掌握某个或某些环节的高新技术,绝不意味着就掌握了人的生命孕育的所有奥秘。
人的生命的复杂性还远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内容所能包含的。人与所有生物最本质的区别之一是因为人有意识,能思维,具有丰富的精神活动。就是说,人的生命是肉体与精神的统一体,是身心、形神的统一体。正由于人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自觉地认识与反思自身,自觉地带有目的地从事各种活动并相互结合,形成群体,所以人就不单纯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还是具有人文文化性质的“社会人”。这样的话,人的生命及其本质至少不能脱离身与心、自然与社会这两方面属性来思考与研究,其高度的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如此,接下来我们将从另一侧面来讨论人的生命含义或意义。从人的生命诞生讲,人类赋予自己生命以无比的价值与尊严,尽管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表述。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天地氤氲,化育了人类,所以人与天、地是一样的大,人命至重,贵于千金。西方基督文化则首先创造了一个有关上帝的神话,由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始祖,再通过婚姻的盟约,让人类自然繁衍后代,每一位自然降生的人具有和他人不同的个性与特质,因而每一个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尊严与人格。不管是自然化育说还是上帝创造说,究其实质都是人类通过自我的意识创造了颇为类似的关于自身命运与价值的观念。
从人的生命的历程角度看,人类对人的生命意义的阐发更是极其丰富而又多彩:欢乐、痛苦、爱情、自由、幸福等等。中国传统文化通常强调的是自强不息、道德修养与升华、知足常乐、化忧为乐,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在西方基督文化中,往往把人的生命视为苦难的历程,人的一生是赎罪的过程,因而,只有通过对苦难的体验才能理解生命的意义。在西方哲人们的眼中,生命的意义更是五花八门,法国作家加缪(A.Camus)指出:生命是漫长而苦不堪言的分娩过程;弗洛伊德认为:生命是爱恨交织的过程;叔本华(A.SchoPenhauer)强调:生命是欢乐、坚韧、意志的统一体。
把人的生命的终结与生命的存在及意义结合,是西方思想家特别是西方哲学家们的深刻见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JasPers)指出“:生死,包含了一切有生命的此在”,“死亡也如性别一样,皆属生命范畴”。海德格尔(M.Heidegger)则提出了著名的“向死而存”的命题,他把死看作是揭示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的方式,死亡贯穿于生命的始终,不只是生命的终端,而是向死的存在,唯有死的可能,才使生显示出其意义。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存”思想实际上蕴含着向死而生的意义,它表明,人不只是向死而存在着、生活着,人更是因死的可能及必然而使生活更有意义,因而更珍惜生命与生活。
上述对生命含义的简述,可以作为生命伦理学理论的参照,并且至少能引伸出三点结论,进而对一些生命伦理现象提出质疑:
第一,生命是肉体与精神、心理的统一体。这个观点看似平常,但往往在医疗实践中被忽视,尽管医学对人道十分重视,但实际操作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经常是狭隘的生命观、传统的医学生物模式起着主要的作用。例如,当患者面临生命晚期与临终期时,医者要么不惜一切代价,企图竭力抗衡死亡,运用各种高技术手段无益地延长患者的肉体生命;要么草率地处置,只图解除病人肉体上的痛苦,而忽视临终之际病人的心理、精神的需求,没有去认真对待和宽慰其心灵、情感上的危机,这是否真正体现了对患者的生命的尊重呢?
第二,生命存在、生命质量与生命价值的统一。尽管我们说,生命有其特定的含义,人的肉体与精神不可分离,但是,肉体生命暂且尚存而意识完全不可逆地丧失,这样的情况在当今高科技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做到,实际上生命已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从根本上说,生命存在和生命质量两者是对立统一体:生命存在是表现形式,生命质量是内涵。不存在无生命质量的生命体,同样也不会有无生命形式的生命质量。只要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身心统一)存在,就一定具有某种程度的生命质量。在这个意义上,一些人用生命质量论去否定生命存在(神圣)论显然是荒谬的、站不住脚的。或许有人不以为然,会提出诸如“植物人”来反诘:难道植物人不就是有生命而无质量吗?在我们看来,对植物人的争议实际上并不在于其是否是生命体,有没有生命质量,而在于“植物人”究竟是不可逆的还是可能复苏的生命体,如果有复苏的可能,就不能把他看作没有生命质量;如果绝对无法复苏,那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生命的意义。现在的难点恰恰就在于当一些医生专家一再声称“植物人”不可逆、不可能复苏时,不时地出现有关“植物人”复苏的报道。还有一些有关生命价值的说法,试图以生命价值来对生命存在与否或生命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作出决断。若以生命的观念来考察,这同样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既然从理论上讲,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其尊严是平等的,那么要以外在的(通常是社会的)价值标准去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有失公平与公正。因此,所谓生命价值,只能从人的生命的内在本质上去理解,即把生命价值与生命存在、生命质量结合起来考虑,在生命价值领域,生命的价值只能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而不能以任何其他的价值标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等等)去衡量。在这个意义上,生命在任何时候都是神圣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和看待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