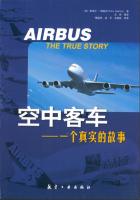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法亦随之毁损,加之藩镇割据,唐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大大缩小,造成财政匮乏,“王赋所入无几”。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缓和阶级矛盾,德宗建中元年(780年),采纳了杨炎的建议,颁诏:“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茕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州县常存丁额,准式申报。其应科斛斗,请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夏税六月内纳毕,秋税十一月内纳毕。......其月,大赦天下,遣黜陟使观风俗,仍与观察使、刺史计人产等级为两税法。此外敛者,以枉法论。”推行两税法改革,即在原来的户税、地税基础上,将当时的一切杂税增赋加在一起,改按资产征收,分夏秋两季交纳。
两税法源于唐前期在租庸调制以外所征收户税和地税。唐朝前期的户税和地税不是政府的主要税种,只是租庸调制的补充。唐初,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征收户税。贞观九年(635年),太宗又下诏“天下户三等,未尽升降,依为九等”,把三等中的每等又分为上中下,成为九等。户税与租庸调制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一种私有财产税,是以私人资产为本,按人户的资产数量确定征收标准,缴纳货币的税种,且自王公以下到普通农民都要负担;而租庸调是“以身丁为本”和均田为基础兼有人口税和公有财产使用税性质的复合税种,租庸调规定王公、贵戚、品官勋爵及不定居的商贾等都享有一定免除赋役的特权,租庸调是缴纳实物的税种。由于户税从王公以下都要负担,因此富商大贾往往勾结官府,求居下等,以求少交。代宗大历四年(769年),唐政府对户税进行整顿,明令按户等缴税规定:“天下及王公已下,自今以后,宜准度支长行旨条,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余品并准依此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税。......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征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高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税,余准九等户税。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纳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这个新规定较天宝年间的户税增加了很多。据《通典》记载,天宝时(此指天宝七载至十四载,即公元748—755年),八、九等户分别纳税四百五十文、二百二十文,现增至七百文、五百文,增长了一倍左右,可见户税在唐朝的财政收入上地位日见重要。地税是由隋开皇时的社仓发展而来的。唐初以设置义仓为名,规定从王公百官到百姓,按垦田顷亩,每亩交粟二升。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韦坚创变造法,即将义仓粮食转市轻贷,运送京师以供军国之用。这样,唐王朝不但将原来具有各地居民积蓄备荒性质的地税,变成向民间增收的一项正税,而且地税也由实物税变成了货币税。安史之乱以后,在未受到战争影响或影响不是特别严重的州郡,地税仍然照旧征收。代宗广德元年(763年)规定:“一户三丁者,免一丁庸税,地税依旧,凡亩税二升。”地税的税额也在增加,大历四年(769年)规定:“京兆来秋税,宜分作两等,上下各半,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每亩税六升,其荒田如能佃者,宜准今年十月二十九日敕,一切每亩税二升。”次年,又规定:“京兆府百姓,夏税上田亩六升,下田亩税五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荒田开佃者亩率二升。”可见不仅地税每亩税额在不断增加,而且已分夏秋两季来征收。到大历八年(773年),又规定:“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文,以京师烦剧,先加至三十文,自今以后,宜准诸州,每亩十五文。”自此允许折钱缴纳地税。户税和地税,到天宝年间,已占了唐王朝税收的很大部分。据《通典》记载:每年地税收入约为以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相当于粟米收入的二分之一;户税每年平均约二百余万贯,折算后相当年绢布收入的三分之一。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盛行,地主庄田经济迅速扩大,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大量的自耕农成为地主的佃户,寄住户、寄庄户、客户、逃户和隐户在户口总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安史之乱前,天宝十四年(755年),中央掌握的户数近九百万户,人口为五千多万;至肃宗乾元三年(769年),中央仅控制将近二千万户,人口为一千六百万。这样,以均田制为基础,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就无法满足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需求。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代宗大历年间,唐王朝的赋税收入,已经逐渐改变为以户税、地税为主。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奏行两税法。他在奏疏中说:“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丁无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779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这就是两税法的主要内容。两税法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员)“量出制入”的税收原则。在两税法中首次确定了以国家财政支出总额来匡算财政收入额度,以此分摊于各地作为赋税标准的“量出制入”税收原则。这就打破了西周以来“量入为出”的传统财政税收思想,其目的是要对政府的赋税办法及额度都加以一定限制,以使人民的赋税负担能够处于相对合理、稳定的水平和状态,从而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涵养税源,最终保障和增加政府的财税收入。
(圆)“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征税对象。两税法规定上自皇亲国戚,下至贫民百姓,甚至是不定居的商贾游贩,所有“见居”人口都是纳税对象。以前贵族、官僚、衣冠形势户等享有的免税特权,在两税法中均予以取消。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经济特权的取消,则意味着大地主庄田经济中的依附民再无存在的可能,大量被地主庄田隐冒的庄客因此而浮出水面,成为国家的纳税户。如初行两税时,唐王朝“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计得三百余万”,而“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得“客户百三十余万”。这些浮寄户,就是过去为权门豪强所隐占,不负担国家赋税的隐匿人口。因此,唐王朝的纳税编户大增,财政收入也增加了。两税法无疑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政府的征税对象范围。
(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征税标准。租庸调制是“身丁税制”,而两税法则是“舍丁税地”,“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征税标准是以田亩和资产的多寡为依据,尤以土地为主要衡量标准。两税中的地税是履亩征粟,户税虽说依据资产,但土地是资产中的重要内容,所以也主要是依据土地征税。税额的计算基础是以大历十四年(779年)垦田总数所应缴纳的钱谷总额分摊到个州县,按各户贫富等级征收。行商则按所在郡县税收的三十分之一均摊到人纳税。这种“计资而税”的制度充分考虑了纳税户纳税能力而量身定制出纳税标准,相对于按人丁平均摊派的旧制度要合理得多,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因不堪赋税而逃户的现象,起到稳定税源的作用。
(源)“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的赋税期限。两税法确立了“夏秋”两季缴税的纳税期限。夏税完纳时间不得超过六月,秋季不得超过十一月,并因此将其称之为“两税”。由于征收时间明确,改变了过去“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使人民得到了很大的便利。
(缘)“定税计钱,折钱纳物”的完税手段。两税法以前,作为正税的租庸调完全缴纳实物,仅作为其补充的户税缴纳铜钱。两税法完全以钱来作预算,用钱计定后,再折纳成实物。两税法关于完税手段的货币化规定,反映唐以来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在全社会比较普及的程度,但唐的商品经济发展仍还有较大的局限,其表现就是两税法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实物纳税的影响,所纳税款还须先以钱定税额,再折合成纳税的物品,即“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
(远)“租庸杂徭悉省”的简化税制。两税法是合各种赋税为一体的税收制度。它以地税、户税为基础,把其他各种杂税吸收进来统统以两税的形式来征收。这无疑简少了纳税项目,简化了纳税手续,给予人民极大的便利。
从以上可以看出两税法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把土地作为封建政府征税的依据。在税源上体现出由“丁身税制”向“舍丁税地”的转变,封建国家保障税收的主要手段也由超经济强制的编户齐民的户籍管理,变为经济强制的清查田亩的资产管理,由此,两税法开创了一个新的税制时代,以后宋王安石变法,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等都是对“舍丁税地”税制的完善。应该说,两税法奠定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税制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两税法实施的重要意义还在于起到了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两税法改变了过去普遍存在的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征税对象不分贵贱、贫富,而征税标准又是按资产分类,这样,无地或少地农民的税负降低了,贵族官僚地主又没有免税特权,农民没有必要成为庄田依附民以逃避赋税,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程度降低了。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变为经济性的租佃关系,农民在是否佃租地主土地方面开始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也有了程度有限的议价权利,这样,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进行配置也开始具备了可能性,这是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条件。其次,两税法以货币为主要征税方式,就迫使农民参与商品交换和经营,农民家庭经营方式逐步多样化。农民从事多种经营,促进了唐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如宣宗大和年间,京畿地区“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农民还从事手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制茶业、矿业等需要劳动力较多的行业。由于农村中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雇佣工人,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或农闲时无事可做的农民就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他们长期或短期出卖劳动力,甚至进城打工,以养家活口。这样,商品生产和交换大为发展了,并且为宋代的商业繁荣打下了基础。
尽管两税法改革起到了简化税制,减轻税负,安定农业生产和生活,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稳定国家财政收入等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严重问题。第一,尽管两税法“量出制入”的初衷是稳定税负水平,但对封建政府的财政支出没有任何约束,因此就出现了不断加征的现象。两税法实行后刚两年,建中三年(782年)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于本道两税钱,每千增二百,因诏他州悉如之”。贞元八年(792)四月,“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奏请加税什二以增给官吏,从之”。开始加征还是暂时之举,但以后就成为定制。陆贽指出:“大历中非法赋敛......既并收入两税矣。今于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复又并存。”第二,两税法税额都以钱币计算,完税时间定在每年夏季的六月和秋季的十一月,共两次。由于征税时间紧迫,农民不得不将农副产品集中上市销售,商人则乘机压低市价收购,农民换得钱币后,又必须购买需要向官府缴纳的粟米绢布等实物,而实物额是按官方牌价折定的,这样,农民在反复交换中不断受到损失,完税的钱数虽然未变,而百姓的实际负担已经大为增加,正如陆贽所说:“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糜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第三,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地方官吏为了多征户税,竟至强迫民众分户析产,或招诱他县居民迁居本县,以虚报政绩,邀功请赏。第四,两税法规定以税代役,但徭役不可能被货币取代,所以两税法实施十几年后,徭役又恢复了。第五,两税法虽规定“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但对官僚地主并无实际的约束力,大官僚、大地主往往勾结官府,对田产隐瞒不报,照样“广置田产,输税全轻”,而只有小块土地的平民则成了纳税主力。加之实行两税法后,对土地兼并完全自由放任,土地兼并情况更加严重,以至于在推行两税法后的30年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
总之,两税法的实行是符合当时土地私有制发展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的,确实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制定两税法的出发点毕竟是维护封建政府的税收收入,因而它会伴随封建政府税收收入需求的增加而变质,加之在实施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弊端,因而实行两税法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继续发展,老百姓仍然在苛捐杂税的泥沼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