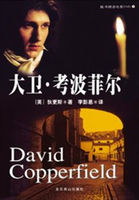果真如翔哥所说。
我穿着翔哥新买给我的衣服走进工场。从大陆带来日本的衣服都被翔哥处理掉了。后来刘利告诉我,他说我走进工场大门的时候好像一片云彩飘了进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被人如此美丽地形容过了。刘利不是文人,刘利可以如此形容我令我意识到我依然年轻或者美貌。当然我还只有二十几岁啊。我开始将工作服往新衣上套。陈师傅上上下下地打量我。
“哇,是鳄鱼牌的T恤。名牌啊,少说也值八、九千日元。刚刚才打几天工啊。”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看新衣上鳄鱼的刺绣。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知道衣服有名牌。在国内的时候喜欢买衣服,选来选去都是随心所欲。衣服的联想来自于商店街而不是品牌。突然间发现自己远远不及自己所估量的范围。鳄鱼只是通向更加广阔更加丰富的世界的一个小小的窗口。小小窗口逼真地将我生活的边缘显现出来。陈师傅也绝,仅仅一个品牌商标而已,却偷天换日地将我的处境都挖苦了。我无话可说,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陈师傅的话,我满头的雾水。
远远不止这一点儿。
午休的时候,我和刘利在三楼的空屋里闲聊,卫东走了进来。
“工资拿到了吗?”
想起饭前陈师傅曾经将装有工资的信封交给我。
“拿到了。”我说。
刘利说:“我也拿到了。”
“可以告知我是多少钱吗?”
我和刘利相互看看对方,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告诉卫东。我和刘利数了数信封里的钱。
“十六万的样子。”
“我和你差不多。”刘利说。
卫东蹲在地上,他开始抚摸自己的头发。
卫东说:“我说了你们可别急。”
原来卫东无意间听到陈师傅给老板打电话。电话的内容是关于林真的工资。
林真的工资长了。一个小时比我们多一百日元。卫东看上去有一点儿气急败坏。
“同一天在工场就职,同样的工作,有什么理由林真的工资要比我们高?”刘利也愤愤不平。
我本来想说一点儿什么,但是我突然想起了翔哥。想起了我和翔哥将来有可能发展的那样一种关系。如果不是林真自己将自己的丈夫介绍给陈师傅,如果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林真的丈夫经常到工场来和陈师傅聊天的话。凭借陈师傅和林真的男女关系,凭借陈师傅为一家工场之主,林真比我们多拿一百日元我觉得是天经地义。
男女关系也是特权。
只是林真的丈夫好可怜。林真为什么不考虑自己丈夫的面子和感受。“兔子不吃窝边草。”我说。
更何况我和陈师傅有过节。我是清馨的空气而陈师傅是发了霉的面包。
“婊子,婊子养的。”
刘利不愧是开过书店的。他用相同的一个词同时骂了两个人。
卫东像一个影子般突然慢慢地站起来。
“说心里话,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继续在这个工场里做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没有前途。以你们和陈师傅的过节,你们永远也不会长工资。你们不长工资没有关系,问题是你们影响了我。”卫东逃跑般地冲出了房间。
好久好久我和刘利都没有说话。休息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我看见刘利点燃一支香烟。在火柴的燃烧着的明亮里,刘利的肤色比原来更加苍白。“卫东说的是真的。我不想折腾了。再待一个月我真的就回国。”刘利说。我说:“你不是想赚很多很多的钱吗?”
我又说:“你的书店不是已经关掉了吗?”
我问刘利:“你不是还想重新做一番事业吗?”
在这个工场里唯一与我相依为命的刘利说他一个月后就回国令我觉得不太真实。不,是我不愿相信它会成真。刘利如果回国了,我就等于被活埋在这家工场里了。刘利是我唯一能够留在这家工场里的理由。
我忽然觉得卫东挺讨厌的,就为了一点点儿钱。本来我们应该相互安慰的。
然而我很快就冷静下来。我在第一次见大学教授的时候就明确地对教授说,我说我来日本不是为了学历和钱,我说我是想了解日本的文化和风情,我还说我想了解日本人的国民性,因为我在乎的是能否写出我自己喜欢的文字。是的,我来日本因为出于偶然所以没有具体的意义。基本上我一个人吃饱了穿暖了其余的就全都与我无关了。我可以像房顶上那只乌黑幽雅的乌鸦,除非不得已便永远地立在阳光下的电线上。我的烦恼是奢侈的。我愿意一辈子都烦恼,这样我会一辈子为烦恼写散文写小说。
卫东要养家所以要赚很多很多的钱。刘利的签证已经过期所以是不法滞在。为了不给日本警察发现的借口,刘利不敢穿着制服走出工场的大门,刘利也不敢骑自行车。刘利始终处于神经质的状态下,始终被动,始终无助除了我和他的家人对他的安慰。刘利随时有可能被日本的警察抓到然后遣送回国。刘利是灰不溜秋的,是恐惧的。我不能不在乎卫东和刘利的感受。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基本上还是想成为一个美丽的善解人意的女人。
整整一个下午我无语。我始终被一种心情包裹着。十七岁离开家乡开始独自在这里那里闯,好多好多的任性、创伤和乱七八糟都交给那时那刻的好朋友。岁月将好朋友们带给我再带走他们。如今在日本这家小小的工场里,刘利也要离开我了。逝去的再来的都是伤感。分离如人生的主题曲流转在我心里的每一根神经上,有知有觉。人生的位置总好像是后退了又后退。我想哭想流泪。我是空屋的看守人。
卫东见我一个下午都不肯说话误以为我是在生他的气。去中华街的饭店送过货,卫东一直在我的身边小声说你不要生气。这个有着圆脸厚嘴唇满头怒气冲天般直立着的头发的广东男孩,他试着挽回他的冲动所带来的后果。于是我告诉他说:“我没有生你的气。”
我说:“我理解你的心情。”
“是真的吗?”
“真的。我只是心情不好,与你无关。”我说。
“我不是说你们最好离开这里吗?”卫东说:“刚才我去中华街,富贵阁刚好贴出一张招人广告。招女服务生。富贵阁是很大很漂亮很有名的饭店。”卫东有意连用很字。卫东说富贵阁的工资比这里要高出很多。卫东又用了一个很字。我忍不住笑起来。
卫东说:“我不是女生,不然我才不会将这个情报告知于你。”
我没有信心,没有介绍人自己主动找上门去的事我已经失败了一百次。“可是这里是中华街。中华街里的老板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请中国人做事理所应当。再过几天就是五月。五月初是日本的黄金周。日本举国上下都休息。中华街那时候人山人海,饭店忙得不得了。”卫东说。我与卫东的谈话简单得不得了。问答式的。我觉得卫东所说的一切都与我没有关系。虽然已经是四月末,风中仍然带着凉意。反正脖子上挂着与我同样的翠玉的刘利要回国了,我又不坚强。好像放风筝,先是来到了加油站,接下去来到了这家工场。接下去,管它是哪里呢?
富贵阁朱栏玉砌、富贵堂皇。果然如卫东所说,富贵阁的正门口的看板上白纸红字写着以下几个大字:急募女服务员。竟然是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