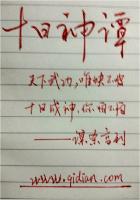“你外公是不是睡着了?”
他笑容满面,似乎在逗我玩。我呆呆地看着他,一时竟找不到标准答案,只得默不作声,靠在门框上,极其缓慢地嚼着口里的苹果。
他手里还在整理丧事搭棚要用的油布,见我不回答,笑着对我说:
“你外公睡着了,对吧!”
我仍是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似乎觉得我接受了他的结论,便摸了摸我的头,笑笑走开了。
我当然知道外公不是睡着了。他一个人躺在后面小屋的床上,一动也不动。大人们都在前面的院子里忙活,小伙伴们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不多久,我也不敢一个人留在后门口,一个寒战过后,我也慌慌张张逃离了外公独自躺着的小屋。
不知什么时候,前院多了些新面孔,他们个个身着军装,似乎也不是正规的军装,蓝黑色的,帽檐又是白色的,也没有腰带,也没有皮鞋。他们手里拿着各不相同的乐器,有大号、小号、中号、架子鼓,也有人不时举起号来吹两口的,可是声音总归不怎么动听,于是我对那些掉了漆的号没多大兴趣了,只盼着那打架子鼓的叔叔能敲两棍,但不知为何,他不怎么敲那鼓。
一旁的“仙鹤亭”多少弥补了我内心的遗憾。那是用4根钢管支撑起来的一个亭子模样的构架,顶上却也是做得如张开的鸟翼一般,钢管四周挂了几块褪了色的仙鹤图案的花布,将亭内外隔开,风过处,花布扶风,里面却什么也没有。
我对它的好奇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
天上挂了一轮好暖和的太阳,伴着阵阵秋风。大人们似乎更忙碌了。外婆家堂屋正中躺着一口黑漆棺材,棺材盖横在在棺材旁的木架子上,棺材里面似乎铺了一层崭新的黄绸,我当然好奇那棺材里有些什么,可无奈我个子太矮,够不上,大人们又太忙,我又害怕被骂,故而“探奇”只得作罢。
几位大伯将棺材盖盖上,在边上锤进了长长的钢钉封死,就抬上了河堤,放在了事先预备好的木架子上。我被牵着跟上了河堤,才发现“仙鹤亭”的4条“钢管腿”也被固定在了棺材四周。许多人簇拥在棺材边,先前院儿里的新面孔们也各自执了鼓号之类,集中在棺材前头,还有母亲、几个舅舅和姨妈的头上都绑着洁白的布巾,长长的自脑后垂到胸前。母亲抱着灵牌跪在棺材前,小舅舅跪在她旁边。放鞭炮的爷爷肩上背着沉沉一大袋鞭炮,胳膊上还挂着一长窜大红的鞭炮,他嘴里含着的烟似乎为他放鞭炮提供了许多方便。
“哎唷!”
我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被按在了我的头上,扯着我的头发,让我只觉疼痛难耐。抬眼一看,竟是小舅妈正拿着一个用白纸糊了的像帽子一样的东西往我头上套,一摸,竟是竹篾片弯成的架子,难怪会挂着头发。
那“帽子”似乎还没完全戴稳,可能也是因为挂着我的头发,让小舅妈觉得稳了,她便放过了我,我赶紧舒了口气,抬手去摸了摸头顶上的帽子。却还没来得及将它的样子猜测完整,突然感觉两只大手从背后伸来,支起我的胳肢窝,一把举了起来,我一回头,发现还是小舅妈。
她似乎有些吃力,可仍旧是半举着我,接着便围着外公的棺材快步小跑起来。
她总共小跑了3圈。
我却觉得那时间十分漫长,因为被架着的感觉实在是不大好受,尤其是胳肢窝。3圈转完,她仍不肯放下我,只是半举在半空中,我的胳肢窝越发难受了,正要挣扎着下来,却被她一把举起来,直往棺材盖上送。我顺势将两脚分开,一屁股骑坐在棺材盖板上,双手伏着盖板,努力不让自己滑下去。
我一抬眼,我四周竟是“仙鹤亭”褪了色的仙鹤图案的半旧花布,在秋风的吹拂下,有事儿没事儿地飘动着,趁着风扶花布的间隙,我也能看到河堤,以及河堤下的良田与河塘,当然,还有四周的出殡的人群。
突然,我右侧的花布被一把掀开,又一个人被举了进来。我定睛一看,竟是二哥。从他头上戴着的竹篾片“帽”,我头顶的竹篾片“帽”的样子第一次在我脑子里清晰地呈现出来。他和我一样骑坐在棺材盖板上,双手扶着“仙鹤亭”靠后的两根“钢管腿”,刚开始他还在四顾这“仙鹤亭”的内景,后来,他似乎是无处可看了,才将眼神投到了前面的我。
我看着他,期待他和我说句话,可他如同不认识我一般,始终没有开口,很快将眼神移开了。
我将头转回来,学着他的样子将两手扶在“仙鹤亭”前面的两根“钢管腿”上,我正前面的一块仙鹤花布是被撩起来的,堂哥、堂姐们的头上都系着洁白的布,随意站在棺材两边的空地上,只有当中的一块地被空了出来,不远处,大舅舅正举着一架照相机,对着拍照。
我相信我是被拍进去了的,后面洗出来的照片可以为证。除了我,还有当中跪着的母亲、小舅舅等亲人。
然而,自始至终,我都没有看到外婆,照片上也没有,也不知她有没有跟着出殡的队伍送外公最后一程。对村里出殡的规矩,我是一窍不通。不过,不管那天她有没有跟着一起去,我相信,她的做法都是合村里的规矩的,她可是最通情达理的人。
外公的棺材在众人的吆喝声中被缓缓抬起,抬棺材的是8个虎背熊腰的汉子,他们大多是我叫不出名字的,可能是村里经常从事这一行的近邻。我将钢管抓得更紧了,生怕掉下去。当棺材被抬起来缓缓前移时,我才算放下心,不过,这种放心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不久,我便想到,我屁股下面,正躺着死去的外公,他要是突然从里面坐起来,岂不是要吓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