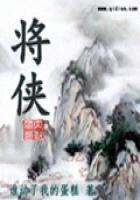尚冠里,病已家中,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此时虽是初秋,尚冠里却一直是秋雨绵绵,过往的行人也似是被这不间断的雨幕打消了出门的心思,街道上的人也是愈发的少。
其中的一位不过十多岁的年纪,堪堪用一只白玉簪绾了发,一身玄衣更是衬得人风神俊秀,长身玉立在门前,一双湛湛如墨的眸子含着笑意看着自己。
另一位,身长八尺有余,傲然如玉,抿着嘴唇,虽是寡言之人,可却微微有些孩子气。
病已起初有些怔愣,旋即从善如流的一笑,先放人进门。
那玄衣少年环顾四周,赞到:“地方虽小,却是内有大丘壑。”
病已一向对这人颇为头疼,他自诩当不得外人所赞的“端方有礼”,心中总觉有些尴尬,只是同样被赞“君子如玉”的这位,比起自己还要狡诈的多,就每每毫无愧色的含笑受了。
“陛下谬赞了,只是这秋雨绵绵,不知陛下来此为何?”病已懒得和这人打机锋。
这一脸笑意的玄衣少年,可不就是那本应该居于深宫之中的昭帝陛下。
昭帝陛下笑意不改,径直走进了内室,在正中的塌上坐了,轻咳了几声:“你前些日子不是还一心想着去塞外?”
果然见病已一脸的讶异和欣喜,而伫立在一边的卫洛却也隐藏不了内心的喜色。他自然对卫洛来历了然于胸,挑了挑眉,并没有开口。
一旁的御瑟倒是自袖中取出一个小小的物件,递给了刘弗陵。
“霍光是范明友的泰山,到底免不了走漏风声,你们拿着信物去投奔赵充国,他自然有个计较。”
病已接过自刘弗陵手中递来的物件儿,却是一枚精巧的银叶子,他心下诧异,果然就见刘弗陵一脸郁结之色:“这个物件儿横竖他是认得,也不算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你收好了便是。”
病已看见他这一幅子尴尬的样子,心中猜度此物可能有关昭帝陛下的隐私,心觉好笑,却有不敢笑出。
刘弗陵不轻不重的咳了一声,问了一句:“只是你这去塞外之事,可是已经跟许姑娘说过了?”
病已脸色顿时有些诡异,他点了点头,有些哭笑不得的说道:“许姑娘倒是一点都不给面子,那副子我要一去不返的忧心可真是溢于言表。”
“哦?”刘弗陵自然看出病已的言不由衷,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圈病已,摇头轻笑:“你如今的确文弱了些。”
文到还好,德美才秀曰文,只是这“文弱”一词便让病已有些忧心,毕竟“文弱”一词,他倒是从平君那里先听来的。
两人说着,却不防“商商”之声作响,病已心中诧异,却见刘弗陵沖自己挑了一下眉。
卫洛和御瑟剑已出鞘,正敛声屏气等着来人。
门外,一灰衫女子轻笑出声:“呵,我不过一介女流之辈,你们如此,可真是看得起我。”看她身形,似是妙龄女子,然而听其声音,却是个中年妇人。
御瑟、卫洛和刘病已齐齐看向了刘弗陵,刘弗陵似乎丝毫不意外这个女子的出现,他淡淡一笑,端的是清贵高华:“皇姐,别来无恙啊。”
那中年女子一步一步走进房中,虽然不过是一身寻常的灰衣,可这女子通身的气派,却是多年养尊处优才能熏陶出来的。
她孤身前来,面对剑锋棱峭的卫洛和御瑟,倒也全无惧色:“鄂邑盖长公主于元凤元年已薨,民女李穆清。”
刘弗陵闻言,嘴角不禁勾起了一抹笑意:“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李穆清一怔,神色有些怔忪:“是啊,这个名字,是我母亲取得。那么多年过去,似是都忘记了呢。”
毕竟有昔日的情分在,刘弗陵看见自己平素里一贯强势的姊姊这般样子,心中一拗:“阿姊!”
李穆清抬眼看他,眼角有泪水缓缓滑落:“成王败寇,盖长既然输了,自然不会苟活于世。当初离开长安,不过是一心想去河间,既然心愿已了,请陛下赐死。”
刘弗陵眸子一动:“阿姊,鄂邑盖长公主薨于元凤元年。”
李穆清似是没料到他这么说,她一贯是个强势的,如今却又有泪珠滚滚而落,然而说出的话却依旧执拗:“虽则如此,我并不认为当初和上官桀合谋废帝有错,面对权势,谁不想向上爬。”
“我既然享受过了大长公主的尊荣,又怎能容许霍光打我的脸。”
“阿姊,我知道。”刘弗陵忍不住一叹,毕竟霍氏和上官氏的斗争少不得他添油加醋,“所以,朕依旧给了你死荣。”
“阿姊,即便你当初不离开长安,朕也不会……”
‘陛下是个重情的,只是,对于盖长来说,尊严,才是最重的。”李穆清打断刘弗陵的话,“民女自此离开长安,再不进长安城半步。”
刘弗陵看着一贯骄矜尊贵的阿姊如今面容之上有了颓色,往日保养得益,看不出年纪,如今可能是途中奔波,面容却已苍老了。
他想要开口拦住她,可是谋反之事,却像是一根刺横亘在心头,年幼时的照拂和谋反之事一齐涌入脑中,几欲让他崩溃。
刘病已自从盖长进来之后就一言不发,毕竟他身份尴尬,不好开口,如今见到这两人的僵局,终是不忍心开口:“长公主回长安,难道不是心中对陛下有着一份挂念么?”
果然,刘弗陵闻言忍不住抬起了头,李穆清远去的背影一顿,却始终再也没有回头。
一室寂静。
刘弗陵是个重情义的皇帝,且不论重情义的皇帝是否称职。但对于刘病已来说,他的这份重情意,让他至少摆脱了身为”废太子之孙“,却不被宗正承认的尴尬地位。
病已曾经是个孤僻的孩子,尽管孤僻并非他所愿。
正如刘弗陵亦曾经感觉到孤独,尽管孤独亦是被逼无奈。
虽然两人在宫中的极繁华之地和极荒凉之地,然而命运还是让他们邂逅。
当时病已不过五岁,他自幼虽然多病,却是极贪玩的性子,正值夏日,长安城中的莲花开的正好,尤以太液池中的一池莲花尤甚。病已看着池水之中的莲花,袅袅婷婷,正是横波艳色,潋滟风情。可惜对于一个年仅五岁的孩子来说,美丽的莲花远不如莲蓬有吸引力。
孩子的贪玩促使他去采摘莲蓬,可是,冷不防却有人出声提醒他:“小心。”
病已本就是偷偷采摘莲蓬,趁着四周一片寂静之时来到此处的,谁料想会有人在自己身后,猛然一惊,几欲落水,却被人抓住衣领,病已颇为狼狈的被抓了回来,跌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听到有人凉凉的出声:“你该起身了吧?”
病已才发现自己倒下的时候压住了人,急忙起身。同时跌坐在地上的男孩子竭力优雅的站起身,却最终失败。他站起身想要呵斥,却在看到刘病已的那一刻猛然愣住。
两人四目相对,俱都是震惊。刘弗陵,也就是那个被病已连累的男孩子,和刘病已面容竟然有七分相似。刘弗陵如今身上的清贵之气虽有,到底不过是个孩童,没有气质的分别,倒也相差不大,俱是唇红齿白,黝黑的眸子,不过病已因为久病而少许瘦弱了些。
此时夏日的阳光打在两人身上,薄薄的光线召开了两人心中的那一抹震惊与好奇。那是一种血脉之中的神奇力量。天家无亲情,却在冥冥之中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他们打量着彼此,病已终归年纪小点,忍不住怯怯开口:“大哥哥,你是我的亲人么?”
刘弗陵有些发怔,皇家的辈分一向乱的出奇,他虽然已经猜出了眼前的男孩子的身份,却没有纠正他话语之中的错误:“你可以这么认为。”
他颇有些别扭的询问他:“你不知道在水边玩很是危险么?”
病已颇为委屈的看着他,很诚实的回答道:“可是如果你不下我的话,我也不会有事。”
他有些踯躅的开口:“我只是想要一个莲蓬。”
病已说这个话,虽然只是解释,可难免不会让人多想。毕竟被一个粉雕玉琢的娃娃看着,都不免会承诺些什么的。
他歪头打量了面前有些瘦弱的男娃娃,虽然不像是饥寒交迫,可是倒是身体不好的样子。于是他唤道:“御瑟。”
病已一愣,这才发现原来面前的少年并非是独自前来。只不过眼前这个面容普通,神色冷峻的男子,太善于隐藏自己。
御瑟看了病已一眼,没有表情的走到太液池边。
却听到刘弗陵发令:“御瑟,摘一朵莲花就好。”
病已愣住。
正在这时,刘弗陵从御瑟手中接过莲花,慢吞吞递给他:“送你了。”
病已诧异道:“可是,我要的是莲蓬。“
刘弗陵颇为无辜的眨了眨眼:“可是我只想给你莲花。”
刘病已颇为嫌弃的看了莲花一眼,碍于别人的一片好心,并没有直接丢掉,不甘不愿的拿在手中。
他问眼前的男孩子:“大哥哥,你叫什么名字?”
刘弗陵怔住,他不想胡编一个名字骗他,却还是说不出自己的名字。对于卫太子,也就是他大哥的后人,他的内心,是矛盾而复杂的。
于是他只是神色复杂的看了刘病已一眼:“有一天,我会告诉你我的名字。可是如今,我却并不想说。”
谁料得病已也是颇为善解人意的一笑:“你既然不愿意说,我便不问。其实我也不是很想知道。”
刘弗陵顿了顿,才不冷不热的轻笑了一声。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一旁的御瑟依旧面瘫。
只不过病已在回去的时候,觉得袖中怪怪的,翻开来看,却是一朵已经洗干净的莲蓬。
他忍不住回身去看,却只看到了一高一低两个人的背影。
树上的蝉鸣喧嚣入耳,年幼的病已却觉得心中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