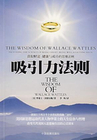偷香楼的人聚得快,散得也快。不一会儿的功夫,楼里只剩下十几个人。赵竹心他们还没有走。
赵一平问她:“竹心妹妹,我们现在去哪啊?”
赵竹心这才开始匆匆往外走,气冲冲道:“去哪都好,就是不要在这里。”也不停步,急急地朝门外走去。
赵一平委屈地躲到庞离身边,说道:“竹心妹妹怎么发这么大脾气?”
庞离笑道:“没事,我们陪她到别出去玩。”赵一平答应着,忧伤的表情又换成笑脸,欢快的跑出去。
唐叔拉住庞离,道:“九公子,我留下来。”
庞离道:“也好。”
出了偷香楼又是一番热闹景象,这里就好像跟外面不是同一个世界,好像它永远都可以这样欢乐。可赵竹心却不开心,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开心。她一气之下本想离开风波庄,可是却撞见了熟人——“书生强盗”黄秋。
当她发现黄秋的时候想躲开对方,却已经来不及了,谁知黄秋与她迎面而过竟没认出她。她随即恍然,自己今日的打扮早已不是那个小乞丐,而且黄秋也绝不会想到能在这种地方遇见自己。但她心道:“也不知黄秋来这做什么?他倒是极有可能被曲长秋收买的,还是避开些好。他虽不认得我了,却认得平哥哥和庞离,得赶快找到他们。”
才一回身,就看见赵一平和庞离迎面走来。她迎上去,说道:“我们到其他阁楼看看。”拉着二人就近走进一个房间,这间房与偷香楼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外面富丽堂皇,张灯结彩,名字却是极普通的,叫做“宴芳阁”,进到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连桌子和椅子都没有,但却有一个人。赵竹心他们本来想再进里面的屋子看看,却被这人拦住了去路,
赵竹心问:“这里面不许进吗?”
那人道:“姑娘可以进去,这两位公子却不行。因为宴芳阁只招待女客,从没有一个男人可以进去。”
赵竹心道:“你不是男人吗?”
那人对她的无理之言丝毫不动怒,温温和和地说道:“这内堂我也从未进去过。”
赵竹心没话说了,她已知道,这个风波庄里的规矩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她正想和赵一平、庞离一起退出去,忽然有“铮铮”之声,是有人在调试琴弦,很快曲调已成。赵竹心对琴棋书画这些是一样也不懂,人家的画好不好,她看不出,人家的曲子弹的好不好,她也听不出,只是听到这琴音之中,有一股哀伤之感莫名涌上心头。
她忍不住要进去看看,于是对赵一平和庞离说:“你们先到别处看看,但要小心,那个黄秋也在这里,你们别被他撞见。”赵一平说要留在这里陪她,她又嘱咐道:“你听话,帮我照顾好庞离,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我可是要生气的。”
赵一平只好默不作声。
赵竹心自己走了进去,只见里面这间屋子只是比外面多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凳子而已。这屋子里也有一股香气,可如果说偷香楼的淡淡幽香让人觉得温暖,那这里的香气就是冷的。
一位红衣美人怀抱琵琶坐在那里,好像根本没注意到有人进来。她虽穿着一身如火的红纱衣,可神情却冷得像冰,纤长的手指在琵琶上欢快地舞蹈,奏出的曲调却令人想要流泪。
当赵竹心的第一滴泪流下,琵琶声也随即停止。红衣美人道:“原来姑娘是知音人。”语气不带丝毫感情。
赵竹心答道:“我不是什么知音人,只是不知为什么,我听着听着就想起了自己的姐姐,所以才忍不住……”想到姐姐,赵竹心整个人都会变得脆弱。
“人生无常,生死有命,姑娘也无需伤心。”红衣女子已猜到赵竹心的姐姐不在人世,只是她怎么可以那样冷漠,难道人命在她眼里也根本不算什么吗?
听着这样冷冰冰的言语,赵竹心实在不舒服,她说:“我还有朋友在外面等我,打扰姑娘之处,还请原谅。”
“这个宴芳阁里终日冷冷清清,如今好不容易佳客到访,这么快又要走了么?”她的语气仍不带一丝温度,可却有一股苍凉之意。
赵竹心忍不住有些可怜她,于是又走了回来,可屋里连她坐的地方也没用,她索性就做到了床上。叹气道:“你既想有客人,为何不给人家准备一把椅子?不是别人冷落了你,是你拒人于千里之外。”
“姑娘是在教训我?”红衣女子的语气中好像有了些讥诮之意,她说:“我很久没听到别人的训话了。”
赵竹心道:“那是因为你许久没同别人说话了吧?也不知那个祁老大为什么肯让你留在他的风波庄里,难道要将他的客人都吓跑吗?”
红衣女子道:“因为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风波庄。”
赵竹心奇道:“听说风波庄是祁老大一手建立的,根本没有依托任何人。”
红衣女子承认:“的确未依托任何人。”
“那……”赵竹心很快反应过来,她忽然明白这红衣女子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你就是祁老大?”现在赵竹心对她的厌恶和可怜都变成了敬佩。
祁老大道:“不知姑娘现在可不可以坐下来陪我喝喝酒呢?”
赵竹心摇手,说道:“酒我是不喝的,不过吃吃菜,聊聊天,我倒不介意。”
赵竹心进了宴芳阁里屋之后,庞离本也想跟赵一平在外面等她。可是风波庄里的一切对他来说太过新鲜,加上他近日烦事缠身,也实在需要散散心,因此还是忍不住要到别处逛逛,可赵一平却怎么也不肯走,庞离只好说:“那你留在这里,我一个人去走走。”
赵一平犹豫着,还是说道:“不行,竹心妹妹要我保护你。”
庞离看他那副认真的样子,不禁觉得好笑,说道:“你放心,这里这么多人,不会出什么事,而且我会非常小心。你乖乖的在这里等着。”
赵一平心里只系着赵竹心,庞离坚持,他也不再阻拦。
而另一边的偷香楼中可谓是谈笑风生,姬尔安和蓝婼一见如故,把盏夜话,好不快活。蓝婼并不是个酒量很好的女人,她的眼中已有醉意,痴痴笑道:“姬公子可真会哄人开心。一个女人遇到像公子这样的男人,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姬尔安苦笑,叹气道:“恐怕是不幸的。”
“哦?”蓝婼将酒端到他面前,姬尔安在她手中就着喝了,蓝婼笑道:“如果能常伴公子身侧,还有什么事是不幸的呢?”她的话越说越大胆,就跟她给人的感觉一样,利落果敢,不拖泥带水。
姬尔安听了当然要笑,可笑声中不是开心,是无奈。“若是在几天前听到姑娘这句话,我一定很高兴,甚至一定会娶你。”
蓝婼听完这句话也不知该高兴,还是该惋惜。姬尔安这么说,就代表他一定是喜欢自己的,可话中之意是却是他绝不会让自己成为她的女人。
“为什么?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她本不想问,她觉得一个人拒绝了你,就是拒绝了,至于理由是什么,没有必要知道,可这一次她忍不住问了出来。
姬尔安把玩着酒杯,黯然道:“因为我原本有一个妻子,她美丽高傲,每个女人都迎合我,只有她在的时候,才让我觉得自己身边的这个人是有真情实感的完整的人。但她却好像永远跟我保持着距离,我觉得自己始终也不能走近她。”说到这里,他眼中现出落寞的神情。
蓝婼有些妒忌他的妻子,为什么她拥有这么好的男人,却不知珍惜?她问道:“你是为了她,才不肯要我?”
姬尔安缓缓摇头,又喝了两杯酒,才接着道:“就在几天前,我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在此之前,我还曾责怪过她。我是个连自己妻子都不能保护的男人,甚至没办法替她报仇!”
“她是被人害死的?”蓝婼小心翼翼地问,“对方很厉害吗?”
姬尔安凄然道:“没错,她是被人害死的,连我都有份害她。”
蓝婼没有再追问下去,因为她知道接下来的故事不会太好听,她相信面前这个男人一定深爱他的妻子,无论是谁伤害到自己心爱的人,都不会好受的。
谁知姬尔安却说:“更可笑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在她的心里存在过,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对她是什么感觉。”
“你岂会不知?旁人也看得出你很喜欢她,否则又怎么会为了她而拒绝别人的好意呢?”她虽然已经决定放弃这个男人,但毕竟还是不甘心的。
壶中的酒已经没有,人似乎还没有醉。香香又端了一壶新酒送进来,笑盈盈地进来,又笑盈盈地出去。
待香香出去后,姬尔安才回答蓝婼的问题,“我并不是为了她才拒绝你。我刚刚说,不清楚自己的感觉,也许只是一个借口。知道她离世的消息,我是气愤大于伤心。我的女人,即使她犯了错,我也绝不能容忍别人去惩罚她,除了我,谁都不能动她!”
“那……是为了谁?”这才是蓝婼关心的问题。
姬尔安幽幽地道:“为了一个我不敢去拥有的女人。”
“不敢?”蓝婼以为自己听错了,好奇地笑问:“这世上也有你这种人不敢的事?”
姬尔安承认,他不敢做的事情的确很少,但这一次他也只能无奈地说道:“我身边有许多女人,我也都很喜欢她们。在遇到她之前,我对每一个我喜欢的女孩子都一样,可我不能带她回去,因为我不确定自己可以护她周全。”
“呵,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胆小。”姬尔安语带讥诮。
蓝婼似乎已猜到他说的是谁了,微笑着问道:“你说的可是刚刚那位姑娘?”
姬尔安默认。他向来少与人说心事,不想今日在这风波庄里竟与一个初识的女子将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