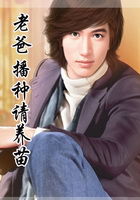冯国胜似有所觉,奏道:“朝廷若不分头传旨,单赐臣等一旨,也好作为凭据。”
朱元璋的脸色才转了过来,当即恩准。又指指坐在一旁的朱允炆对二人说道:“朝廷已立皇太孙为储君,除在文华殿视事,还随朕殿上殿下听政。”
冯国胜忙恭维道:“皇太孙年轻圣明,一望便知。”
傅友德也在一旁忙说:“陛下册立太孙,乃国家社稷之福。”
朱元璋听了高兴,把眼朝朱允炆看去。朱允炆或许因受了夸奖,脸上泛红,一时没有答话,便有意对皇孙说道:“宋国公当年作朕的亲军都指挥使,侍奉左右多年,十分亲信。颖国公阵前势不可挡,鬼神皆怕,战功不凡,如今又是皇亲,二卿都是可资倚重的人。”
朱允炆听了,忙站起来说道:“这次卿等前往西北,必然多有劳苦。”
冯、傅二人称谢,却未离座。朱元璋一旁见了,便有些不乐。
这时,傅友德拱了拱手,像有话要奏,忽见圣上脸上不悦,欲言又止。
冯国胜、傅友德见圣上半晌无话,起身拜辞。朱允炆见两位开国老臣就要退下,刚欠了欠身,见皇爷盯了自己一眼,便没起身。待两个武臣下殿,朱元璋郑重地向朱允炆告诫:
“君臣之间,不可多礼!”
朱允炆忙低头称是。
这天,朱元璋因有心事,在坤宁宫用过晚膳,想去个清静的去处。想了片刻,才命摆驾郭惠妃房中。
如今的郭惠妃年近五旬,宫中保养虽好,毕竟禁不住岁月的消磨,当年姣好的面容早失却了光泽,就象春日泛绿的杨柳,经了秋风的荡涤,悄然褪去了内里的浆液,只剩下失了韵味的枯黄。朱元璋虽然也渐至暮年,但在美女如云的后宫,可以尽情地寻访春色,所以从马皇后去世以后,郭惠妃这里来得日渐稀少。
郭惠妃生情娴静淑惠,宠遇渐衰之后,守着跟前两个皇子,倒也清静。如今皇子都已长大,相继去往各自封国,只能与跟前的宫女相依渡日,今见圣上驾临,忙小心接着,哪敢怠慢。
朱元璋多时不见郭惠妃,蓦然从她那张老了许多的脸上读出了岁月的印痕,不觉冲着那梳妆台望见自己银白的胡须。大约人们多是从别人那里观照出自己年纪的增长,光阴的流逝,朱元璋本是来破闷的,睹景生情,不由叹道:“朕果然已垂垂老矣!”
郭惠妃见圣上神情黯然,忙说:“陛下都是因为日夜为国操劳的缘故。”说完又道:“妾妃近年竟也大觉心力不支。”
朱元璋知道惠妃是在安慰自己,说道:“自皇后故去,朕深感精力疲惫。”
郭惠妃想,因为马皇后是自己的义姐,圣上常在自己跟前流露怀念之情,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缘故。
朱元璋果然说道:“太子不幸,皇太孙幼弱,朕勉强支撑,何可依赖!”
郭惠妃深知圣上因太子病故心力交瘁,内心同情,却一时找不到话来劝慰。
朱元璋因郭惠妃远不如年轻的妃子乖巧伶俐,心里不乐,便不再说。呆呆看着屋里的陈设发愣。心想,还是先前的模样,只是眼前的惠妃却已今非昔比,一时索然。这时,就看见了屋角那架摆放了多年的屏风,当时翰林学士宋谦遵旨抄在上面的唐诗依然潇洒飘逸,看着看着,暗自诵道:
“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
永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
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
吟罢,长叹一声,自语道:“朕久不来这里,竟将此诗也渐渐忘怀了。”
郭惠妃先见圣上倏然不乐,转而又对屏风感慨不已,似乎多少悟出了些缘故,忙在一旁说道:“当年陛下降旨把屏风摆在这里,不知不觉竟有二十来年了。”
朱元璋像没听见一样,怅然道:“朕如今方知,怠心一萌,万事皆休。”
郭惠妃见圣上一脸深沉,若有所思,不知何意。
朱元璋忽又降旨:“明天将屏风移至坤宁宫,朕一日三省。”
郭惠妃因此物在自己房中放了多年,忽听移往别处,心中难舍,然而圣上有旨,谁敢违拗!不由又涌上一阵凄凉。
五
朱元璋把冯国胜、傅友德派往山西,意在命他们节制西北各省兵马,尽管如此,因为燕王那几句话,仍然对蓝玉放心不下。想起这几年因太子与蓝玉沾着一层姻亲,对他过分倚重,常年在外带兵不算,军中大小将校任他调遣,如今太子故去,皇太孙如此幼弱,此**威过重,的确不无后患。想起他那年征北得胜后的狂妄行状,更加顾虑重重。恰巧,这天靖宁侯叶升从四川军前还朝,见过朱元璋后奏道:
“日前凉国公已率臣等将叛军击溃,时下正在剿捕贼首月鲁帖木儿,只因川西临近番邦,当地军力不足,凉国公命臣回朝请旨,可否像西北那样在当地募兵,增建卫所。”
朱元璋心想,朝廷命他前去平叛,如何管得这许多事情!沉吟了半天,勉强准了。
叶升见圣上恩准,便又从袖中取出一张奏呈,道:“臣临来之际,凉国公将这次平叛的有功之人开列在上面,连同拟任新增卫所的指挥、千户,命一并呈给陛下。”
朱元璋听了,顿时把脸拉了下来,升黜将校是朝廷的事,领兵之人岂能如此擅越!忽又想到,怪不得奏请增建卫所,原来是要安插自家的亲信!当时将名单草草看了一眼,说道:
“先转吏部品议。”
叶升见没立即恩准,只得说道:“如此臣回去仔细向凉国公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