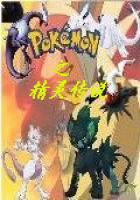却说那一路的磕磕碰碰已使他狼狈不堪,定眼细看,原来长发已乱,发中混合泥沙,残枝尽往身上沾染,白衣浓妆重抹,好不精彩。原那般若想着是要为他清理一番,却想他素来无理,何不以此灭灭他的威风,消消他的锐气,说着,便真心不再理会,到处走走,想到出去寻点吃喝之类,夜以充饥。
原来那所处的高地周围尽是荆棘,只是留了一跳小路通往别地,别人是不易察觉的,想那体型庞大的猛兽,更是不易通过。不过小虫之类或是天上飞的,那就没有办法阻挡了,若是闲时啃她两口,咬他皮肉,那也无性命之忧。
他仍旧紧锁双眉一脸愁相,梦境之中,他一直徘徊在云端,时而下落,但似永无尽头,走不出这场梦境。突然,他睁开了双眼,四处胡乱拍打了一番,但又就地蜷缩了起来,头埋得十分低下,留着那双眼睛嘀咕咕地乱转,像极了那做了损事怕遭报应的贼。整个人顿时变得庸了,从前那潇洒的模样,也是成为了飘扬的笑谈。
又是那般若一路哼哼叽叽满载而归,红艳的野果实,清冽的泉水,更甚有野生的山鸡,池水的大鱼,想着是要好好吃上几顿,即使再有几日不出,也不至于像那饿极的疯子漫山遍野地去寻找那吃的东西来,想着,遍觉得轻松自在,一路快乐着走向高地。
好生奇怪,不见了那罗新龙阿生,他又会去哪个地。想着,捉摸不透,又听见悉悉之声,回过头来,不及反应便觉得失了重,天地倒转。那罗新狠脸狠眼,那般若扑倒在地,被用力地掐住了脖子,不一会儿,她的脸是青筋暴涨,目鼓如牛,一副快断气的样子。好不容易,她嘶哑地吼叫了一声“龙阿生,你到底在做什么?”
他正是邪念冲头,哪里肯听,手中力气分毫不减。
她实在难忍,胡乱抓了一把,便碰到一块石头,于是拾起来朝他头上重重击去,他身体一震,却不曾倒下,于是又攻击了数次,待到血肉模糊时,便松了些力,般若趁机将他推到在地。
他只觉得眼前惚惚恍恍,身子摇摇欲坠,终于给倒下去了。她心慌无措,以为他性命有失,但又残留微弱气息,便生了火,运了水,替她整理了容貌,又铺了干草,便他睡得安稳。夜深多露,又怕他带伤染寒,遂出去了自己的衣裳,替她盖好。自己则暴露于寒风之中,几次因寒惊醒,却也忍了下去。
天渐渐有了曙意,黑夜渐渐散去,迎来第一丝光明,好像苦难后的庆贺,心情在此由低谷转入了高峰。
她微微睁开双眼,感觉衣服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又依依看见远方有人坐在悬崖之边,以为他又会有什么疯狂之举,遂惊恐地叫了一声“不要!”
他回过头来看她,清风吹起了他的头发,他的脸。在晨风微润中显得分外凄美。
他的声音回旋在山谷。“你醒了?”尔后又笑笑说,“你过来。”
她便过去了,同他一道坐在了悬崖边。
悬崖的景色,不比一般的低地,多了几分俯视的乐趣额,也添了几分胆战心惊的快感。他脸上没有了伤痕,淡淡地笑了一下,说了一句“你居然没事。”
她十分不解。问道:“我为什么要有事?”
他解下了她腰间的小瓶,在她眼前晃动了一下,说道:“就是它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她等待着他的继续,既不言语也不发问。
“是魔果提炼出来的香,能够迷惑人心,引发使用者心中的魔念,使人疯狂致死。每个人都有难过的坎,都有难以放下的东西。”
她终于开口发问,“那这魔果又是什么东西?”
“你有所不知,紫阳幻境有两大难解之毒,一是魔果。再就是情果了。人心是最可怕的魔,情是这个时间最毒药,虚空老子花了十八年的时间配置了这世间最毒的药,便是虚空在世,也无力救之,必死无疑。”说着便作以风轻云淡之态,似乎早已参透生死。微微而笑,早该料到这姑娘绝非凡物,却不曾想害人却害了自己。
“你说的这紫阳幻境,又是什么?”
“似真亦非真,可触不可碰。真亦是实,实亦是真。可笑姑娘竟然安然无恙,莫非心中毫无魔念。”
“心自宽敞,有怎会心生魔念。”
“也罢,你现在正处于我的梦境之中,杀了我,你便能出了这幻境。要是被那山林野兽食了姑娘肉身,便要叫姑娘白白丧失了这来之不易的生命。”
凭那罗新龙阿生怎么劝说,她也丝毫不动决心。见那生死不弃之情,他竟然也为之所动。两人相处几日,罗新龙阿生是觉得意志清醒,竟无一次疯狂之举,他也隐隐有所感觉,她身体里有一种东西在净化他心中的魔念。他也觉得惊奇,便探问:“姑娘怎么这样奇怪,是入了哪门高深的派,竟有如此玲珑不染世俗之心。”
她听了便笑道:“小时常去佛堂听和尚讲经,后又有和尚说我与佛同缘,有那佛根。”
见他哑然不语,她便知自己的话让人家不明白了,便又说道,“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于是起身说道,“既然我能化你心中的魔念,何不让我们携手破了这场梦。”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话竟出自一个女儿之口。原以为女儿是水做的身子,只知依傍男儿家,不仅毫无主见,更是目光短浅,胆怯坏事,感觉新奇,便接受了她的意见。
一路行行走走,而那眼前之景又是如此天衣无缝,不明不白地闯入,想想也觉得荒唐了。
他平静的侧面,甚是好看,她行走的背影,甚是迷人。两人并肩走在天地之间,凭夕阳拉长身影,十分和谐。淡,脱了尘世扰。
“姑娘身体里的佛性,怎的回事?”他行走时有所思,却始终无所参透。
“你也不必太过较真,只不过是小时候听了几回佛堂,染了两份佛性。”
“我只知道北有邪鹰,南有煞天,东有轿子,西有刺青门,却不曾有听闻哪方有佛。”
“你说那邪鹰、煞天、娇子、刺青门,乃邪教也,食肉百姓自以为豪,尽失道义却满口豪情,生有一张恶人脸,怀有一颗污浊心。佛却不同,佛有慈悲心,平视善恶,渡化一切人之迷、困、挣之灵魂,教人以真善美,予人君子气度佛者,必定怀情天下,顺逆不受。”
罗新听听便笑道:“你这小女子怎么尽是胡思乱想。我只知败者失天下,战马未死人先哀,遍地白花不了愁。世间怎会有你说的那般超出常理的自由之人,人,生来,往往是被约束的。尽管有人逃脱了规则,那也成为了下等人。”
般若不再言语,沉默也许胜于雄辩。
于是几天又耗了去,出路竟毫无头绪。
烦恼时般若却想,不是说人处于梦境之中,怎会有饥饿、恐慌、痛苦,更甚至于思想。便又以此恍然大悟,世间一切皆由心生,于是叫那罗新一道摒除尘世的杂念,忘记世间的一切,断了这无尽的贪念,感觉好像处于死亡之边缘,许久没有知觉。
再醒来时,已是身处郊外,具体何处,也无从得知。
两人渐渐醒来,惊吓了一屋子的女人。她们顿时都惊讶弹跳了起来,双脸刹时绯红,不一会儿便躲到那屋外边去了。听闻声响,进来一男子,皮色老成,略有年纪。
三人房中谈了一会儿,那人说了他们近日昏迷的状况,所问及,必有所答,态度不坏,不过般若却说要答谢他家娘子时,他便神色凝重,不明态度。见了,也只是僵硬的气氛。于是胡乱答谢了一番,便匆匆告辞。
走在脱离梦境的大路上,方觉天之广大,山之雄壮,景之秀丽,人之渺小。
于是般若便问起了那刚刚令她疑惑的事情来,听她道:“我只是想要感谢他家娘子多日来的尽心照料,有什么可忌讳的?”
罗新便取笑说:“亏你身居别宫数十载,天下之事竟无闻。”
“说来与我听听。”
“你身居皇宫,尽是一家子的女人,倒没什么,没有体会那男女之别,难道没有人教你闺中礼数?”
“教是教是教了,只是无心去学。何必要那重重的锁往身上套。”
“像你这样的女子,旁人不知道的,就以为是轻薄,这样的女子,人家是万万不敢要的。”
“天下男女皆一脉,只是苦了那套规矩,教人细心地学了去,什么力量,都被锁在了这自以为是的安定。”
“罢了,我说不过你。不如带你去天山看雪,那儿的女儿率真如你,一路还可以看看这世界,学学世故人情。不过还是要请你扮好男儿,以免一路多惹是非。”
那般若听说要去天山,便高兴得不得了,笑道:“在下卿源,听凭公子吩咐。”
罗新听了,也觉得好笑,说道:“好一个卿源。”说了,便高兴地上路了。
欲知后事,请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