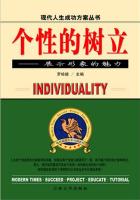很多人都怕一个人呆着,一个人活动,逛街、看电影、吃饭等等。其实一个人的乐趣太多了,方便,绝对的自主权,产生各种经历的可能性,等等。如果说一个人的活动过去存在一种面子上和心理上的障碍,那么你感谢星巴克吧,感谢那些为你的孤独提供场所的地方吧。人成熟的重要标志是能不能一个人呆着。如果你能够经常时尚地孤独、孤独地时尚,那该多美。
我的笔记本快没电了,最近的一个电源插座上已经有了两条电源线在上面。我顺着线找到一位看着比较好说话的人,轻轻地说:“先生,我电脑没电了,你能不能让我用一会儿电源?”
那人头也不抬:“好吧,先把我的拔出来,你先插一会儿吧。不过你插一会儿得再把我的放进去,我这儿一大篇东西要写完。”
你看星巴克就是这样充满时尚和智慧。
你要解决的唯一问题,是在星巴克打开什么牌子和型号的笔记本。研究一下MacBook系列,把公司发给你的戴尔latitude放包里别拿出来,约几个穿着时髦的俊男靓女,假装讨论最新的graphic设计,当然不能用PC做。
又透着俗了不是?其实你在星巴克孤独地时尚,在达不到纯粹孤独的境界时,也不妨享受一下比较世俗而实用的目标——看别人和被人看。
你该学一门乐器
缓解压力最好的方式,都是先增加压力
对于乐器这个话题,商务人士最普遍的说法是:“等我退了休,就去学钢琴。”或者,“我小时候也练过古筝的,可惜后来没坚持下来。”
总结下来就是:乐器这东西,是让人看着眼馋,但掌握起来十分费劲的事情。对于令人羡慕而难以拥有的东西,人们的反应有两种:一是提出前提条件,像“等我有了钱,等我退休有了时间”;二是把这类大人不好完成的事情交给孩子去完成,所以现在孩子们都在学乐器。
最近,我们一个同事开始学习小提琴,起因据说是看了王力宏在台上连唱带奏出神入化的表演,内心的音乐激情开始迸发,于是就买了琴,请了老师,一板一眼开始学琴了。还有一个50多岁的同事开始学钢琴,起步虽然枯燥费劲,但热情丝毫不减。
我们为这种毅力大声叫好,实际上,成人学习乐器,是一种比较纯粹的自我折磨,偶像的激励其实并无实际作用。一个成年人能够把学习乐器坚持下来,他就毫无疑问具备了挑战生理极限、平衡浮躁心态、遇事处乱不惊的基本素质。我也强烈建议中组部在考察干部时把这一项指标作为重要参考。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把商务人士学习乐器这件事搞得尽量复杂还是尽量简单。
我们平时看到的大师成才的历程,无一不是充满艰辛的。比如郎朗小时候学琴,一度不在状态,被父亲狠狠地骂,小小年纪一度产生跳楼的念头;比如钢琴大师傅聪,都70多岁了还每天练琴十个小时。看到这些,你会极度崇拜大师,但是另一方面,你的信心都给吓跑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简单化。就像我们平时招聘,广告上和面试中都说这工作怎么怎么吸引人,公司文化怎么怎么好,老板怎么怎么善解人意。尽管你入了职发现蛮不是那么回事,但是公司招人的目的达到了。而且,经历了这番认识上的波动,你在职业发展上肯定更成熟了。
学乐器也是这样,开始要让人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等你上了钩,买了琴,请了老师,随随便便就半途而废也不好意思。上星期我去商场,看到一个商铺打着大幅广告“疯狂钢琴”,“一小时学会弹钢琴”。那是一家公司买了国外的专利教材,开始不写乐谱,只标左右手的指法,一个完全不会钢琴的人确实可以在一小时后弹出贝多芬《欢乐颂》的基本旋律。
看来还是有人研究这种商业模式的,尽管对于学习乐器的人来说,往往难以逃过“情愿上钩、财务投入、精神付出、高调起步、艰难推进、骑虎难下、黯然放弃”这一轮回。
在我本人的学琴过程中,确实不记得经历了什么痛苦,尽管这是我至今玩了手风琴、电子琴、钢琴、吉他等乐器而无一精通的原因。但是我能够总结出的学习乐器的乐趣,应该比别人要多。
学钢琴的女儿有时跟我抬杠,“学钢琴到底有什么用?”
在艺术、创造、锻炼毅力、出人头地等等枯燥的说教之后,我说:“弹琴可以让你跟人不一样。比如,你们表演大合唱,是不是所有人都站着?”
“是。”
“但是有一个人是坐着的。”
“谁?”
“你们的音乐老师,她给你们钢琴伴奏。你爸从上学的时候起就给合唱伴奏,别人都站着,就我坐着,所以你爸跟人不一样。”
再往下的道理留着孩子大了讲,就是差异化是成功的基础。
乐器演奏还可以让人体会到许多商务精神。原来我们新华社乐队有好几个手风琴手。有一年中央直属机关合唱比赛,我们对唱得过人家没把握,就决定要拉过人家,找来四架手风琴一起伴奏,气势可谓大矣。
出于谦虚、不够自信、怕承担责任、紧张等种种原因,四个人进入了疯狂的相互谦让和推卸,已经到了台上,我旁边的手风琴手又把立式麦克风向我移动了近一米,说:“就看你的了,我们跟你走。”
后来,台下观众说:“你们的四架手风琴,气势还不如人家中组部合唱队的一架手风琴。”
这件事让我总结出好几条商业精神,比如:领导力的重要,关键时刻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自信来自平日的积累;还有,做事人不在多,在于每个团队成员投入的程度,等等。
如果放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最重要的是,我要买通音响控制人员,把中组部那个伴奏手风琴的麦克风关小,或者彻底关掉。
新华社乐队的回忆
人家玩娱乐的革命,我们玩革命的娱乐
从上世纪80到90年代,我在新华社乐队当过近十年的键盘手。新华社乐队很有些历史感,成立于60年代。如果说,乐队从创始到现在经历了起步期、巡回下乡、“文革”文艺宣传队和21世纪转型时期的话,那么我所在时期的重要标志是交谊舞大普及,当时新华社乐队的主要任务是给本单位的交谊舞会伴奏。
新华社的职工一直都比较能闹腾,那时候每两周一次的舞会总是把食堂挤得满满的。
舞会一般七点钟开始。六点半过后,来自各个部门的乐队成员陆续赶到,有的从采访现场归来,有的刚刚签完稿件,有的嘴里嚼着包子一路跑过来。电子琴接好了电,萨克斯管吹出A音,小提琴、吉他、小号跟着一通呜呜对音。
能玩各种乐器的党委办公室的范有良,开始琢磨今天是拉二胡还是上小提琴。
食堂的桌椅被清到了一边,地上还是有些油腻,新华社俱乐部的工作人员用扫地的簸箕盛满滑石粉,一路洒过去,马上有人跟上,用脚把白色的粉末摊开,顺便自己来个旋转,公益加热身。
还有五分钟就七点了,鼓手是外面邀请的,到得比较晚。指挥董汉杰跺着脚说:“大家帮忙先把鼓给他支起来。”
人终于齐了。食堂白色日光灯被灭掉,改成彩灯。我们第一支曲子是四二拍的快节奏,把气氛烘托起来。忠实的舞迷们早已等不及,第一支曲子就满场绕着跳,把滑石粉踢得彻底没影,也踢出了一片光滑的地面。
一般的乐队都是鼓手敲下鼓槌起个头,但是乐队常年坚信我们的指挥董汉杰。我们都知道第二支曲子是慢三,但是老董还是很严肃地报出:《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
前奏是大家一起奏的,然后老董一只手臂猛地一压,把我们全按住,另一只手优雅地旋转给坐在前排的小提琴,然后主旋律就是一段如泣如诉的独奏。
小提琴手周勇对音乐的表达趋于夸张,他除了不停地揉弦和制造颤音外,还加上丰富的身体动作。小提琴必须紧紧对着麦克风声音才能传出去,他的身体总是艺术地跟着旋律摇晃,结果出来的音效时强时弱,更加具有颤动效果。
这时乐队仿佛被小提琴感染,大家都停了下来。我一边按着键盘,一边请求指挥和吉他:“大家给点和声,给点和声。”
新华社乐队历史上是以民乐为基础的,所以对和声不大重视,演奏这种西洋乐曲,经常出现硬伤。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个人技术好,一旦有点乱了,指挥老董就优雅地用手一指,主旋律交给一个人,既不会乱,又能产生表演效果。就像足球场上球员传来传去越传越乱,干脆把球交给一个人,让他充分带球充分表现。带丢了没关系,抢回来再交给另一个人重新带,这样观众就被球员个人技术所倾倒,不再去关注是不是得分了。
我们的乐队虽然人数不多,但是都有很强的后备力量,每个位置都有替补。这要归功于新华社人才济济,以及个别天才选手多才多能。比如,我的键盘手位置,范有良是备选,老范总是希望我在,这样他可以选择演奏别的好几种乐器;小提琴周勇属于驻场选手,经久不衰,但是还有国际部著名记者许钺乃,许大记者经常担任驻外记者,但是任何时候把他拉来,都可发挥作用;萨克斯有新华社俱乐部的老员工刘文玉;最泛滥的是手风琴,曾经在中直机关歌咏大赛上,新华社有四架手风琴在台上伴奏,气势上首先压倒别人。但是后来由于我的电子琴模仿功能较强,伤了手风琴的积极性,新华社著名的手风琴手周宗真、王博广等人渐渐疏于参加乐队活动,只在重要场合才偶尔出马。吉他手有当年著名的音乐玩家刘波、郑春骅,美声和民族音乐歌手有杨绍英、姬斌,还有黑管手夏福临。那时没有什么DJ,乐队演奏间歇时,守在音响控制台边播放舞会音乐的总是老夏。
如果你感叹今天街头的交谊舞,什么曲子都能跳起来,这种功底来自新华社食堂。那时我们可着劲儿地给大家助兴,中西乐曲,男女声独唱,男女声对唱,乐队什么曲子都能奏,舞者什么曲子都能跳起来。舞会就是一个世界音乐的大荟萃。
可是后来,交谊舞会不再时髦了,现在到了街头,你仍然可以看到中老年舞者痴心的投入,但是他们缺少一个纯粹的氛围,比如说他们没有现场乐队,比如说他们地面上根本不洒滑石粉,根本就旋转不起来。
新华社乐队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走到今天,经历了一代代人。其最大的精神财富,就是让激情永远自然地流露,不论在田野乡村,国家级的剧院,还是在新华社的食堂,我们的乐手、歌手们,给一个调就唱起来奏起来,给一片空间,就把它变成精彩的舞台。这就像新华社活跃在全世界新闻第一线的编辑记者,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走到哪里,精彩的新闻就从他们的笔下和键盘间发出。
20年前的那一拨,已经不在乐队的一线,许多已经成就了新的事业。比如歌手姬斌是《瞭望周刊》和《环球杂志》的总编辑;手风琴手周宗真现在做公关公司的老总;吉他手刘波是跨国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不久前一个过去的同事说,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的午后,他去新华社宿舍小区办事,院子里的树荫下老人们摆着棋局,或者围成一圈打着牌,这时突然传出一段二胡的声音,屏住呼吸倾听,觉得弦声渐深渐近,如泣如诉,令人动容。一位老者在树下旁若无人地鼓弦,《二泉映月》的旋律和着夏日的蝉声,在躁动的空气中回旋着定格。
不用猜,能如此出入无人之境者,正是现已退休的前新华社乐队的范有良。在那一瞬间,我的耳边又回响起乐队中老范那些精彩的solo,乐手们那些即兴的配合,小小的失误,还有那种无须动作和眼神就能形成的默契。
什么时候,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再凑起来,在新华社重开怀旧创新的交谊舞会。
我们身边还有没有诗人
商业社会并非会扼杀诗人,只要诗人不再扼杀自己
当今社会,诗人像一个过时的字眼。20世纪80年代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个诗人特别有名,还是学生时就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当时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崇拜。二十多年后有了点自信,在一次校友聚会上见到这位诗人,竟能大方地过去说:“我一直特别崇拜你呢。”
已经成为商人的前诗人放松地哈哈一笑,大喊着:“你骂我,你骂我呢!”
我从不会写诗,就是以前愿意跟写诗的人在一起。在吉他伴奏的低语中吟诵《致橡树》,是那一代青年的标志。
可是那一代青年已经老了。上个月参加几位前诗友的聚会,其中一位现在还活跃在文坛的诗人带来了自己的作品。他的新诗集还请国内某著名音乐人配上了音乐,诗人自己朗诵,光盘随书发行,一个多媒体时代的昂贵浪漫。
在我们这个充满利益的商业社会,竟也能猛然听到富有节奏的语言写出的景物,诗人低沉的声音在电子合成器模拟的潺潺水声中缓缓流出。
天静下来,钟停下来,只有白水溪
匆匆奔流,映入每一个巷口。
老树上的阳光,阳台下的溪流,
青灰的碎玉,暗绿的清秋……
诗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时间不敏感,所以从前每次长谈,每次畅饮,都是从黄昏到黎明。
夜里十二点刚过,当代诗人谈兴正浓,一直歪在沙发上的某前诗人打了个哈欠说:“咱们就到这儿吧,明天早上我还有一个谈判,挺大的一单。”
大家说没劲真没劲。没劲说的是他要中途退场,不是说挣钱没劲。
现代社会的金钱观念和时间效率改变了诗人,但是,如果你还是诗人,那么你一定仍然会迅速地爱,投入地爱。
我们上学的时候,男女之爱这种事还不方便太公开,甚至还发生过躲在礼堂里做那个的一对被劝退学的事。但是诗人们全不在意。假期同学们回家探亲,拥挤的火车站台上充满了扛着大包小包的各路旅客。这时一对男女旁若无人地紧紧相拥着接吻,旁边的人竟被这突然发生的场面镇住,在他们周围自然让出一个空间。他们还是在吻,仿佛电影里的浪漫镜头,镜头绕着主人公,在炽热的嘴唇和天空的光晕间切换,观者一时也觉得现实被虚幻了。
那男主人公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诗人。可惜的是,在当年诗人的众多崇拜者多年后依然能够背诵诗人的名句时,曾经在站台上忘情长吻的女生后来全然不记得任何写给她的火辣诗句了。
诗人进入爱的角色十分迅速。我们学校的舞会每次都会出点事情,外校来的女生,跟我们学校的诗人跳上一会儿,就都相互摆脱不开了。有时大家还议论一下,“你看那谁谁谁,他跟那个女生眼神不对耶,他们俩眼神都不对啦嗨。瞧啊他们俩出去了,去礼堂了吧。”
那个时候还没有“放电”之说,只是看到眼神也能有这么大作用,比诗歌的作用来得还快。后来也证实,那个舞会上经常因为眼神而导致后续暧昧事件的男生不是真正的诗人,后来这个电眼男成了一名优秀的影视演员。所以,诗人们对演员的本领一直是由衷地嫉妒。
但是,诗人有自己爱的方式。我们聚会中的一位诗人,近年来笔耕不止,写出了15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但是他从来只用笔和纸来创作,需要交出版社付印的文字他会叫人敲进电脑。他的创作用纸都是带柔软真皮封面的牛皮纸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