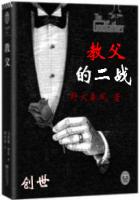天愈发的黑下来了,珍艳站起来,拍拍手,冲着我笑。这次是满脸全笑,又径直的开了门,“你看,”她指了指门外边,“我该走了。”说着略低下头走出了门,不出三步,又回过头来,却见我还在门旁边看她,不由得一阵紧张,想回过脸却又舍不得,仿佛这是一次上好的机会,失不再来。她看着我,那眼神,我看得出来,充满了期望,充满了忧伤,充满了深厚的情谊。我欲以同样的目光回报她,极力想去做好,却始终无法达到她那样的丰富复杂。
她走了,消失在夜色里,我的双眼也全被黑侵占了。这黑仿佛是逐客令。逐客令一下,客人就得无条件的走。因此珍艳走了,然而逐客令的下与否却由不得我。珍艳,我唯一的客人啊。
正愁着没有下海的路费,突然想到了珍艳。她一定会有办法,而且她一定会帮我。这天珍艳又来了,来核查月度生产,照例要抽出空来看我。于是,我有了个好机会。珍艳才坐下,我就开门见山的说:“珍艳,我要走了,想去汕头那边,或许……”我突然发觉这不是我想说的,便收住了。她听得分外清楚,站了起来,笑容大减,双眼圆睁,看我像看怪物似的。我立刻感到一阵惧怕,意识到事情没有我想的那样一帆风顺,她大概不会同意我去。珍艳好久才缓缓坐下去,脸上稍微恢复了原色,舒一口气,“也好,这里小打小闹的混不出龙来,男儿志在四方,”笑着看我,“你能去那边自然最好呀。是不是愁路费?”她自以为她笑的很自然,其实我一眼便看穿了,那是一种善心的伪笑。她是想笑的最好,好得让我无法分辨真伪,然而她不知道,这种笑越自然越显得人工斧迹。
我点了点头,还想补充说点什么,似乎是要挽救一个可以挽救的损失,“我不是,其实我只是想……”可是,我却不知该怎么样挽救。
“不用说了,”她的声音开始颤抖,“我今天身上没带钱,你又不早说。明天我送来。”
我看着她的脸,远不如来时那样红润,开始有些后悔告诉她这些事了。
她走了,虽然才刚刚来。明天,真的送钱过来了,六百,多了,太多了,我要还她二白,她死也不肯收。
“你什么时候走?让我来送你吧。”
“不不不,不用了。我,我还要回家,同家人商量。什么时候走,我也不清楚。”这时候说话的语气分明表明我在撒谎,不知她是否发觉。
她沉默了一会,“好吧。那今天就是告别的那一天。”
看着她无比忧伤的样子,我真不知该怎样才好,想了好久也只能说那句老套的话来,“珍艳,我谢谢你,真的,非常感谢你……”
珍艳似乎不需要我的感谢,“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再见!祝你成功。”她看着我,眼神和上次元宵节那次差不多,那样的期望,那样的忧伤,那样的一往情深。说完这话,她走了,头也不回的走远了。她是一直低头看路走的,手不停在脸上擦拭着,她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