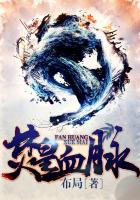黄三金突然光临生日酒宴,令罗老爷子等人措手不及。席间黄三金为女儿出走之事又伤伤心心哭了一场,说了一番后悔莫及的话,使得罗家的人对他更是摸不着底细。
“如此看来,三金是真的悔悟了。”临睡时,梁氏对丈夫说。
“悔悟又能怎样?人已跑了,是死是活尚不得知,连刘家的人也不依不饶地在向他要人,他这是自作自受了。”说起这事,罗运宏就一肚子的气。
梁氏又说:“对梦瑶是没指望了,但不能把通达也耽误了啊!”
罗运宏叹息着点了点头。
前些日子两口儿就商量过通达的婚事,托人给说了个姑娘,是长江县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叫杜慧芸,模样儿不错,且粗通文字。罗大掌柜和梁氏都说可以,但是给通达一说,却给挡下了。
通达说,他心里只有梦瑶,只要一天不见梦瑶的尸身,他是决不会另外考虑的。今日酒席散后,两口儿又将通达唤进房中,重提说亲之事,没料左说右说不抵事,通达根本就没商量的意思。
罗大掌柜生气了,说:“今日黄伯的话你是听见了的,即使梦瑶还活着,你能斗得过知府刘大人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更何况梦瑶八成是不在人世了,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梁氏也说:“通才也快二十的人了。你当哥的不把媳妇娶进门,你兄弟也不好提亲事的。”
通达便道:“那就让兄弟先娶媳妇好了,反正我不娶。”
话虽这样说,但依照老规矩,哪有先给弟弟成亲然后再说兄长的婚事的道理?罗运宏拿通达没法子,只好暂且搁搁。梁氏心里急如火燎,以后两天时时跑到老爷子面前去唠叨,要老爷子出面开导开导通达,说恐怕只有爷爷的话他才听得进去了。
“不顶事的,我说了也不顶事的。”老爷子却道。
梁氏便流下泪来。老爷子叹息着:“这事再怎么着急也是没用的。我就琢磨着梦瑶即便没死,她也会铁心不再回来了。就顺着通达一些时日吧,事情终归会有个结果的。”
这天罗通达一早要去大英盐场,梁氏将换洗的衣服拿到他房间,忍不住又要提起这码事来。通达却先开了口,说道:“妈,我晓得你又要说啥了,你就省了这份心吧。”
梁氏赌气地掉头就走。来到院子里,又见通才提着包袱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通才,你这是往哪儿去?”
“去遂宁收账,爸没给你说?”
梁氏这才记起昨天丈夫说过的让通才去遂宁收账的事来。她赶忙往厨房跑,很快拿着一包点心走来:“我真糊涂了,总是记住这忘掉那的。”罗通才说明日便回来的,要不了这么多。梁氏不由分说,硬给塞进了包袱里,直把通才送出大门。
罗通才来到郪江码头,搭上一只去渝州的货船,顺江而下,出郪江口,进涪江,直至下午日落才到遂宁。在兴隆客栈写号时,店老板说鑫源盐号的黄大掌柜已经把他的房间定下了。黄大掌柜还说,请二少爷在房间里歇着,等会儿要来约他出去吃饭。
没想黄三金说过的话这么认真,罗通才便很感激。在房间里擦洗了身子,换了身光鲜的衣服。估计时间还早,便到街上去逛了一圈。回到客店时,天色黑了下来,黄三金已在店堂里坐着等他了。
“通才,跟黄伯走,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黄三金说。
跟着黄三金走出店门,经衙门口,顺城街,拐进一条幽深的街巷,就见里面不少人家都红灯高挂,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其间有个特别显眼的去处,红彤彤的朱漆大门,门洞子两旁各悬着一只灯笼,上面写有“云香楼”三字。
黄三金抬步走了进去,便有个老妈子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两手捧在腰间道了个万福,说道:“黄大掌柜,罗二少爷,玉琴姑娘和菊香姑娘早在楼上候着了,快上去快上去!”
黄三金拉着通才便往楼上走,来到一间名为“紫霞轩”的房间门口,两个美貌的年轻女子甜甜地笑着迎了出来,将二人引进房中。
坐下后,黄三金对通才说道:“我曾说过要请你听苑娘唱曲儿的,可惜苑娘一死,就听不成了。今晚让你到这云香楼来听听菊香姑娘唱曲儿。我想与苑娘比,菊香姑娘也差不到哪里去的。”
站在对面着粉红色罩衫长裙的女子向罗通才嫣然一笑。
原来苑娘在去蓬莱之前曾在云香楼唱了半年之久,方圆百里的官家富商浪荡子弟,没有不来捧场的,云香楼也着实地红火了好一段日子。菊香姑娘生就一副好嗓门,那时候她天天缠着苑娘学艺,竟然也将唱曲儿的技法练得像模像样的了。
黄三金对菊香说道:“菊香姑娘,二少爷可是个前程远大的人物,今晚你可要侍候好,不然我可不依你的。”
菊香款款走到通才身边,紧傍着坐了:“二少爷,你想要啥只管说哟!”
又见黄三金手一招,另一位穿绿衣名叫玉琴的漂亮女子嘻嘻笑着,竟一屁股在黄三金膝上坐了。就这当儿,老鸨儿领着小厮送来酒菜,笑道:“二位边喝酒边玩儿,岂不更好?”
黄三金便道:“要得要得,边喝边玩儿!”
四人围着小圆桌坐了下来。自走进云香楼那一刻至今,罗通才心口儿都在“咚咚咚”地乱跳着。在蓬莱镇,虽说他也是个不怎么正经的浪荡哥儿,但像今晚这样堂而皇之地在这种场合与烟花女子狎玩却也是头一遭,更何况当着长辈的面,他就是想玩也不敢那么明目张胆的。
黄三金看出了通才的尴尬心理,笑了笑:“你呀,就是今后当上了广运盐号的大掌柜,也不能像你爷爷和父亲那样,只会赚钱不会享受。挣那么多银子干啥?都塞进棺材里去,岂不冤了?”
罗通才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菊香便要敬他酒,他喝了,说想听菊香唱支柳三变的曲儿。菊香答应着,从墙上取下琵琶来,调了调琴弦,纤指一划,琴声如清泉洒出。罗通才心里便道,还真像那么回事了。
就听菊香唱了一支《菊花新》:
欲掩香帏论缱绻,
先敛双蛾愁夜短。
催促少年郎,
先去睡、鸳衾图暖。
须臾放了残针线。
脱罗裳、恣情无限。
留取帐前灯,
时时待、看伊娇面。
这姑娘嗓音果然中听,且弹唱时,那对黑亮的大眼儿总是含情默默地指向罗通才。二少爷不由心旌摇动,曲儿唱完,竟然还痴痴地将菊香姑娘盯着。
黄三金看了眼通才,鼓掌叫起好来。二少爷这才跟着拍手叫好。
黄三金嚷道:“还不赏菊香姑娘酒喝?”通才急忙端起杯来递与菊香。
菊香放下琵琶,竟在通才怀中坐了,说:“二少爷喂我。”罗通才不禁桃红满面,颤抖着手儿喂菊香喝了酒。
黄三金即对玉琴姑娘说道:“你看二少爷与菊香,真个是情投意合了!”
接下来便是一阵畅饮,其间菊香又唱了两支曲儿,而罗通才渐渐地就放开了胆子,尽兴戏耍。足足玩了一个时辰,通才已是半醉。黄三金搂起玉琴姑娘,结巴着说道:“我们走,让二少爷与菊香去……去‘脱罗裳,恣情无……无限’。”
二人走后,通才便无所顾忌起来。菊香又缠着与通才喝了三个交杯酒,而后将他半扶半抱,推开一道侧门走了进去。里面竟是菊香姑娘的卧室。烛光摇曳,绣衾溢香。
在床沿坐定,菊香脱去罩衫,酥胸尽露。通才把持不住,一把拥在怀里,将菊香痴痴地盯住,嗫嚅着说道:“柳先生曲儿写得好,你唱也唱得好。‘留取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
菊香甜甜地笑着,香唇儿就将二少爷吻住了。罗通才哪经过这种场面,热血顿时沸腾起来。菊香却是个风月老手,一夜之间,颠鸾倒凤,翻云覆雨,二人直至筋疲力尽方才罢休。
“菊香,你真好。要是你一直这样对我,就好了。”罗通才梦呓般地说。
“我当然要一直对你好了,只怕你不会的。过了今夜,明儿一走,就将菊香忘在脑后了。”菊香道。
“我怎么会?不会的,决不会的。”通才道。
“要是今后你当上了广运盐号的大掌柜,再娶上个花容月貌的夫人,心中哪还有菊香的位置了?”
罗通才摇头道:“看你说的,我怎能当上大掌柜呢?”
“黄大掌柜说你能,你就一定能的。”菊香肯定地说道,“黄大掌柜说了,你人很聪明,很能干,将来是干大事的。我当然就信了,所以才对你这么好的。”
罗通才突然十分自信起来。黄三金说得也是,尽管哥哥勤奋好学,上进心强,但确实也太呆板太迂腐了。如果今后真的让通达当了广运的大掌柜,也不知要吃多少苦头的。他越这样想,便越觉得自己是个有能耐干大事的人了。
通才默默地寻思了片刻,痴情地亲了亲菊香:“放心,我要是当了大掌柜,会对你更好的。”
菊香像猫一样蜷伏在罗通才怀里,突然道:“我听说过你们家的七星神井了。”
通才一愣:“你怎么也听说了这事儿?”
菊香道:“到云香楼来的客人,南来北往的,消息可灵了。我就听好些人都在说,你们家罗老爷子是个奇人,凿出的七星神井如何如何神奇。我就在想,你们广运盐号可要发大财了,没人能比的。”
罗通才更来了兴致,说道:“当然是没人可比的了。除了我爷爷,天底下没有哪个能凿出那样的神井来。”
听通才如此说,菊香姑娘翻身伏在他身上,将粉香的脸蛋儿在他脸上磨蹭着,娇滴滴说道:“二少爷,你家的七星井究竟是怎样个神奇法。给我说说,你说嘛!”
罗通才防线彻底崩溃,觉得像菊香这样的女子也只是一时好奇而已,说说也无大碍,便将七星卓筒井的秘密说了出来。
菊香道:“照你这样说,那外面传言的八口盐井却不是七星神井了?”
通才得意地笑道:“那是爷爷摆下的迷魂阵。”
菊香摇摇头,又道:“二少爷,你说那神井井口不过碗大,却有数十丈深,随便怎么说我都不会相信的。”
“信不信由你。”通才突然又觉不放心了,说道,“我可是喜欢你相信你才给你说的,千万不要对外人讲了。”
二人缠缠绵绵,直到雄鸡三唱,东方发白,方才睡去。糊里糊涂中,二少爷竟然做了一梦,他果真当上了广运盐号的大掌柜,又见一乘花轿吹吹打打地抬了过来,里面坐着一位美娇娘,通才挑开红盖头,却是菊香。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罗通才顿时惊醒。
就听老鸨儿在楼廊里“当当当”地敲着铜钵子喊话:“各房间的姑娘听好了,吃罢午饭都到下面等着,一块儿广德寺烧香去!”
罗通才猛然想起他还要办的事来,赶忙穿衣下床。见菊香仍在憨睡中,不忍叫醒,便俯下身去吻她的脸蛋儿,没料她却醒了。
菊香搂住他不放:“不嘛,我不让你走的。”
“不行,我还有正经事要办哩。”
“那你今晚还来。黄大掌柜说了的,只要你想玩,银子他都开了。”
“办完事我还得赶回蓬莱去,家里事太多了。”
“那你就不来了?”
“放心,我肯定会来的。”
罗通才好不容易脱身下楼,在外面饭馆里草草吃了点东西,便去郑家丝绸铺讨账,没想郑家掌柜的早将银票准备在那里了。事情顺利办妥,罗通才赶回兴隆客栈去取自己的包袱,黄三金正在店堂里坐着。
“怎么样,玩痛快了吧?”黄三金笑问,又道,“人啦,辛辛苦苦图个啥?不就图个快活?”
罗通才脸便红了,却道:“事情已办了,我马上就回蓬莱去。”
黄三金道:“你先回吧。你姨母今日要来烧香的,明后天我才回得去了。”
待通才取了包袱,黄三金将他送到骡马栈,顾了马车上了路方才返回。罗通才心里叹道,还是黄伯会活人,真是活出滋味来了。哪像我爸,榆木疙瘩一个。
回到蓬莱已是深夜。通才去向父亲交差,罗运宏自然高兴,问道:“老二这回办事怎么如此利索?我还以为你会在遂宁多待一天两天的。广德寺灵泉寺正逢观音香会,你就没趁机去赶赶热闹?”
通才说道:“家里事多,我只想快去快回,哪顾得去赶热闹?”
通才去后,梁氏便道:“自那回出事挨了训,老二一下就变了,懂事多了,也成熟多了。”罗运宏也感欣慰。梁氏则在老爷子面前将通才夸了又夸。
卢夫人去遂宁烧香,听说翠娘也要去,卢禺便要一同前往。车到遂宁,在天上宫麒麟阁刚安顿下来,没料黄三金就寻来了。黄大掌柜说,他在遂宁办了事,晓得卢夫人和太太今天要来,就专门候着。
卢禺心里不爽,嘴里却道:“太巧了,我也是有公事要办才来的。今晚聚聚,喝一杯。”
黄三金则道:“我已在四海春定好了酒席,卢大人和夫人今晚一定要喝个高兴。”
当晚在四海春的这台酒,卢大人却喝得不怎么尽兴。本想这回来赶香会又可与翠娘云雨一番的,意想不到竟被黄三金给搅黄了,他喝起酒来哪还有什么兴致可言?而黄大掌柜却是另一番心情。今晚他兴致意外地高,老缠住卢禺敬酒,一杯又一杯地喝过不停。
卢大人奇怪了,问:“黄大掌柜一定是有啥高兴事藏在心里了?”
黄三金却道:“请卢大人喝酒,还能不高兴?”
卢禺摇了摇头。其实黄三金确有高兴事藏在心头,但他绝不可能向卢大人透露半点的。卢大人不高兴了,突然说道:“明日夫人和翠娘去赶庙会烧香,你与我去拜会知府刘大人,如何?”
黄三金亢奋的情绪当即冷却下来,叹道:“哎哟,卢大人,我可不便去的了。梦瑶生死未卜,踪迹杳无,我怎好去见刘大人呢?”
卢禺笑道:“就算我一个人去,刘大人也会问起你家小姐来的,你叫我咋说?万一刘大人晓得你在遂宁,恐怕就更不好办了。”
黄三金赶忙拱手:“拜托卢大人了,明日在刘大人面前千万为我遮掩一二。”卢禺笑了笑,也就不再说啥。
翌日黄三金便陪着卢夫人和翠娘到庙上烧香去。去了灵泉寺又去广德寺,两个庙子跑了下来,早已累得两腿发软,浑身无力。
回城途经西山脚下,忽见两个小尼姑扶着一位老尼在林间小道上缓缓而来,黄三金便依稀记得那老尼正是在知府门口曾偶然一见的惠果法师。黄三金退在道旁站了,待惠果走近,迎上前去。
“师太请留步。”黄三金双手合十道,“弟子有事要请教师太。”
惠果看了眼这个自称弟子的人,口念“阿弥陀佛”,并不发话。
黄三金则道:“我有个女儿,半年前突然失踪,至今生死不明。请师太为弟子指点迷津,早日寻到女儿的下落。”
惠果似有不悦:“这些事你去衙门口问二神仙好了。”说着便要离去。
黄三金一把扯住:“都说师太道行高深,慧眼神明,我只能请教师太了。”
惠果又将黄三金看了看,说道:“作孽之人自作孽,慈悲之人常慈悲。阿弥陀佛。”惠果再无多言,径自去了。
翠娘和卢夫人在旁听得真切,都觉诧异。黄三金也悟出惠果那不明不白的言语中似有责损自己的意思,心里便很不是个滋味儿。
回到麒麟阁,卢禺已在里面候着。杨二自备了一桌酒菜,卢大人说就在家里吃好。黄三金上了桌子便直叫饿,没等卢大人发话便先捞了一碗蹄花汤喝了,而后便问:“刘大人问我什么没有?”
“怎么会不问了?”卢大人道。
黄三金便紧张起来。卢禺笑了笑,说:“如今刘大人心情好多了。”
黄三金舒了口气,便听卢大人说,前些时刘公子疯疯癫癫闹得知府大人不得安宁,刘夫人便又厚着脸皮去静业禅院请惠果法师前来解难。惠果不得已再次去了知府大人家,与公子刘义单独在一间屋子里待了半个时辰,也不知使了什么法,出来后刘公子果然就好了许多,不怎么疯癫了。
翠娘便道:“卢大人,这么说来,我们也可以退他们彩礼了哟?”
卢禺道:“刘大人可没这样说。我看这事没这么容易就了结的。”
黄三金便又哀叹起来。他陡然想起下午在西山脚下偶然见过的惠果法师来,想起她说过的那句不明不白的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