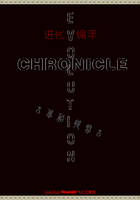嘉音一时语塞,又细细打量了这个满头花白的老城主一眼,他穿着身黑色罩衫,脚底一双蓝白相间的棉布鞋,都是八成新的样子,料想平常时都锁在橱柜里,只有待客时才穿的。满脸皱纹,微弓着背,浑浊的双眼里写满了真诚,这个岁月不饶的老人笑起来像极了话本小说里那些善良慈祥的老爷爷。
老城主一看天色,说:“时候也不早了,留下来吃饭吧,我去下厨给二位做些家常菜,姑娘你坐会儿。”
假装耳背听不见嘉音连声说的“算了吧,不打扰您了。”老城主快步走进后厨准备。
既然走不了,嘉音就决定在这里吃顿便饭,她跟进去想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老城主再三推让,见她执意留下,就给她安排了些简单的活。她摘了会儿莕菜,把能吃的菜叶全扔到了地上,不能吃的菜根整齐码在盆里交给老城主,正在切豆腐的老人家一看,鼻子一酸,忍了好久才没掉下眼泪。
小姑娘被老城主恭恭敬敬地送出厨房,并连声嘱咐道:“一看你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不该待在这里的,在外面等我做饭就行。”
眼瞅着嘉音到了外间看不到厨房情形,老城主心疼地用小盆一点点收起地上被扔掉的莕菜叶,放在一旁,打算明天自己吃。这一幕被在房顶上干活的不败尽收眼底,他张张嘴,没有说话,只是又给瓦房上多加了几层茅草。
饭菜上桌的时候不败刚好修完屋顶下来,和等了许久的嘉音一起落座吃饭。老城主家里用的是一张方桌,凳脚长短不齐,稍微用力按上去就会左右摇晃,不败找了几块木片垫在桌下才踏实许多。
晚餐对于老城主来说还算丰盛,三菜一汤,麻婆豆腐,醋溜白菜,葱花炒蛋,青菜汤。青菜和白菜都是院里空地上种的,鸡蛋是家里散养的老母鸡下的,豆腐是东街徐大娘半卖半送的。家常菜三个字当之无愧。
嘉音偷偷打量了下不败,本以为无肉不欢的他会说些失礼的话,没想到莽汉不败抓起饭碗就吃,运筷如飞,热情地就像在皇宫里品尝满汉全席一样。嘉音看着正目瞪口呆地注视不败的老城主,笑着解释了一句,“他刚干完活,有些饿,您别见怪!”
老城主食量很小,只吃了一些就放下筷子,看着二人笑笑,说:“你们多吃。”就好像身前坐着的是久未回家的孩子一般无二。
酒足饭饱之后该谈正事了,老城主的表情有些局促不安,但他还是坚持说了自己的要求,“嘉音小姐,我希望您能把您手里的天涯洛星草转卖给我。”
“叫我嘉音就可以,老城主您为什么要买这株药草?”
“哎呦呦,瞧我这脑子,还没向两位自我介绍,老朽陈亭歌,忝做节时城主二十七年。”老城主站起来向二人行了一礼,又道:“实不相瞒,节时城背靠黄沙,唯一的出口丹阳峡车马难通,既无商贾交行之便利,又无岁岁丰收之沃土,百姓艰苦,民生凋敝。可春朝帝国的苛捐杂税繁重,我身为一地父母官,保境安民,治土有责,多少次上书朝廷想要因地制宜、减免节时城赋税都杳无音信。所以就想动些歪脑筋,这株天涯洛星草世间难寻,是治疗太子妃病情不可或缺的药引,将它进献给太子就能用这个人情为我节时城谋些福利。”
陈亭歌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面上因为羞赧涨得通红,腰杆却挺的笔直。他放弃了书生傲骨逢迎权贵,是因为被世俗社会打磨了棱角,他明知从今往后将与清流二字无缘,却由衷地为自己骄傲;他在这个位置上举棋不定二十七年,做出选择的那刻就好像回到了二十七年前自己踌躇满志来到节时城的模样,那年他给自己题了八个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时至今日念念不忘。
“卖给您可以,左右在我手里也没什么用处,能拿去救人那再好不过了。您打算出什么价买?”嘉音不忍心刁难面前的老人,从储物戒指里掏出那盆药草,顿时满室银光照的人神迷目眩。
老城主脸更红了,从怀里掏出十个水币,说:“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了,你看够吗?”
这十个靛蓝色的硬币晃的嘉音有些发愣,“您应该知道我在拍卖会上成交的价格是它的千倍不止吧。”
没等陈亭歌再说话,始终保持沉默的不败站起来,弯腰从老城主手里接过水币,又从嘉音手里拿起药草放到桌上,道:“钱货两清。”
老城主反应过来,高兴的喜出望外,站起来连声道谢,“我替节时城十万百姓谢过二位壮士高义,他日如有差遣,只消一封书信,刀山火海我陈亭歌不说半句二话。”
餐桌上,慵懒的小姑娘舒展了下筋骨,笑说:“反正花的也不是我俩的钱。那既然没什么事了,陈城主,咱们就此别过。”拉着不败就要走,不料大块头纹丝不动。
不败看着陈亭歌问:“城主大人,我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我觉得您应该是个好人,可是客栈店主提到您的时候为什么满脸害怕惊恐的神色?”
嘉音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冒险团里的肌肉担当,道:“没想到你也学会思考了?是不是跟我们不靠谱的团长学坏了!”
陈亭歌喟然长叹,“我陈某人自诩是个清官,却不敢说自己是个好官,做清官简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可以;做好官难啊,为民办实事,谋福利那才是他们心里的好官。新历九百六十四年我请人在堰塞河修了座桥,修石桥经费不够只能修了座木桥,三年之后木桥因为日晒雨淋塌了,六个走在上面的行人掉下了桥面,被堰塞河湍急的水流冲走,两天之后才在下游的浅滩发现他们的尸体。五个种完地回家的庄稼汉和一个手里握着薄饼的小女孩,五个家的天从此塌下来了,我去现场看的时候见到那个小姑娘双目无神地直视这片蓝天,手里尤紧握着她可能半月才能吃一次的薄饼不肯松手。我不敢见他们的家人,因为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老城主叙述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些哽咽,眼眶发红,双眉紧簇。“后来我慢慢发现,原来自己只是个清官,不是个能臣,我修过没人愿走的路,筑过高河十丈的坝,判过百口莫辩的冤案,伤过一去不复的民心。我开始渐渐被街坊疏远,被同僚排斥,我争不来朝廷下拨的经费,不愿收富户上交的重礼。我是这个时代的孤儿,流浪在鼎沸喧嚣的人间。”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明年我就该到任离职还乡,走之前还想再为这里的百姓做些什么。无论他们怎么看我,我只认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嘉音和不败出了城主府就往昨天住的那个客栈走,“这么迟回去杭左一定八卦个没完!”嘉音把玩着手里的钱币,“真是败家呀,又该挨铁公鸡的骂了。”
“真是一个好人。”不败和嘉音完全没聊在一个频道上,从城主府出来他鼻子就一抽一抽的,想哭却哭不出来,毕竟他有几十年没哭过了,忘了这项本能也可以理解。
街角有个学堂,学生们还在借着灯光读书,“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真是好学呀。”嘉音感慨道。
“怎么没有先生,这么晚了孩子在这儿会不会不安全啊!”不败问。
“人家肯定不是第一天在这里夜读了,先生也许马上就回来了。”嘉音没理会不败多余的担忧,把他拉回了客栈。
中年掌柜见他们回来,马上换了一副笑脸迎上前,“哟,几位回来了,里面请里面请,上房有,热水也有,吃点儿什么,我让厨房给您现做。”
“现在让咱住了?”不败话里带刺。
“当然,城主府禁令早就撤销了,几位随便住,上房有的是?”中年掌柜中气十足地回答道。
想到一心为民的老城主,不败忍不住就想为他辩驳几句,“今天我见过城主了,没你说的那么可怕。”
掌柜的疑惑问道:“谁和你说的城主可怕?”
“那你下午的时候抱着我大腿不撒手,哭诉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要是违逆了城主的意思在这里呆不下去。这段您演的哪出?”不败反呛他。
掌柜的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件事我和您说,您别往外传。陈城主执掌节时城二十七年,清廉公正刚直不阿大家都看在眼里,曾经他好心办过几件坏事,我们、包括那些受害者也早都原谅他了,只是他自己一直过不去心里那道坎,越来越疏远街坊。他平时吃穿用度都节俭,所有的俸禄都拿来开他府外街角的一个学堂,那个学堂免费收上不起学的穷孩子,一开就是二十年,孩子们也都珍惜这个机会,去上学的都用功。大家知道他不容易,就各尽所能帮他,可他发现出门买菜街坊都是半卖半送的,以为我们畏惧他的权势,索性自己在家种菜养鸡。下午我接到通知的时候,就想帮帮老城主,脑子一热,给二位演了这么一出,真是对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