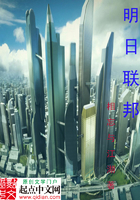甘婧挑眉,将轮椅转了个角度,直面嬴政,不骄不躁地行了一个宫礼:“沐与浩参见秦皇。”
方才踏进来之前,他便听到烟茵正在向旁边的这个男人请教“李斯鼠论”,他的脚步虽然微顿,但最终还是踏了进来。
“都起来吧。”兴许他们两人敢光明正大地在这亭子中讨论,当是清白的,多疑的嬴政这样宽慰自己。
烟茵显得有些紧张,战战兢兢地便是不敢抬头看向嬴政,道:“臣妾,臣妾今儿个出门透透气,恰逢卫国右相大人出门。臣妾以前经常听宫女们说卫国丞相才识渊博、学富五车,便想跟右相大人探讨一番,陛下您……”
嬴政挑眉,历经沧桑的脸上威严丝毫不减,两鬓白发更添冷峻,用低沉浑厚的声音问:“不知爱妾同右相大人都谈了什么?”
“臣妾,同右相大人评论了李斯大人的鼠论,还探讨了如今封国是否应当存在。”烟茵做出一派小女子的娇羞模样,又带着几分胆怯和害怕,让人心中油生怜惜之情。
这两个可是当今朝堂之上的禁忌,烟茵却敢在这时候提出来,甘婧颇感意外,抬眸看向烟茵,却见她低着的眸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
“既然如此,真人倒是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嬴政直接在石椅上坐下,眸眼之间已经没有了刚刚的阴沉,反而多了几分亲近。
甘婧眼中闪过了然的亮光,看来,当初让毒姑变成烟茵进入秦宫做内应的做法虽然冒险,但也是正确之举。
嬴政生性多疑,若是方才毒姑回答说只是简单问问一些日常琐事,嬴政的怀疑会更甚,反之,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将一些嬴政比较敏感,官员私下常交流而却没人刚跟嬴政提的点果敢地暴露出来,嬴政才更会相信。
烟茵脸色骤变,吓得忙跪在地上,低低啜泣道:“臣妾不敢,臣妾妄议朝政,请陛下治罪。”
“你若是不说,真人便将你贬去漠北。”嬴政狠言威胁。
“臣妾,臣妾以为不应废除封建,李斯大人出身底层,曾是楚国一个看守粮仓的小吏,焦虑于个体存在,虽后从一介贫贱布衣跃升为帝国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丞相,但丞相大人心中算计的仍是小老百姓心中的算计。
李斯大人认为封建当废,乃因此制保护的是上层贵族的利益,但却忽视了如今之秦帝国,乃是家天下而非国天下。”烟茵轻声说道,若是仔细听去,兴许还能捕捉到她一字一句中的颤抖。
嬴政放在腿上的左手拳头微微收紧,右手直接挑起现正跪在地上的烟茵的下巴,双眸寒光四射地质问:“你可知你这么说,将要面临的是什么?”
寒雪般的声音充满了不容抗拒的凌厉,直刺在场每个人的心中,就是跟着嬴政过来的小太监,也忍不住为烟茵捏了一把手心的汗。
李斯可是嬴政最信任的人啊,她算什么,顶多就是一个妾,居然敢在嬴政面前大谈李斯的不是,还直言那政策有问题。
烟茵这会儿倒是凛然不惧,嘴角扬起一抹邪魅的笑意,道:“臣妾知道,但也是陛下让臣妾说的啊,臣妾可不能抗旨不遵。”
嬴政正要往下方脖子扼住的手却在此时转了个方向,往她的脸上滑去,细细摩挲着她的脸,笑道:“真人倒是有几天没来你这儿了,过两天真人要移驾阿房宫,美人可愿随伺?”
“臣妾遵旨。”烟茵笑颜绽放,眉梢眼角皆藏秀气。
外头守着的宫人莫不目瞪口呆,但秦皇在前,谁也不敢明显地表现出来。
赵高瞥了眼甘婧,轻声提醒嬴政道:“陛下,这右相大人还在呢。”
兴许在嬴政看来,赵高不过是在提醒他有外人在,不要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可是甘婧却看到了他余光之中的一丝阴险。
嬴政这才放开了烟茵的脸,转过身来看向甘婧,脸上的亲近也一并敛去,又变成了那位有万夫难敌之威风的秦皇。
“方才美人已经说了自己的看法,真人也很想知道,卫国的右相大人对此,是如何看。”
甘婧并没有直接说明自己的看法,而是拱手道:“臣想,先请旨饶恕与浩冒犯之罪。”
还没开始说呢,就给自己筹划了一条退路,卫国的这位丞相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难怪李斯上次会败在她手中,嬴政心中腹诽着,最终还是极其“开明”地说:“允。”
“谢秦皇。封建制,世人皆知源于西周武王,西周通过封建制,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控制,开发边远地区,扩大统治区域,并逐步构织出遍布全国的交通网络,形成对周王室众星捧月般的政治格局。
后期为何封建止步不前,爆发内乱,乃是因为各个诸侯卿大夫和周天子血缘关系越来越远,他们对周天子的感情基本上已经很淡漠了,再加上距离较远,不会很听命于天子。
而今秦国实行郡县制,任命的太守更与中央无血缘关系,若战乱爆发,由谁亲力亲为维护中央?再者,本相敢断言,郡县实行三四十年内,必将出现大面积官场腐败,而且愈演愈烈。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矛盾激化将官逼民反。大一统的郡县制事实上不会制约过战乱的发生,只会使得战乱更无秩序,更无规律。郡县制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是个倒退,是私有制的进步,公有制的倒退。
秦王认为作为国天下的秦帝国,是该私有为中下层或是为家国?李斯丞相虽是统一过程的一大功臣,但因私人情感便轻信于一人之言,本相只觉国将不国”
甘婧一言说的毫不避讳,既将古之封建与今之郡县进行对比,还暗讽嬴政识人不清,任人为亲为重,嬴政不语,他早便知晓这位丞相正直凌厉,可没想到他连自己的面子都一点不给,当真狂妄!
看到嬴政的拳头又在收紧,甘婧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再一拱手道:“秦皇,这便是本相的见解,不喜之处请秦皇见谅,本相一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好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嬴政哈哈大笑道。
赵高知晓,嬴政在外邦面前不怒而笑,必然是怒火焚烧的象征,便打着哈哈出来圆场道:“陛下,您待会儿更术士还有一场方术会要谈,可能不宜久留。”
嬴政侧目看了甘婧一眼,便甩袖而去。
看着那一群人走远,烟茵这才恢复了一脸淡漠的神态,抿了口茶戏谑道:“你可真是不怕死,敢在老虎头上拔毛。”
甘婧轻摇着头,抚摸着手中的红线,勾唇道:“你也不赖。”
谁能想到,曾经互为对手、势要杀个你死我活的人,如今却同坐在一方亭子下,谈笑风生,玩弄一国之首。
“那是,那老贼也不过如此,区区几句话便能将他气得满地暴走。过几天我到阿房宫伺驾,可是个好机会,要不?”烟茵放下看手中的杯子,冷眼看着他们离去的方向,妖艳的红唇翕动。
“暂时放着,时机未到。”甘婧哪里不知道她的心思,自己敢当着武林众人的面为她制造一出假死的戏,又将她安排入秦宫,就是因为她跟自己的经历类似,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便是嬴政!
烟茵拍案而起,不满地抱怨道:“又是时机未到,要是早几年前老娘早把他弄死了,还让他活到现在,我就是不知道你究竟在等的是什么时机!让一个个机会就这样在眼前跑了。”
在甘婧身后的阴竹闻言,眉角微蹙,拿起剑便做出预防的姿势:“不可无礼。”
他对甘婧将毒姑安入秦宫的做法实在不解,但是既然已经安排了,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在他看来,毒姑还是那个毒姑,本性不会变,方才看她怒气冲冲,便以为她是想要对自家主子动手。
甘婧将他手中的剑挡下,摇着头道:“无妨。”
转而看向烟茵,嘴唇翕动,一字一句传音至她的耳中:“若不想秦氏一族死而不僵,你自可去尝试。”
原来,右相便是右相,看事情都比别人要远上几分。烟茵已经镇定下来,嫣然一笑:“如此,当是听从大人安排。茵儿也该退下了。”
“袅儿,还不随本宫回宫准备准备。”
站在亭外的袅儿一听,便上前来作揖道:“是。”
从亭子出来,嬴政已经是被气得吹胡子瞪眼的:“赵高,你说,她说的是不是在理?”
“奴才以为,右相此人狂妄,说出的话陛下不必放心尖上。”赵高谄媚笑道。
嬴政前进的脚步倏忽一停,回过头来的眼睛阴鹜又充满嗜血的戾气。
赵高怔住了,他不过恭维了一句,怕是恭维错了;后边跟着的奴才也很少见嬴政如此生气,一群人吓得全部都跪地,连连磕头:“陛下息怒、陛下息怒。”
他之所以这么生气,不是因为右相的那一番话太过落了他的面子,反而是要找到一个敢否决自己意见的人,居然还只是外邦人!他庞大的中央养了这群大臣有何用?
“滚!”
他脾气一上来,自己也压不住,出声便是怒吼。
跪了满地的奴才怎么可能就这么跑了,那会死的更惨的!
此时,咸阳城外的集市人来人往,异常热闹,马车声、呦呵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
一名灰袍男子带着弟子往酒楼二楼上走,抬头正见楼梯口一个熟悉的身影。
“侯兄。”
被点名的男子本是计划众人饮酒我独乐呢,一听到熟悉的声音在呼唤自己的名号,转头,眯着已经快要迷蒙的眼睛望去,满脸沉醉地笑道:“是卢弟啊,快,快这边请,同我喝上两杯。”
卢生来到侯生正对面坐下,这才看到了他满桌子的狼藉模样,花生遍桌,酒樽也东倒西倒的,这该得是喝了多少酒啊。
眼瞧着侯生又要拿起手中的酒樽豪饮,卢生赶忙截下,劝道:“侯兄若是心烦气躁,大可到外头找人打一顿,不可喝酒伤了精神,你我下午可还要入宫讲修仙的。”
一听到修仙,已经烂醉如泥的侯生笑呵呵说道:“去他妈狗屁的修仙。给那个贪于权势的人讲什么狗屁道理。”
卢生闻言大惊,四周看了看确定没有其他人,这才敢开口道:“侯兄醉了,有些话就是醉在肚子里也不能随便喷出来,若今天有外人在场,侯兄一家老小堪忧。”
大概由于喝断片了,侯生吐出来的话语都不成条理的:“始皇为人,天性粗暴凶狠,自以为是,他出身诸侯,兼并天下,诸事称心,为所欲为,认为从古到今没有人比得上他。”
由于现在这上面就都是自己人,卢生也就没有看着他,但还是忍不住劝上几句:“皇帝能称霸天下靠的不也是一众大臣吗?侯兄你别想多了。”
“哼,大臣?他用的是官吏!专门任用治狱的官吏,狱吏们都受到亲近和宠幸。你说那些博士虽然也有七十人,但只不过是虚设充数的人员。
丞相和各位大臣都只是接受已经决定的命令,依仗皇上办事。皇上喜欢用重刑、杀戮显示威严,官员们都怕获罪,都想保持住禄位,所以没有人敢真正竭诚尽忠。皇上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一天更比一天骄横。臣子们担心害怕,专事欺骗,屈从讨好。”
见侯生边说着还边往自己嘴里灌着酒,卢生眼疾手快地将酒樽夺下,蹦的一声摔在桌上。
“侯兄,你该醒醒了,要不我让酒保帮你打盆水上来洗洗脸?”说着,卢生起身便要去唤酒保,侯生却又像橡皮糖一样黏住了他:“没,我没醉,你听我说……”
喝醉酒的人最是难控制,卢生也终于是知道了这其中的百般滋味,被缠住分不开身子,也只好乖乖地重新坐下。
“你可还记得秦法规定,如果方术不能应验,我们该面临什么样的处置吗?”侯生晕晕乎乎,但还是甩着脑袋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