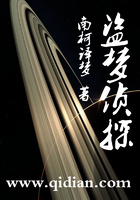高三的寒假,那个漫长寒冷的冬天让很多人浪离在外无法归家,我的爸爸也差一点离开了我,他是被烧伤的,厨房的媒气泄漏引发的爆炸,镇医院看见伤势太过严重不敢收,辗转转去市中心医院。
全身多处烧伤,面积约为百分之四十。
我赶去医院时手术已经完成,我这辈子也忘不掉我爸像一具干枯烧焦的尸体躺在icu里奄奄一息垂死挣扎的的场景。
恐怖的,渺小的,卑微的,无法接受的。
病菌感染,一系列的并发症接踵而来,连日来大量抗生素使得他整个人昏昏沉沉,挣扎在生死边缘,生命那么脆弱与无奈。
我妈整夜整夜提心吊胆的守着。
在我爸昏迷不醒的那段时间,我们用光了家里所以的积蓄,也借遍了所以的亲戚好友,可面对巨额的医疗费,所有努力都只是杯水车薪。在毫无办法下,我们只有转回镇医院,也许上天听到了我内心的祈求,爸爸在转院的途中奇迹般醒了过来,我埋头放声大哭,想要向他倾诉这一个多月来的害怕与无助。
每一次换药对我爸是巨大的痛苦,漫长而艰难的,是我无法体会的剥皮抽筋般的疼痛,隐忍的呜呼声里,我坚受不住躲进厕所里闷声流泪。他无法像正常人通过声嘶力竭宣泄疼痛感,因为吸入大量的有毒气体,声带严重受损,至今无法恢复,甚至于下半辈子都将会是个无法自理的残疾人。
整夜的无法合眼,止痛药似乎并不起作用,黑夜漫长难捱。
所幸的是他活着,一切都在好转,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生命还有盼头。
妈妈从家庭妇女成了工厂小工,白天要上班,晚上要照顾爸爸,这个家所有的重但全部由她来抗。
一整个寒假我都只是往返于医院和家,病床上的爸爸已经在逐步恢复,能够进行简单的摇头点头。
我小心的垫高他的枕头,一口一口的喂汤。
爸爸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平时妈妈叫我把刚买回来的排骨和藕煲汤,我也不会,偷偷的叫来爸爸帮忙,他虽是口头教授,有时也气不过我的笨,便上手解决了。
那个无所不能的人已不能够继续为我遮风挡雨,我必须默默扛下一些事情,咽下想说或不能说的烦恼。
窗外的槐树早以不见了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一阵风呼啸而过发出颤抖的声音。
镇上的医院不比市里头医院人多,天还未黑一整栋楼便听不到什么声响。
妈妈一进门,爸爸发出虚声,她轻手轻脚脱下外套,拿着开水瓶出门打水。
她回来的时候我已经醒了,看见她往水盆倒水。
“我出去转转”我起身拉门。
我妈将毛巾投入热水中浸泡,不住提醒:“处面冷,拿上我的外套”
“我不冷。”我执意。
“嗯哼!”爸爸努力的发出声音来。
我回过头拿起外套就冲了出去。
我爸知道我不想看见他身上的伤痕,他认为我还太小接受不了这般触目惊心的丑陋。
住院部的大门口安装的是声控灯,我默默数着它多少秒熄灯,“咚”我跺脚,48秒,足以让人从黑暗的室外走向光明的屋内。
半个小时里只有俩个人经过,其中有个送外卖的。
寒冬的月光格外亮,我都看得见自己的影子。
“你晚上吃饭了吗?”我妈问我。
“没。”
“怎么能不吃饭,以后会得胃病的。”我妈似乎有些生气:“你现在是大人了,要学会照顾自己,如果你也病倒了,我......。”
我打断她:“知道了,回去就吃。”
“明天我要加班,会晚回来。”
“嗯!”我问:“要留饭吗?”
“可能会通宵,我在外面解决吧!你记得明天给你爸煮些流体食物,枕头要垫高,搬不动他的话就叫徐医生。”
“这些话你都说了无数遍了。”
“怎么!现在连你也开始嫌我烦了?我现在是还在才烦一烦你,哪一天,等我不在了看谁还烦你......”
“你烦不烦!”
一个人的废话程度与其快乐有关,妈妈的幸福来自于爸爸,我并个太想当这个人。
我的性格已经开始扭曲。开始明白有种东西比学习成绩更加重要,也许你不会明白追债的年底跑到家里要钱,把玻璃家具都砸了,我吓得直发抖,我妈不敢去拦,我爸默默流泪。正值壮年的家庭顶梁柱没能为妻女遮风挡雨还反倒让她们遭受亲戚好友的欺凌。
那段时间的生活其实像慢性毒药一样,一点一点消磨着我们一家人的心性,平日里不经意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疼痛,然而一旦触及到敏感之处,长久积存的愤懑就会顷刻间一泻而出。
从高一到高三,从80多人到现在的40多人,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离别。
高三的下半学期,那是一段特别难过的时光。
为了高考学校取消了夏季午休的时间,在昏睡中听老师们的课,晚自习由两节增加到四节,我上得头昏脑胀,课间的5分钟全体都趴在桌子前睡觉。
白天是没完没了的复习,晚上是没完没了的试巻,其实我什么也学不进去,只有一次一次的强迫自己,也许只有这么做才可以不必改变一切。
“有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斯蒂芬。金
这句话是在某一本书上看到的,现在深有体会,也只有这句话能形容我心中无数般不舍与挣扎。
这次模拟考我考的非常的糟糕,考BJ是非常渺茫的,我找班主任谈了自己的情况准备放弃高考,班主任勃然大怒:“叫家长面谈!”
我灰头土脸的回答:“我妈没时间上学校。”
“那就让她给我打电话!”
我也明白这种大事他是做不了主的。
想了很久才鼓起勇气和妈妈商量。
妈妈低着头:“你自己决定吧!不后悔就好。”
高考的前几天班主任还是找我谈了:“你妈妈已经给我打电话了,可我想了想应该再劝劝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为的就是这一天,不管考得好不好,至少咱努力了啊!”
“老师你就随我吧!”我找不到言语表达。
他语重心长:“我知道你家里的情况,现在是比较难,可这不是借口!”
“老师,我是上不了大学了,你又何必给我希望呢?”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上不了大学就上不了,那是以后的事儿,现下你还是我的学生,在学校一天,我说的话就要听。”他想了想又说:“这试必须要考,不然你连毕业证书也拿不到。”最后他说:“不参加高考会是你一辈子的遗憾!”
老师说的话我不敢去反驳只有诺诺答应。
我很矛盾,不想改变现状,又不满现在残酷的抉择。大家突然都严肃认真起来,只有我每天都活在战战兢兢中。
一直到高中最后的一天课,每个老师都在讲明天要带什么,要吃什么,不会做的题怎么办,先是邱老师说,再是林老师说,最后一节课班主任又重复。
晚上的时候我们在教室举行了告别晚会,前面是各人同学表演的才艺,后面的比较精彩是各科老师的才艺,林老师最喜欢巜金粉世家》唱的是暗香,看来是苦练多年。
邱老师的学历最高,念的是外国文学。
曾老师肯定就是讲笑话,物理老师最有才华拿着已有年月的葫芦丝吹奏的月光下的凤尾竹。
我永远都记得石老师最可忴带着耳机,手拿歌词,把陈楚生的巜有没有人告诉你》唱得是笑料百出,他说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么傻。
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太明白他们其实也不大会表达,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叮咛嘱咐。
那天的两层蛋糕一口都没有吃,慌乱中就满教室都是人潮涌动,几名女老师见势不妙就早早的跑出走廊,我拉着简陌往外跑,地板砖上全是甜的发腻的菠萝啤,脚底打滑,我们俩摔了好几次,班长走过来扶我的时候顺手将一手的奶油全糊在我的脸上,他看着我哈哈大笑,我身上没有纸巾又不敢拿衣服去擦,只有被简陌拉着去找水龙头,这期间又被人踩了好几脚,我抹开右眼的奶油,通过一条细缝看见班主任满脸都是白的,正在人堆中寻找方向。
全校的水龙头都挤满了人,简陌告诉我有个女生在冼头,我们又找去了老厕所那边,那边还没有什么人,就是太黑,她大概是怕我踩到“地雷”,让我站在原地不动帮我清理。
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本来是冼了澡去教室的,现下怕是又要排队等洗澡。
整栋女生宿舍楼更加热闹,从一楼到四楼的楼梯间到处都是水,有人拿着各色的水桶去一楼打水,有几个刚刚凉水冼完头的披头散发结队去冼澡,还有几个大概是班级晚会刚刚散还沉浸在激动中说说笑笑,打打闹闹。
已经过了熄灯时间,校园内依旧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准考证上的我笑得天真烂漫,我看了很久,也想了很多,拿出书包,才装上一半的书,另一半只能抱在怀里。
去办公室时没有人在,没有人也好我实在是没有勇气看见班主任失望的眼神,放下了准考证我就出了校园。
一连半个月我没出过家门,也没有同任何人联系过。
敏婕放暑假来找我,让我去学校拿毕业证,我想了一百个不去的理由却一个也挡不住敏婕拉我的一双手。
校园内一片狼藉,穿过长长的走廊,教室里也只有班主任一个坐在课桌那里。
“石老师”我低着头看着马上要露出脚指头的布鞋。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如果现在地上有一个洞我一定要跳进去,然后躲在里面永远也不要出来,现在只有盯着办公桌前的书心里默念上面的字,希望时间可以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班主任没有说话,抽出一支笔放在签字本上让我签字,提起笔我看见我是最后的一个,班主任拿出证书放在桌面上,我公公正正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拿起证书向他鞠躬。
“以后要是有困难就来找老师”他没有看我。
“老师您别这么说,是我太不听话,让您操碎了心。”我满怀诚意:“老师您多多保重,我走了。”
“走吧!”他大手一挥。
偌大的教室,一个人坐在这里,以后是再也听不见这班兔崽子的吵闹声了,他既感轻松又倍加失落。
寝室里大家早以搬走,门背后贴满了合照的大头贴也都被撕走了。
我的被子被叠了起来,收拾时发现中间夹着一张毕业照。
我站在英语老师的后面,左边是王蒙,右边是方馨,相片的背面有一张纸,和照片一起压的塑封膜里。
那天的太阳很大,阳光照的我睁不开眼,我皱着眉、眯着眼,照片拍的不像我。我只拍了一张毕业照,那段时间我太穷了,我妈没有时间管我,一百块钱我用了一个月她也没发现,我不敢也不想问她要。
王刚和班主任站在教学楼前摆姿势,他这三年来长高了,足足比班主任高了一个头。班主任很快也发现了,他让王浩去找来了几块红砖,然后站在上面特别配合大家的拍照。
毕业照后的纸上写的是照片中人物依次的名字,那潇洒凌厉的字迹,我认得是班主任的,全班一共42个人,加上老师、校长53人。
再见了,我最亲爱的同学们!
再见了,教我育我的老师!
再见了,我最美好单纯的年华!
我们再也不能似孩子般无理取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