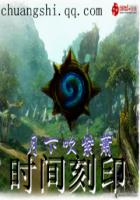竟然是段连祺,明明是极熟悉的人,可菱歌此时却害怕到了极点,只见他快步朝她走来,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眼睛里燃起了一把烈火,愤怒的神色仿佛一匹随时会张开利齿将她撕碎的猛兽。
“魏菱歌,你非要趁着我不在的时候偷偷搬出来,我待你就那么不好?我就这么讨你的嫌?”菱歌只觉得自己的身子僵硬了起来,眼睛盯着他额头上的伤口,瑟瑟的发着抖问,“你怎么受伤了?”段连祺嘴巴里发出一声嗤笑,仿佛愤怒至极,低沉着声音说道,“你还知道关心我?你可知道我听说你一个人搬走了,去向不明的时候有多么着急?”菱歌稍稍镇定了一些,轻声说,“我没有办法,没有理由再赖着你。”说话时轻轻的挣扎着,试图将手抽回来,却被他越抓越紧,仿佛一对手腕要碎在他手心里,疼得她倒吸了一口冷气。
只听段连祺怒道,“你需要什么理由?从前我不勉强你,是因为我敬重你,我步步退让也是害怕太直接反而伤了你,今天我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你,我爱你,这便是最好的理由。”菱歌仿佛陷入了梦境里,不可置信似的看着他,却见他的眼神无比灼热,仿佛可以将她瞬间点燃。她怕极了这感觉,不由得哀求道,“你放开我,你受伤了,我帮你弄点药……”话音未落,他的唇已经贴了上来,带着不可拒绝的霸道与占据,像是要将她吞噬进身体里。
领子露出的一小节粉白的脖颈被他揉得发红,菱歌只觉得自己仿佛就要窒息了,却贪恋着这种霸道,贪恋着他身上带着热气的烟草味道,在这样孤寂的世上,唯有这一点霸道与热烈可以带给她一直企盼的安全感,可残存的理智仍旧提醒着她用力的挣扎着,她伸手推他,他胡乱的抓住她的身子,纠缠间颈上那串粉红色的珠子被他一把扯断,顷刻间一颗颗珠子跌落在地上,胡乱慌忙的跳动着,嗒嗒嗒嗒的响个没完。那样安静的房间里,每一颗珠子都落在了他心上,每落一颗心头便疼痛一次,直到那珠子终于不再跳了,滚落了一地,他才终于放开了他,看着她唇上被自己啃咬的痕迹,心上不禁内疚方才的无礼,可他不愿道歉,她本来就应该是他的,这只是迟早的事情。
菱歌好不容易站直了身子,一颗心还正狂乱跳着,抬眼又看见他额上的伤,也顾不得喘息,忙回身去手包里取了手绢,湿了些水替他擦了擦伤口,冰凉的帕子敷在滚烫的伤口上,段连祺只觉微微的疼痛像蚂蚁一样啃咬在他心上。恍惚间想起七岁那年,他在院子里骑木马摔了一跤,膝盖破了个口子,小小的人儿偷偷拿了一罐药粉,躲在床上胡乱的给自己上药,眼泪扑簌簌的掉在绒布褂子上。二姨娘在佛堂里抄经,母亲忙着在前厅陪军中将领的夫人们打麻将,只有大太太发现了他,帮他细细上了药,又用自己的手帕替他包好了伤口,段连祺还记得,那手帕是极淡的绿色,绣着白色的小花。
后来他独自一人在英国长大,身边从来不乏软玉温香,但此时菱歌一双柔荑带着细微的冰冷,眸子里漾开了一汪静谧的清泉,却是他从未体会过的温存美好,一时间竟然有些意乱情迷。但见一缕碎发从她耳际滑落,终究忍不住将她拉进了怀里,轻轻的磨蹭着她的鬓发,在她耳边笃定的说,“就算你逃到天边去,我也能把你找回来,这辈子你总归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了。”
菱歌此时方觉自己累极了,伏在他胸前听着那脏器有力的跳动着,低声问,“你到底怎么受的伤?”段连祺摩挲着她的背,带着怜爱的嗔怪道,“还不是你闹的,我打电话回来找你,下人叫不来,才说漏了嘴,我一急,自己就开着车从奉阳赶了过来,路上累极了,一晃神的功夫就撞上了路边一个行人,脑袋被方向盘碰了一下。所幸被撞到那人倒没什么大事,已经吩咐人去看过了。”说着,仿佛无可奈何似的轻叹了一口气,说道,“菱歌,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
他如今傲睨半壁江山,是世人眼中仰望不及的一个人,按理说天下的财富宝物皆是唾手可得,可他却说出这样孩子气的一句话,他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可这确是他此刻的心声。
他总觉得,她是他命中抓不住的一只流萤。
菱歌闻言,于甜蜜之中生出一种惊恐,忍不住道,“你和我天壤之别,终究是不可能的。”段连祺淡淡的一笑,说道,“只要你愿意,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菱歌,我不愿意这权力地位成为你我之间的障碍,若是如此,我宁愿和你一起做一对普通的牧马夫妻,粗茶淡饭,相伴终老。”菱歌见他一双眼炯炯的望着自己,那眸子里的深情与恳切,让她没有办法拒绝与怀疑,可她终究不敢相信,此生他就这样认定了她?
总归是短暂的一生,如果不是早有定数,怎么会在这样落魄的际遇中遇见他,既然遇见了,为何不能趁着这最好的年华,和他好好爱一次?若能一起终老,自然是世上最美好的事情,就算缘分浅薄,不得善终,起码爱过一场,也不辜负彼此这一刻的情深。
这样想着,仿佛胸中生出了一股无由来的勇气,揪着他的衣襟,低语道,“我从小就赖皮,你若是把我留下,这辈子怕是就撵不走了。”
段连祺闻言大喜,脸上浮起一抹孩童的笑,畅快道,“除非我死,否则这辈子谁都不能把你从我身边撵走!”
菱歌恼了他一声,说道,“不许总把生死挂在嘴上。”
段连祺也不说话,只笑吟吟的看着她,满心的欢喜仿佛要从眼睛里满溢出来,菱歌被他看得心上一阵乱,别过了脸去望向窗边。原来已经是十四了,天边一轮圆盘似的月亮高高挂着,四下里静谧无声,只有微微的风声拂过耳际,仿佛极遥远的一阵歌声,轻轻浅浅的,忽而又想起那日在台上为莺儿伴奏时她唱的那首歌,大抵这就是注定的了吧。
段连祺从她身后悄悄走上前来,把她环抱在怀里,月色洒在苍茫的大地上,街道上的行人们都变成了一个个影影绰绰的水印子,格外不真切。菱歌天真的想,或许多年以后,那些不甚真切的水印子里头,也会有一个属于他们的所在,平平淡淡的过着普通的夫妻生活,相伴终老吧。
这样想着,她把头靠在他胸前,只愿这一刻,时光能永远的静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