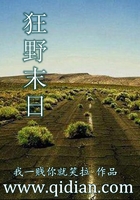萨尔置备酒席的地方在一处偏远的客栈。这里地势平坦,向北渐低,春秋季节风沙极大,几座土坯房连同栅栏组合起来的客栈就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大荒地上,颇显荒凉。
客栈虽显破旧,却是当年萨尔率部族与大魏贸易中途时常歇脚的地方,且这里位置适当,不至让双方觉得尴尬。
一路上,云海向儿子讲述着他与萨尔的传统友谊,并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他与萨尔的默契,希望两家情谊能够世代星火相传。同时也希望此行能打探出些许敌情。军镇虽大部是新兵,可再不出兵,练兵何用?
但云翔却认为大敌当前,无论如何此行太过冒险,与萨尔交情再好,终究是敌人。父亲身系一方军镇,自身性命岂可儿戏?
灵活变通是老将的能力和对世间的参悟;直率刚健是小将的性格和对当下的理解。
众人行至一处矮山头,已经能远远望见那家点有篝火的客栈,云翔心生一计,对着云海说:“父亲,儿愿领一亲兵在此放哨,一旦有变,进可掩护退可求援。”
几个时辰后,云翔这一看似多虑的行为不仅挽救了他的父亲,甚至拯救了整个怀荒军镇。
云海微笑着点了点头,儿子周全的行事方式令他赞赏,无论如何留个观察哨是正确的。
云翔又对陈参军行礼说道:“陈参军多加小心,务必确保父亲安全!”
目送着父亲骑马朝渐渐走近客栈,云翔的心中忐忑不安起来,但又心存一丝侥幸,唯愿父亲顺利赴宴,尽早平安返回军镇。
在云翔不平静的内心深处,是一种不曾有过的恐惧。
云翔虽是大魏边镇的校尉军官,一个威风凌凌的准将军,一个砍过人头、踩过尸体,在外人看来不怕死的硬汉,却在父亲以及全军镇的生死攸关面前恐惧了。
他不知道那可怕的后果会何时到来,但他知道,一旦父亲遭到不测,军镇便群龙无首甚至彻底瘫痪,指望那没用的监军是没用的。
此刻,就在云翔立在客栈不远处山头独自心惊胆战瞭望的时候,柔然王子吐贺真也已经巡视到萨尔所在的部落大营。当被告知部落首领萨尔不在大营而是去找老朋友叙旧后,吐贺真大怒:部落即将开拔北还,而首领却不在大营的指挥位置,简直荒唐可笑!
于是吐贺真马上做出了部署:向大营外多个方向包括怀荒军镇派出斥候瞭望观察;大军随时待命,部分骑兵出营列队,与吐贺真保持五里距离,随时接应;自己则带着所属的百余精骑亲兵外出寻找质问萨尔。
年轻的吐贺真要当面问个究竟:这么晚了,你丢下部众,到底要干什么?
另一边,云翔的恐惧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消散,反而越来越坐立不安起来。
不行,在此坐等不是办法,必须马上调集军队接应,无事最好,一旦有变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于是,一向行事谨慎的云翔在交代了几句后,就独自留下哨兵,纵马跑回了军镇。
军镇早已开始戒严,监军拓跋赤传令众将齐聚军镇主帐,各兵营没有命令不得擅自调动一兵一卒。
拓跋赤在等待着一切关于云海的消息,一旦有变,他会毫无顾忌的夺取指挥大权,然后上表朝廷云海忤逆,将其革职问斩。
这是拓跋赤多年梦寐以求的心愿!
云翔快步踏进主帐,他没有想到拓跋赤的动作如此之快!
“云校尉”,拓跋赤大声呵斥道:“你可知罪?”
云翔拱手道:“不知监军所谓何事?”
“少废话!左右!”拓跋赤唤道。
“在!”
“拿下!”
未等坐在主帐内的众将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拓跋赤接着起身吼道:“别以为本将不知,白天有几个柔然奸细前来通风报信,夜晚镇主便和你等外出,若非有不可告人的阴谋,何故不知会于我?本将在此监军,就是为防止你等小儿犯上作乱。说,镇主外出是否出逃?还是有其他目的?”
“事关机密,过后便会知会监军!”云翔已经被两个士兵抓住臂膀压在了地上。
“连本将都不能知晓,看来真是要投敌啊!”拓跋赤长叹一声,道:“看来到能知道的时候,本将恐怕已经人头落地了!将此等忤逆小儿拖出去砍了!”
众将本就云里雾里地被传唤到了军镇主帐,见此情景,也都明白了一二分。军镇里大部分将军都是随镇主将军云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生死弟兄,怎忍心见死不救?于是纷纷站出来说情:
“监军,此事事关重大,还请查明真相后再做定夺!”
“求监军放过云校尉,现在镇主将军安危尚且不知,别错杀了好人呐!”
见诸位将军求情,拓跋赤也好有个台阶下。吓唬吓唬就行了,有把柄还怕你跑了?此外,毕竟有朝一日大权在握,还得靠大家支持才能搞好工作,大家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拓跋赤道:“既然众将求情,本将暂且饶你不死,但你活罪难逃,先押入大牢,明日上表交予陛下发落!”
“不”,云翔昂起脸正色地说道:“父亲为了全军镇的安危,亲自犯险,所带亲兵不多,在下回来就是想再调些部队,也好有个接应。”
“放肆”,拓跋赤对着云翔大声吼道:“本将不治你的罪已经网开一面,你居然胆敢要求调兵?”
未等拓跋赤说完,云翔马上道:“请监军相信父亲,他实属无奈才以身犯险,不是投敌,更不是开小差。我云家世代忠良,才不会做那等忤逆之事。请监军明察!”
就算云翔心知肚明拓跋赤是故意找茬,也只好先放下身段,毕竟调兵才是当前第一要务。
此时,各位将军已经大概知晓事情的梗概,即便在开会前拓跋赤已经说了镇主将军可能会出逃,但也没有人会相信。
“报——”,此时,一斥候来报:“报监军,有一支百余人的柔然精骑朝镇主将军所在的客栈围拢;另我军镇正面的柔然大营有军队调动。”
“再探!”拓跋赤命令道。
“诺!”说完,该斥候飞奔而出。
拓跋赤得意地笑起来,他想向众将证明自己的判断。对于一个无知的人来说,此时他最关心的不是军镇的安危,而是云海的生死。
在他看来,一旦镇主变节或者马上死掉,那个军镇里最高的位置便唾手可得。
“云校尉,你还有什么话说?我怀荒军镇的大营布防和兵力部署你爹最清楚,一旦投敌,我军镇就会有覆亡的危险!”说完,拿起令牌,高高举起。
见此情景,主帐内的将军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不忍看着云翔丧命,更不能就镇主将军的生死置之不理。于是纷纷起身求情,也都是请监军网开一面之辞。
拓跋赤无奈,想再次做个顺水人情,便向云翔问道:“也罢,既然众将求情,本将便饶你不死。不过,要说调兵,你可有虎符?”
虎符是古代皇帝调兵的凭证,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伏虎的形状,劈为两半,一半在皇帝手中,另一半交给地方将帅,只有两半契合方可调兵。而且必须是专符专用,一地一符,决不可用一个兵符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
“虎符在父亲手中,皇上将另一半符也交予父亲,授予调兵之权。”云翔一边说一边懊悔,分手前竟忘记要上虎符。
“哼,你口说无凭,要本将如何相信?”拓跋赤道。
“待父亲回来定然分晓!请监军速速调兵予我,救父亲于水火,不然就来不及了!”云翔近似哀求道。
“休得多言!云校尉,本将暂且不杀你,但你也别得意忘形,不会交一兵一卒予你,有本事带回镇主,道明原委。过了今晚,本将可就要禀明陛下,那时你们可就是通敌叛国之罪!”说完,命士兵放开了云翔。
云翔自知不可能再要得救兵,拱手后便不再多言,退出主帐。
“云校尉,云校尉!”
云翔沮丧着回头张望,见独孤信紧随自己跑了出来。
“独孤营主,你怎么出来了?”
“在下借口如厕跑了出来”,独孤信拍着云翔的肩头说:“下一步怎么办?”
见云翔低着头不言语,独孤信道:“随我到我兵营商议!”
两匹战马驮着两个军官在夜色中疾驰,快到第九兵营的时候,站岗执勤的一名新兵不明就里,高喊道:“军镇戒严,下马核查!”
独孤信没好气地吼了一声“滚开”,便领着云翔纵马入营。
在帐外,独孤信对云翔说道:“我第九兵营愿誓死追随镇主将军,只要校尉一声令下,在下马上命令部队开拔!”
“不行”,云翔推开了独孤信,道:“监军已经下达了戒严令,一旦你调兵,则属私自调动兵马,要杀头的!”
“那你说怎么办?嗯?是在下的性命重要还是镇主的性命重要?还是全军镇将士的性命重要?难道你要看着监军误我军镇吗?”独孤信动情地说道。
“那也不行,我不能陷你于不义!”云翔道。
“你我多年生死兄弟,多少仗我们都挺过来了,况且镇主对在下有知遇之恩,此时不报,更待何时?”独孤信握住了云翔的手,坚定地说道。
“在下有一策,不知二位愿听否?”
云翔和独孤信同时回头,看到大帐旁一个身影窜到了身前。
“放肆,胆敢偷听我等讲话!”独孤信怒道。
“从开始戒严在下就感觉不大对头”,这个士兵继续说道:“刚才路过,听到二位谈话,心中自知一二。不过在下有一策,虽有风险,但确保镇主将军无恙!”
独孤信一眼便认出了此人乃是前几天检阅时候选拔的九夫长,竟一时心急想不出姓名。
云翔早已六神无主,看此人如此淡定,倒想听听有何良策。
“在下听闻营主擅长牧马,敢问可有此事?”木兰道。
“你如何知道?”独孤信问道。
“也是传闻听得”,木兰拱手继续说道:“我第九兵营有骑兵三千,战马三千。既然军镇命令不得调动一兵一卒,却未说不得调动马匹啊!”
听得独孤信一拍脑门,道:“对呀!”
“我营帐有死士二十人,个个愿随云校尉和独孤营主出战”,木兰的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目光,如能成行,这将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作战。
此时,在客栈内,几番觥筹交错,云海已有了醉意,他已经听到了外面的战马嘶鸣声,想着云翔在外的岗哨,云海唏嘘不已。
萨尔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自己并未调兵,怎么会有那么多马蹄的声音?他唤来侍从,想问个究竟。
但似乎一切都晚了,吐贺真已经走进了客栈。
一场兄弟之间的夜宴瞬间变成了两军之间的鸿门宴!
萨尔慌忙起身,向吐贺真行礼道:“不知王子深夜至此,有失远迎!”
吐贺真也不客气,直接说道:“纥奚王,深夜有酒喝怎么也不叫上本王!”
见萨尔不言语,吐贺真继续说:“我们都是大汗的勇士,是草原上的雄鹰,怎料此地还有一群大魏的羔羊。看来鲜嫩无比啊!”
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哈哈哈哈,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原来是柔然王子,爱吃羔羊却乳臭未干,牙口还没长全吧?”云海和颜悦色地将吐贺真的犀利化解。
吐贺真的侍从听得不由火冒三丈,欲上前动手,被吐贺真扭头使了个眼色拦了下来。
“不要逞口舌之快”,吐贺真对着云海说:“本王发现你们汉人就爱动嘴皮子,死到临头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来人!”
说着,从客栈大门涌进来二十几个柔然武士,将宴会场团团围住。
云海自知回天乏术,无论如何凭自己这十来个人是冲不出去了,也不知云翔的救兵几时能到!或者根本就搬不来救兵,虎符还在自己身上,那拓跋赤怎肯搬救兵予我!
正思索间,云海看着萨尔眉头紧锁的表情,他知道萨尔在飞速地思考脱身的良策。凭着对他的了解,他是不会出卖自己的。
此刻,剑拔弩张的双方都知道对方是一块大肥肉,只要自己将对方生擒或是刺死便是大功一件。但谁也知道不能轻举妄动,一旦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果本王没有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魏怀荒军镇的镇主云海将军吧”,吐贺真显然没有干掉云海的意思,道:“大魏不过是鲜卑人所创,也不是你们汉人的国家。不如云将军投奔到本王帐下,本王可保你高官厚禄、荣华富贵!”
“呵呵,王子真会说笑!我大魏如今一统北国,百姓安康。谁想你柔然一个草原部落竟然不知好歹,屡次犯边,搞得我大魏子民民不聊生,本将恨不得将你们碎尸万段,还投你帐下,简直是痴人说梦!”云海大义凛然,不卑不亢。
“既如此,就休怪本王不客气了!”说完,示意手下将云海等人拿下。
柔然武士一拥而上,客栈内顿时乱作一团。萨尔假装挥刀上前,朝云海使了个眼色,云海用剑格挡,迅速闪开,绕到萨尔背后,一把抓住他的脖颈,把刀架在其脖子的动脉处,大喝一声:“都别动!”
吐贺真看到萨尔被擒,赶忙喊道:“住手!住手!”
萨尔趁机发挥,忙喊道:“王子救我!王子救我!”
“放开纥奚将军”,吐贺真有些着急了,道:“本王可放你一条生路!”
“王子殿下”,云海不无调侃似的说道:“你当本将也乳臭未干?会相信你的鬼话?休得多言,马上让开一条路!”
还未等吐贺真挥手,客栈大门处陆续让开一条通道。云海一行人与吐贺真的柔然武士对峙着走出客栈。
看到云海没有放人的意思,吐贺真没有让栅栏处的武士让开,而是将云海等人团团围住,最外面一层士兵都跨上了战马。
“云将军,看来我们这次插翅也难飞了!”陈参军凑过来对云海说道。
“别怕”,多年的厮杀使云海显得格外冷静,说道:“大不了鱼死网破!”
事已至此,吐贺真仍不忘对云海进行策反:“云将军,你这样没用,你是出不去的!放开纥奚将军,本王已经看到了你的实力,不如与本王一起做大事吧!”
“放我等出去,本将一定保证纥奚将军的安全!”云海道。
吐贺真还欲喊话,却扭头听得远处一阵阵号角声,此起彼伏。接着,听到一群骑兵朝自己冲杀过来。
“王子,有大魏的骑兵”,一个侍从道:“不过好像人数不多,十余骑而已!”
柔然人自小在草原长大,成天听得都是马蹄的声音,因而一个娴熟的骑兵能够轻而易举地从马蹄声中判断出战马的数量。
“不要慌”,吐贺真故作镇定,说:“本王就不信他大魏十几个骑兵就敢朝这里冲杀!”
吐贺真有理由相信,自己带来的一百余骑亲兵都是柔然军中的精锐,骑射、劈刺样样在行,他们简直是柔然军中的娇子。有他们侍从自己,定能化险为夷。何况听马蹄声对方只有十几骑,冲过来不是找死吗?
“不,王子”,身旁的侍从惊呼:“不是十几骑,远处似乎有——上百骑!”
客栈院子里的篝火将四周照的通亮,却掩盖了远处的夜色。月光并不皎洁,这样的夜晚一眼望去,竟是黑压压的一片。
吐贺真分明能感觉到,大地在颤抖,连小石子都能悄悄蹦跶起来。这样的氛围不是十几个骑兵所能够渲染出来的。
“报——”,一在远处警戒的柔然军官纵马来报:“禀王子,西南面有大队骑兵来袭,看不清楚,但听马蹄声约有上百骑!”
吐贺真倒显得并不慌乱,他自幼外出征战,在柔然人看来,他简直就是个天赐的武士,专门为了应对大魏而出生到草原上的。他想建功立业,为柔然人获取利益,没想到今天遇到了这么大一块儿肥肉,更没想到的是大魏地反应如此之快。
想吃吃不下,想走舍不得,真是鸡肋啊!
然而大魏的骑兵似乎不会给自己抉择的机会了,前锋的十余骑已经到了吐贺真肉眼能够观测到的范围。即使是黑影,也能看到微微亮闪的铠甲。
“蠕蠕休走——”木兰纵马扯高了嗓子吼道。
“蠕蠕休走——蠕蠕休走——”紧接着,云翔、麻奎和其余的伙伴们也都高声叫喊了起来。麻奎看到柔然人更是愤怒异常,想到自己被杀害的亲人,不由加快了行进速度,高喊着欲杀之而后快。
“蠕蠕”是北魏皇帝拓跋焘给柔然起的绰号,拓跋焘认为柔然人是一群智力低下、不会思考的虫子,故赐此名。该绰号一经起草,迅速传开,瞬间成了此时木兰等人忽悠吐贺真的王牌手法。
方才警戒的柔然军官听得怒火中烧,看到吐贺真挥手下令,便准备掉转马头领着最外一层的骑兵冲杀出去。
木兰看着对方有异动,立刻拉弓搭箭,迅速将弓箭射出,看得云翔好不惊奇!弓箭飞出,借着客栈门前篝火的光亮,在前方画出一个浅浅的、漂亮的弧线。
还未等柔然军管完全调转马头,他便应声栽到了马下。
整个场景一气呵成,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却看得吐贺真张大了嘴巴。
“王子”,身旁的侍从再一次打断了王子,用手指着侧翼道:“听,魏军的大队骑兵并未朝我冲来,而是在向我们身后运动!”
“不好”,吐贺真这才恍然大悟,急忙说道:“魏军是要包抄我们,快,上马!”
听闻吐贺真的命令,原先包围云海的武士纷纷跑去跨上战马,先前最外层的骑兵朝吐贺真围拢过来。
“蠕蠕王子,休要跑了,我大魏精锐马上就将你等围困,跟着本将征服草原吧!哈哈哈哈!”望着远处的大魏骑兵,云海来了兴致。
“王子,顾不了那么多了,在敌围定前赶紧冲出去吧!”一柔然侍从道。
“好”,吐贺真扭头对云海说:“今夜本王饶你不死!不过别忘了你刚才说过的话,待本王撤去,就放了纥奚将军!”
百余柔然骑兵随吐贺真仓惶北去,伴随着阵阵马蹄声消失在了夜色当中,只留下了孤单单的纥奚萨尔。
架在萨尔脖子上的刀在吐贺真走远才放下,云海冷冷地说道:“你们未来统帅的豪情就全都留在你身上了!”
“哈哈,云将军说笑了,他只是草原上一只稚嫩的刍鹰!在生死面前,他只知道他的性命最金贵!”萨尔无奈地笑道。
望着远去的吐贺真和远去的百余柔然骑兵,云海攥紧了拳头,内心充满了愤恨。他知道,为了身边自己随从的性命,不能轻易冲上去送掉性命。况且自己一干人的战马都被对方牵走了。他只能静静地等待,等待援兵的到来。
不一会儿,云翔、木兰等人就骑马在客栈前立定,见云海毫发未损,才长舒了一口气。
“父亲”,云翔喊道:“快快上马!”
此时云海才看清,原来冲过来的骑兵还每人牵着一匹战马。
“来了多少人?”云海着急地问道。
“二十余人!远处是独孤信在牧马!”云翔道。
“你们可真够胆大!此地不可久留,按照常例,柔然会有大队骑兵在后策应,随后就到,一旦让他们知道我等的虚实,就什么都来不及了!快撤!”云海下令道。
独孤信和司马楚等人牧马还在向北纵深奔驰,见身后客栈方向示意的火把信号,独孤信一声口哨,几个骑兵架马向右迂回,将牧马群扭转方向,逐渐朝南驶去。
“萨尔兄弟,你我后会有期!”云海大声拱手道。
“后会有期!云将军先行一步,兄弟在此等候王子,他还会回来的!”萨尔道。
“回军镇!”云海大声命令道。
“诺!”
“等等”,云海再次勒住战马,问道:“刚才那一箭是谁射的?”
“是在下!”
“你叫什么名字?”云海问道。
“回禀将军”,木兰行礼道:“在下虞城花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