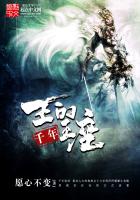他躺在黄沙之上,只有乌黑的眼睛不时转动着,望着风云难测的天,海市蜃楼中映出女子昔日如花的笑靥。
边上偶尔路过骑着骆驼的几个商人,踩在这片柔软暴热的土地上,他们都穿着富贵的衣裳,可是这里离人烟处还有很大一段路程,苦于寻不到水源之地,无论有多少钱财都如粪土一样无用。
骆驼圆圆的眼珠转动,那些商人也看向他,有商人说道,“看,那里有个疯子,这么热的天气躺在那里不是找死吗?”
“可能是脑子有什么问题。”他旁边的人用手指了下自已的头哈哈大笑道。
“反正他也要死了,那我们把他的水壶也拿走吧!”那商人心动道。
旁边一个背琴的中原男人有些不忍,“你们怎么能这样,这不是害人性命吗?”
叶良喜闻言转过头,从迷惑心智的幻像里走出,不解的望过去。
那背琴人一生也望不了那一幕,看着他的少年有着明亮如星的眼睛,可眼神却是空洞无光的,他还年轻,还有大好前程,可好像生命就交付在了这荒漠之中。
也许他永远都不会懂少年有着怎样的人生,叶良喜说道,“你们要拿就拿走吧,这水我不用了。”
他抬起黑色的布履将水踢给那个背琴的人,此刻他只想走入黄沙之中,与蛇虫蝎蚁相拥才是他最好的归宿,背琴人目露感激,可是看到叶良喜身边只有一个水壶,这离水源之地又那么远。
“那你怎么办?”
“他们说的没错,死人是不用喝水的。”
叶良喜转身向荒漠深处走去,幽黑的目光深遂的说道。
几个商人用着奇奇怪怪的口音交谈,他们其中有人用拗口的口音对着叶良喜大怒说道,“这个人,这个中原人他不是和我们一道的,你怎么将水给他了。”
“为什么?”他展开笑容,黑色的衣料如墨,面容却纯净无波,干裂苍白的嘴唇启合说道,“心黑的人自然也不需要水,你们难道没有看到他已经严重脱水了吗,这水壶内的水是救人性命的,而不是给你们解一时饥渴的!”
几个商人气得想冲上去,奈何叶良喜已走向了沙漠深处,越来越小的身影仿佛还在讥讽他们的贪念,骆驼依旧睁着圆圆的水亮的眼珠。
聂柳赶到时,他已经走了几个时辰,只剩下头和手还留在外面。
“少主!”
他用手扒开沙土,再晚来一刻,叶良喜已经被流沙掩埋,死神的旋涡,是那样不容情的吞噬着人的生命。
“就这么想死?”他将少年抓出来,眉露怒气问道,“难道性命就那么不值得你珍惜,名门正派究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骨肉亲情都可以不管不顾,起来!老教主和教中的人都还在等你回去。”
“什么魔教的少主。”叶良喜挥着手刀打断聂柳的拉扯,如置身梦里,捂住头目露惊恐喃喃说道。
“我弄丢了最重要的东西,她突然不见了,还是我亲手害了她,你知道这种感受吗?”他像是重病的人捂住嘴开始猛烈的咳嗽。
“我没有那样一个人,也不需要。”男子冷声说道,可心中突然浮现女子的笑容,她会做精巧的糕点,会玩笑般的说,聂柳,我喜欢你。
他年纪不小了,寻常人也许早就该有了儿女,但是他知道自己终其一生都会守着天罗教,不做他想。
在这江湖的乱世纷争之中,世上的人都只是是区区蝼蚁。
聂柳突然有些了解了叶良喜,这个可怜的少年,他游荡在这个世上,只能当别人的棋子。
“是为了那个女人?”
叶良喜突然抬起头看向他,目中满是惊诧,随后又抱着膝自责说道,“师姐被空空子掳走了,是我没有照顾好她。”
他弯腰咳个不断,聂柳又急又气眼皮也跳个不停,实在是看不惯一脚踩在他背上,“如果你还想救他就收起这副懦弱的样子,这方圆数百里只有一处客栈距离荒漠最近!””
他被踏了一脚促不及防,突然倒在地上重重的喘息,在聂柳被他惊吓的收回脚以为他要将心肺都咳出来时,叶良喜突然弯腰吐出一团夹杂着鲜红的血的黄沙。
横福客栈的一间房内,花瓶里插着新鲜的花朵,房间内的床上绑着美丽的女子,她的面前是丑陋的朱儒,江云清睁着明亮如水漆黑似墨的眼睛,冷冷的说道,“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你不会觉的恶心吗。”
空空子改了之前的笑容满面,咧着嘴角阴沉着脸,“你这么漂亮当然不恶心了,更何况小娘子断了我一条手臂,我总该取一些需要的东西吧!”
江云清冷笑道,“可我觉的你恶心!”
矮小的人还不及床塌高,单手叉着腰仰瞪着坐于床上的女子。
他得了一种怪病,怎么都长不高,被有钱人收买,因为身形的伶俐成为了最敏捷的杀手。
曾经,在穷苦的乡下也有喜欢的女子,可是她因为他身形的矮小看都不想看他一眼,眼前的美丽女人和那个乡下女重合起来,她们是那样的相像同样说着,“我觉的你恶心!”
“没关系,反正你马上就会和我一样肮脏。”空空子疯狂起来,他扯开江云清的衣服,发现颈处有一道伤痕,刚想要狂热的吻上去。
却被踢了下去,原来江云清说了那么多话只是为了拖时间,她用内力将绳子挣脱开来,空空子抓住她脚踝,死死不让她动作。
“小翠,不要离开我,小翠,我会赚下许多的钱来迎娶你的。”胖胖的矮子滑稽的样子很是好笑,仅有的一只手用来抓住她,用身子在地上爬,布满沧桑的脸上已生出了满满的皱纹,说着央求的话。
江云清心中悲悯,原来是将她当成了别人,她想抽出脚,却因为伤重,背后的伤口又开裂开,一时之间竟无法挣脱空空子。
门被从外踢开,空空子惊恐的睁大眼看向来人,这里没有沙土,再也处逃离藏觅。
叶良喜看到江云清被牢牢束缚住,拔出剑,狠狠的刺下去!鲜红的血飞溅上来染满了他变的冰冷的面容。
空空子死都没想到他们会找回这里,圆睁着双目看着插在自己身上的剑断了气。
他抽出染血的落拓,以为师姐会夸赞他,满面笑容的看向她,可是江云清说,“为什么?为什么杀了他。”
叶良喜的笑容瞬间消失,惊恐的看向自己的双手,他杀人了,他平时连一只蚂蚁都没有杀过,居然杀人了!
“他只是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而以,我已经砍断了他的手,还不够吗?我们有什么权利夺走他的性命。”
“师姐......,对不起。”他目光惊恐,像极了犯了错的孩子,躲闪着她责问的目光。
“江姑娘,请你不要把名门正派的思想硬加到我们少主的身上。”黑衣男子走进来,抱着剑说道。
“你是谁?”
“天罗教座下护法,聂柳。江姑娘,我们那一日曾有一面之缘。”
还未等他说完,江云清掌风已经袭来,大喝到,“魔教妖人!”她牵动背后伤口,还未等几招,剧痛之下晕了过去,向后倒去。
叶良喜忙扶住她,他动作温柔的轻轻整理她凌乱的发丝,即使在睡梦中,她好似也是不安稳的蹙着眉。
“一个可以让男人活吞沙子差点死的女人,这就是你不肯回天罗教的原因?”聂柳了然的低头看着地上的两人问道,他们一个头面染血,一个身受重伤脸色苍白。
“不,不仅仅是因为师姐,还有许多原因,正邪终究是不两立的。”少年的目光漆黑中布满星辰的亮光,怀中是他心爱的人,他抱着她注视着遥远未知的前方。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想看一看你的父亲吗,他已到迟暮之年,当年与江岸一战,多年伤重迟迟不愈,也许就不久于人世了。”
“那又如何?”
聂柳抽出剑来,风声掠过架在他颈上,“你说什么!那可是你的亲生父亲。”
他被同门嘲笑,被师父下毒,被亲人舍弃,那个所谓的魔教之主又在哪里呢,叶良喜冷声笑道,“父亲?可以将亲生儿子丟给敌人的父亲?”
平坦的大路上,一辆马车踏起滚滚尘烟疾速而行,那车上少年翘着腿,抱着一袋不知是什么点心的东西吃,被旁边赶车的少女时不时的瞪一眼。
丁抚实在是太饿了,她做的东西现在已经让他惧如毒物,只好在路边买些吃的,免的回门派中他又要被她逼迫。
车厢内,江云清靠在叶良喜的身上,“聂柳和你说了些什么,你是不是一定要回魔教去。”
车外的景致飞快的掠过,绿树繁花在他的眼中变幻,阴影照在他俊逸还带着少年人秀美的面容上,耳边女子幽幽的声音好似毫不在意,可言辞中却始终带着挽留之意。
“师姐,你现在伤重,应该回去极剑门养伤。”他满面担忧的对她说道。
她抬起头瞪视着他,语气变的冰冷,“将我送回去你就要走是吗?你我十几年的交情,却不及你魔教少主的权势地位与荣华富贵!”
牵动了背后伤口处又流出血来,染了青衣,他扶住她,面目苍白目光急的说道,“师姐,恩情从不敢忘,可是魔教害我正道多人性命,这其间总要有人了结。”
离那满是云雾的山峰越来越近,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风雨欲来。
“你要做什么,良喜。”她紧张的抓住他衣衫,指甲在他身上都是发抖的,唯恐叶良喜会出事,又怕他会为武林带来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