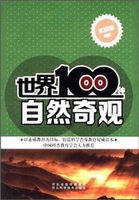话音刚落,眼前的兰珀便幻化成影,扑面袭来,张泊名丝毫不慢,腾空而起,如荒漠秃鹰,一个转身便绕到了紫影后。
紫影缭乱,忽而成剑,忽而成网,忽而消散,忽而聚拢。
秃鹰凌空,忽而启喙,忽而收爪,忽而高飞,忽而俯冲。
鹰击长空,紫霞凌日,各成一番美景,却处处隐着杀机。
突然紫影一旋,漫天间,繁花点点,飘零而下,如紫雪纷飞,悠悠袅袅。
那一片黑色却突然扩大了许多,横空扫荡,将紫雪尽收其中。随即黑影一聚,直冲紫影而去。
一瞬间,紫影不再飘忽,秃鹰也落在枝头,只见泊名的剑停在了兰珀的耳旁,顺着剑锋,几缕褐色卷发徐徐落下,而泊名的黑色外衣却不知何时被他提在了手上,里面似是包裹了什么东西。
“我输了。”兰珀坦然认输,没有丝毫不快。
“承让。”泊名抖开手中的外衣穿上,里面包裹着的一朵朵兰花尽数落在地上。
“真是可惜,从未有人第一次便能破了兰花飘零。张哥哥竟然知道我这花瓣有毒,不然的话,张哥哥只要沾上一片,现在就是兰珀赢了。”兰珀懊恼地跺脚。
“在下纯属侥幸,若不是想起兰姑娘方才说自幼便闻遍花草,可能是使毒高手,或许此时的在下已经是死尸一具了,还要多谢兰姑娘手下留情。”
“放心放心,稍微沾上些毒不会即死,等你浑身肌肤溃烂,少说也要月余才会死去。且若是张哥哥真沾上了这毒,兰珀也会不忍心看张哥哥受苦,会把解药给你的。”
张泊名听到这话,又是一阵疑惑,不知是该觉得兰珀毒辣好还是觉得她单纯好。
“兰珀既然输了,就要履行诺言,张哥哥跟我来,还有这位……”兰珀上相打量了一番郑有成,实在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可以连面部表情都一动不动地站那么久。
泊名抢上前一步道:“不必管他,他正在……入定。”这小子什么时候能不这么丢人现眼……
“入定?”那是这么高深的功夫?兰珀想不明白,干脆不想了,转身走了开去。
兰珀又是在山石上三两下一拍,那道两尺多宽的缝又出现了,张泊名带着终于可以正常行走的郑有成,闪身进入。
本以为里面会是阴暗狭窄的山洞,可两人在里面只走过了一小段,顿觉豁然开朗,这座山背后,竟是一个小小的山谷。
山谷中一间毡帐。泊名轻松放倒了几名看守之后,进了帐去。
帐中收拾整洁,王褒便坐在一张毛毯上,倒不似受了什么亏待,只是手足无力,不能言语,想必是被灌下了类似软骨散之类让人肢体无力的药物,稍作休整应当便无大碍了。
可帐中另一人却是铁锁加身,郑有成看着此人有些眼熟,上前抬起他的头来,不由一声惊呼:“舅舅!怎么是你!”
此人正是内卫司马郑吉,郑吉见到侄儿前来,甚是惊喜,却也是虚弱非常,不能言语。
泊名走上前来,见郑吉虽疲惫不堪,一双眼中却是不屈的神色,不由暗暗佩服,对着郑有成道:“先将人救下来,有什么话回去再问。”
郑有成忙点头,从看守身上搜出了钥匙,救下了郑吉。
张泊名和郑有成一人扛着一个出了山谷,见兰珀还是优哉地站于原地,泊名不禁问:“兰姑娘真要放我们走?”
兰珀用手指绕着头发道:“你们都已经把人救出来了,还有假么?怎么样,我大方吧,除了这第二个玉哥哥,还奉送还你们一个人。”
“可姑娘如此做,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么?”
兰珀笑了:“左右我的功夫是不如张哥哥的,张哥哥要是硬闯进去,我也拦不住,我拼了一身伤还不是和现在一样的结果?那倒不如干脆放你们救人,我省得受伤,你们也省事。”
话是这么说,不过……这个兰执司还真是个奇异的人。泊名拱手道:“那在下就此别过了,兰姑娘保重。”
待张泊名走开稍远,听见后面兰珀在喊:“张哥哥可要记得兰珀啊,后会有期~”
玉门关内,笑尘如期回来和张泊名郑有成接上了头。
笑尘见了泊名,也顾不得放下包裹,急着说:“哥哥,玉衣去了湟水见了先零羌首领杨玉,太子之事,果然是断圯坛和羌人共同策划的,可不知为何,玉衣本就没有打算将太子交给羌人。”
“那羌人怎么说?”从里屋出来一位精壮的中年,急切地问。
“这位是?”
“内卫司马郑吉大人,也是有成的舅舅,我与有成意外救下的。”泊名回答。
“笑尘见过郑司马。”笑尘一礼之后接着说,“杨玉自然很是生气,说是为何预先说好的话不作数,还说羌人已经照着断圯坛的……”说到此处,笑尘不由住了口,看了看郑吉,不知是否该对他透露这些信息。
郑有成忙解释道:“张特使但说无妨,舅舅也是圯桥中人,我就是受舅舅的引荐入的圯桥。”
笑尘放了心,接着道:“说羌人已经照着断圯坛的指示强行东渡湟水,等于和大汉撕破了脸,此时不战也得战了。断圯坛却不照约定把太子交到他们手中,羌人少了一张王牌,便就落入了两难的境地,这不是要把羌人逼上绝路么。”
“那玉衣怎么说?”泊名关切地问。
“玉衣说,太子也不是是个人就能虏来的,我坛丧了五名高手仍是未能得手。目前这个状况,杨统领不妨先做休整,若他日要与大汉开战,断圯坛全力相助便是。”
泊名皱了眉头道:“那便奇了,他们明明受羌人之托虏了太子,却又称未能得手,且若我们没有料错,他们的主力都已回到西域,可千辛万苦虏来的太子反而一直被他们囚于长安。断圯坛如此做法,实在是令人费解。”
郑吉也道:“他们囚禁于我,也正是因为我巡回鄯善之时,碰巧遇见那个玉衣与羌人联络之事。不仅羌人东渡湟水是断圯坛所使,即便更早些的时候,从羌人向义渠大人提议开始,就是断圯坛的教唆。”
郑有成补充:“还有杨大人去的河东那边,不知有没有断圯坛插手。”
郑吉思虑一番,道:“胡乱猜测也没有用,现在我们的消息又多又杂,不如我随你们一同回长安,与杨墩守和尚大人仔细商量一番,再作定夺。”
众人意见达成一致,笑尘正要回房休整一番,泊名往一个房门指了指,道:“尘儿不先去看看他?”
笑尘想了想,茫然地看着泊名。泊名满脸鼓励的神色最终让笑尘下定了决心,点了点头,深吸了一口气,推开门走了进去。
王褒的身体不如武将郑吉,休息了这些天来,虽已可行动自理,却仍是身上使不出力气,此刻正在床榻上,伸出手,吃力地想要拿起旁边桌子上的茶水。
“我来吧。”笑尘取过茶杯,递到了王褒手中。
“笑笑……”王褒一怔,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笑尘见王褒十分拘谨,微微一笑,心道:“子渊现在定是没有心情,不如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吧。”于是说:“子渊,与我说说玉衣的事情吧。”
“玉衣?哦,你说的是小袤。”王褒望向窗外,想起了久远之事。
“小袤与我同为孪生兄弟,幼时的小袤总是比较活泼些,经常会趁读书之时溜将开去,事后再嫁祸于我。可我却也不会生气,小袤若是在外头寻着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头一个便要拿回来给我。爹娘都是读书人,见小袤不求上进,往往要责怪于他,我也会替他求情。其实小袤十分聪明,他的功课不及我,只是因为他的心思不在此处。本始三年……”
说道此处,王褒神色暗了几分,顿了顿才又继续开口:“那年我们八岁,大汉出征迎击匈奴,我们一家当时正在边城,受了战乱波及,粮不足充饥,衣不足抗寒。偏偏小袤此时得了病……流民迁徙,爹娘忍痛留下了小袤。多年以来,我们都以为小袤熬不过那场病,现在我知道他还活着,虽然高兴,却不想他竟成了敌人。这一路上,兄弟相见无语,我比当年与他生死相隔更为煎熬。小袤定是痛恨我们当年放弃了他,他如此对我,也是我自作自受……”
笑尘打断道:“子渊不必想得如此坏,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他对家人仍是有牵挂的。”
“怎么说?”
“你且看这玉衣二字,莫不是从王袤二字变化而来的么?他改了名,却舍不开这名,便足以说明他放不下亲情。正是因为他放不下,才会难以启齿与你交谈啊。”笑尘说到此处,略有深意地看了看王褒道:“正如玉衣那样,子渊,有些事情,并不是一味逃避就能解决的。”
王褒想起了当时自己对笑尘的故意回避,面有愧色,道:“笑笑,你生于天明之时,漫天之中仅有你启明一颗晨星,这整片天空都是你的。而我只是繁星一点,固于自己的位置,不得徜徉……”
笑尘摆了摆手,道:“子渊不必多说了,笑尘只是希望,若子渊有了新曲,能让我在一旁倾听便是。所谓知音,本就是该共赏雅乐,若是形同陌路,岂不叫人伤心。”
王褒带着笑意叹了口气:“那若是笑笑有了合适的词句,也要不吝笔墨,替我填上才好。”
“好。”
一个好字出口,笑尘突然觉得周遭的空气轻了许多,心情也随之畅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