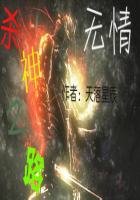那胡人一声喝死妙真子,身形一晃,出了大厅。
齐老大早已醒转,眼见冯均身死,最大的依仗妙真子七窍流血而亡,吓得两股战战,不敢动弹。
那胡人一把提起齐老大,大步向院外走去,同行的两个胡人默不作声,扛着妙真子和冯均的尸体紧紧在后面,转眼消失不见。
过了半晌,众人才醒过神来,都道今日见鬼了,方才绝对是妖人斗法,那道人随手就能招来阴风,端的凶恶诡异,可一山还有一山高,那胡人更加高明,只喊了三个字,便破了法术取了道人的性命。
吴李二人惊魂未定,连声向沈墨俞越赔罪道谢,再没心思饮酒,告辞走了。
俞越一边帮刘三收拾一片狼藉的大厅,一边回想方才发生的一幕,越想越觉得那胡人神威莫测,非人所能为,见沈墨面色凝重若有所思,凑上去小声问道:“沈伯,那胡人使的什么功法如此厉害?”
表面上看不出来,其实冷汗已经浸透了沈墨的内衣,方才危险到了极点,那道人妙真子的修为看上去平庸之极,因此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冯均的身上,却没想到妙真子居然精通邪术,一时大意便着了他的道,若不是那胡人及时出手,自己这条命算不上什么,连累俞越可就万死莫赎了。
俞越的发问让沈墨从后怕中恢复过来,斥道:“莫多问,这几日不许出门,老实呆在后院读书!”
俞越见沈伯面色不善,吐了吐舌头,这场争斗大半因他而起,只道沈伯生自己多管闲事的气,不敢多说,急忙跑去帮刘三收拾。
这时,柜台后房间布帘掀开半边,秋娘探出半边身子,低声叫过沈墨,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什么?
沈墨脸色微变,低声道:“真的么?”秋娘点点头,沈墨又道:“你赶紧回房去,莫再出来。”
夜深人静,沈家酒坊一片沉寂。
后院木屋内,沈墨与秋娘对面而坐,面色凝重,显得心事重重。
沈墨道:“别犹豫了,赶紧收拾行李,今晚咱们就走。”
秋娘秀眉微皱:“沈大哥,要奴家说多少遍你才信,他不是坏人,为何要躲他?”
沈墨急道:“秋娘,人心难测,以前是好人现在未必还是好人,你怎知他没有投靠那帮狗贼?”
“绝不会,他心高气傲,爱惜名声,与少爷和小姐的交情都非同一般,绝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秋娘斩钉截铁的说道,心中却想,当年此人和少爷小姐的交情旁人不知,我却明白的很,他视小姐如神仙一般,怎会反过来加害小姐的骨肉?
见秋娘铁了心不愿走,沈墨又急又气,可又不能发作,强忍怒火道:“除了你和小少爷,现在我谁都不信,事关小少爷安危,万万不能意气用事。”
秋娘看着沈墨幽幽道:“沈大哥不愿信人,奴家愿意。从帝都走到玉陵,又从玉陵走到龙川,咱们还有哪里可去,大漠还是北狄?”秋娘伸出手掌轻轻抚平沈墨鬓边花白的头发,“这十几年,咱们都走白了头,走丢了心……”
沈墨身躯微微一颤,握住秋娘的手,喉头一紧,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忽听门外有人低声道:“沈掌柜睡下了么?”
沈墨一把将秋娘拉在身后,沉声道:“谁?”来人悄无声息,以沈墨之能,居然没有发觉。
只听那人道:“在下不请自来,多有得罪,沈掌柜勿怪。”
话音一落,房门轻轻一动,一人出现在门口,借着灯光看去,正是随张印商队而来的那位中年儒生。
沈墨大惊,此人身法犹如鬼魅,修为远在自己之上。当下双手往袖中一拢,低声喝道:“什么人?”
秋娘从沈墨身后转出来,冲那人万福道:“陆先生安好,奴婢秋娘见过陆先生。”
来人正是陆宜,自从见俞越第一面他就怀疑是故友之子,但沈墨却从未见过,因此心生疑虑,这才深夜来探看,方才两人的谈话都落在他耳中。
陆宜认得秋娘,见十几年前刁蛮可爱的丫头如今竟已两鬓染霜,那对神仙般的故友也已是天人永隔,不禁心头微酸,长叹一声道:“一别十余年,没想到竟在此处遇到你们!”
秋娘神色黯然,拉起沈墨的手臂道:“陆先生,这位是沈墨沈大哥,当年随小姐一起南下玉陵,这些年多亏了他。”
陆宜肃然起敬,躬身一礼:“陆某多谢沈青衣。”
沈墨一惊,微微侧身,双手笼在袖中,说道:“不敢当,陆先生如何知道在下贱号?”
陆宜微微一笑:“当年沈先生一袭青衣夜闯鸿江大盗常子蛟的老巢,巧夺白银十万两赈济灾民;弩箭连毙独龙山十大寇,青衣虎袖里箭名震天下,陆某岂有不知之理!”
沈墨心头狂震,这人竟然如此清楚自己的底细,若是不坏好意,可就糟了。
沈墨出身大玄西南武道宗门龙虎宗,精修龙虎拳,尤擅暗弩,陆宜说的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两件事,不过沈墨也明白所谓鸿江大盗独龙山十大寇在真正的武道强者眼里不过是土鸡瓦狗,不值一哂,但毕竟是莫大的善举,青衣虎袖里箭的名号也由此得来,至于威名震天下云云则不过是陆宜的客气之词,当不得真。
“陆先生过誉了,在下这点丑事不值一提,没想到陆先生非但文名满天下,武道也如此精深。”沈墨双手在袖中一动,“天晚了,陆先生一路劳顿,不如先去休息,明日再叙如何?”
这便是赤裸裸的逐客令了,秋娘一拉沈墨的衣襟,嗔道:“沈大哥,你这是作甚?”
陆宜并不以为意,沈墨秋娘两人带着俞越逃亡万里,一路上不知遇了多少凶险,自己突然到访,沈墨心有忌惮实属情理之中。当下道:“陆某行事唐突,沈先生勿怪。”
秋娘道:“沈大哥生性谨慎,又不认识先生,得罪之处,还请先生见谅。”
陆宜道:“无妨,无忧小姐的事我已经知晓了,唉,转眼十六年了,那孩子……”
秋娘十余年来的委屈如潮水般涌上来,眼泪夺眶而出,低声抽泣起来。
陆宜心中也不是滋味,搀扶秋娘坐下,说道:“十几年难为二位了,却不知为何在此落脚?”
秋娘拭去眼角的泪水,将十几年来的遭遇简要说了一遍。
俞越的父亲俞谨言才华横溢,在帝都与陆宜因文相识,结为好友,后来机缘巧合结识了姜氏家族的三小姐姜无忧,两人情投意合。后来姜氏卷入六世家谋反一案,惨遭灭族,姜无忧和俞谨言当时在城外庄园闲居,才得以逃出生天,南下玉陵,藏身荒山。一年后不知为何走漏了风声,俞氏夫妇遭到十余名武道强者的围攻,当时姜无忧生下俞越不久,修为大损,扑杀尽数追兵后,已是重伤不治。俞谨言心伤爱妻之殁,不肯独活,临终前将俞越托付给沈墨和秋娘,令他们远避龙川,留下遗命,请二人务必将俞越抚养成人,认祖归宗。
说完这些,秋娘已是泣不成声。
陆宜起身冲沈墨秋娘两人一揖到地:“陆某替谨言贤弟和无忧小姐多谢二位。”
沈墨见陆宜眼中泪光闪烁,言辞恳切,不似作伪,急忙伸手搀扶,说道:“陆先生不必如此,我二人受主人大恩,虽死不敢懈怠。”
“当年我们带着越儿来到龙川,寻到俞家,俞侯爷见了信物却不肯认,反将沈大哥赶了出来,说俞少爷早已被逐出家门,他的死活与俞家没有半点关系。天下怎会有如此狠心的父亲?!”秋娘断断续续的说道。
沈墨接过话头:“我们走投无路,又不敢回去,只好留在苦茶镇,幸而小人略懂些酿酒之法,便盘了这家酒坊,权作安身之处。”
陆宜沉吟半晌道:“俞氏乃世袭罔替靖远侯,大玄封爵者虽众,世袭罔替的却屈指可数。若越儿袭了侯爵之位,纵然有天大的祸事,依大玄律也可免除死罪,谨言一片苦心,是想保越儿平安。”
沈墨道:“侯爷只谨言少爷一个儿子,越儿便是他唯一的骨血,本来没有不认的道理,可偏偏就是不认,唉……”
陆宜道:“俞侯爷不认,或许另有隐情。本来陆某也去拜见俞侯爷,其中曲折,到时自然明了。”
秋娘突然问道:“这些年陆先生到可查出些什么来?”
陆宜摇了摇头道:“毫无头绪。”
秋娘幽幽道:“仇恨再大也要有命去报,小姐只余下这一点骨血,奴婢不想让越儿冒这个险,能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便好。”
陆宜略一沉吟道:“越儿的身世万万不能泄露,尤其是无忧的身份。”
“这是自然,就连俞老侯爷那里我也没说。”沈墨忙道。
“这样最好。”陆宜脸色蓦地一变,沉声道:“哼!那帮贼子如此丧心病狂,我陆宜拼了性命也要把他们揪出来,哪怕他权势滔天!”
平素陆宜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今日遇到故人,勾起当年的事来,心伤姜无忧和俞谨言之死,将师门不感外物的训诫忘的一干二净,全不像修身养性的一代大儒,到似个热血沸腾的毛头小子。说完这番话,胸中愤懑之气稍解,心中却是一惊,暗道怎的如此失态,急忙收敛心神。
沈墨大喜,跪倒在地道:“小人身微命贱,修为浅薄,无力协助小少爷,有负主人大恩,今后全仗先生,若有差遣,沈墨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秋娘也跟着跪下:“请陆先生念及小姐情谊,护小少爷万全。”
陆宜急忙搀起二人,道:“不敢当二位如此大礼,陆某一定尽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