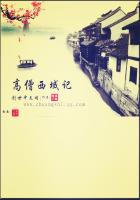一大早,我还在睡梦中,被屋外的吵闹声惊醒:“我的天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一晚上死了这么多鸡?”母亲气急败坏地嚷道。
匆忙穿上衣服,跑出来。只见母亲从鸡圈里一只接着一只往外扔鸡,地上竟已铺了一大片。满地的鸡横七竖八地躺着,鸡毛东一簇西一簇,柔软的脖子扭在一起,每只鸡的脖子都渗出一道道鲜红的血来。仔细看时,才看到鸡脖子上有一排细小的咬痕。
“快叫你爸回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母亲焦急地喊道。
“嗯,你看着,我这就去。”
仿佛大难临头似的,感觉跑慢一步,自己的脖子就立刻会被一种什么奇怪的东西咬断,像那满地直挺挺躺着的鸡。我脚不离地,总觉得背后有什么追上来了。
田里的父亲听了,也是一脸茫然。他拍了拍满是泥巴的手,眉头不由一皱,自言自语地说:“怕真是那家伙出现了!”我听了不由一惊,心里更加不安起来。
跟着父亲急匆匆地赶回来,心里一直在揣测父亲无意间说出的那句话。
“他爸,你看这是个什么情况?一共二十五只鸡。”母亲面带忧愁地问道。
父亲蹲下身,扭过一只鸡的脖子,仔细瞅着。然后慢慢站起来,仰头向屋顶上空望去,像是想起了什么,接着悠悠地说道:“只怕真是那家伙出现啦!”“什么家伙?黄鼠狼自从八年前就已经没见过了。”母亲不解地问。
母亲说的黄鼠狼我倒是见过,八年前,邻居的黄爷爷在野外套住一只,养在家里,可是不到一个月便死了。自那以后,村里再没出现过。
“只怕比黄鼠狼还厉害十倍!”父亲满脸忧虑地说道,“咱家这几百只鸡怕是保不住了。”
“是个啥?这些鸡都养半年了,卖吧,不划算,不卖,这可如何是好?”
父亲再次抬头望了望屋顶的上空。顺着他望的方向看去,只见远处只有一面陡峭的山峰——马家坳——在云雾里起伏,像一条云中游弋的巨龙,没入遥远的天空。儿时曾听老人们讲,马家坳是整个村里人躲避土匪的避难坳,但同时也是流匪窜逃的去处。“山坳里冤魂常在夜里嚎哭哩!”老猎人有时进山,如不是不得已,一般不会夜宿深山,要宿也得找个山洞,多人聚在一起,方可安心过夜。山坳的山腰整个就是一面巨大无比的直立光滑的石壁,仿佛是被巨斧劈开,而那石壁全呈乳白色,远望如一面悬天玉镜,壁上连一株树一径草也没有——那就是有名的白崖山。白崖山一直伸到谷底,远望更像飞瀑直挂,只是没有一点声音;白崖山顶上,有一排常青树,如冠如盖,冬季雪来,便与白崖浑然一色了。就在那白崖的右上方,一孤峰突起,一样的浑身乳白,不长一点青绿,更绝的是,在这擎天一柱的最上方,竟然凭空生出一个口子来,离地千丈,状如门户,势如巨口,黑黝黝不见其底,整个山柱就如拔地而起的巨人,俯视着整个峡谷。
而就在马家坳下,白崖山之上,却天然形成一块巨大的平地——南子坪。通往南子坪的路只有一条,远望像一条细细的藤蔓从悬崖峭壁上缠绕上去。
“前些日子上南子坪看包谷,守山人马子玉无意提起,说他家的几十只鸡竟一夜之间悉数死去,一样的是脖子上有一排咬痕。这样看来,那家伙是下山来啦!”父亲一脸愁容。
父亲说的马子玉便是我的子玉叔。人称“独臂枪手”。至于何以叫这么奇怪的外号,便不得而知。因南子坪地势险要,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很大面积已经被人开荒出来。而山下之人不愿意久居山上,正好子玉叔独居于此,且断了左臂,劳作不便,每年只是靠守山护稼勉强糊口。最近一次见到子玉叔,还是三年前了,那晚子玉叔遭遇了一生最大的双重打击——妻离子亡。听人讲起大概是子玉叔儿子跟子玉叔进山狩猎,不幸坠崖,妻子绝望离家出走。
“马子玉说他也只是在夜里瞥见了那家伙一眼,形如小狗,矫捷如猫,落地无声,只几个跳跃便钻进树林里去了。”父亲粗略的叙说了一遍。
“看来是得请子玉下山一趟。”父亲舒展了一下眉头,点燃半根没抽完的旱烟,悠悠的吸起来。
“他哪里走得开,满坪的包谷指望他看着呢!”母亲打断父亲的话。
“这事越早处理越好,晚了这百十号鸡就真的一只不剩了。趁着时间还早,我赶紧上山,明早一早赶回来。”父亲坚定地说,“今晚你警醒一些,注意鸡圈里的动静。”
“我也去!”心底一阵热血奔涌,总觉得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
“也好,你子玉叔还提起你呢!”父亲吐了口烟。
“这还有些酒,你带上去。”母亲进屋拿出一瓶老白干递给父亲。谁都知道子玉叔嗜酒如命,谁请他喝酒,愿意跟他喝酒,谁就是他的真朋友。
父亲进屋提了那把跟锄头似的土火枪,往肩上一挂,我们便出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