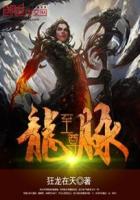一路走去,小径在峡谷左弯右绕,渐渐逼近白崖了。
站在白崖脚下,顿觉呼吸也停滞了,仿佛那面白崖会突然迎面塌下来,把自己压得粉碎。虽说自己也生长在山里,往日更是时时看到的白崖,但真要从这崖间攀爬上去,心里不免也感到惶恐不安。
“你千万注意脚下,不要踩滑。跟着我的脚步走,踩在我的落脚处。”父亲好像一点也不担心。
每攀爬一步,身体便觉得轻飘了许多,双脚也木然无知,仿佛一个趔趄,便要滚落谷底去。
“不要扭头瞅谷底,看久了会头晕。”父亲叮嘱道。
太阳在身后远远地照着,直照得白崖一片通明,而那山崖间太阳照射不到之处,便呈现出暗淡的阴凉。到一拐弯处的大岩石上,坐下小憩。扶着身前的石壁,向白崖下面望去,心里不由得一惊,赶忙缩回头来,似乎身体在这一刹那离我而去,直坠入万丈深渊。抬头向远处望去,只见谷底一片坦坦荡荡,一条流过的枯河蜿蜿蜒蜒,从谷底一直流到村落,枯河尽头聚着一片疏疏点点的房屋,宛如河底的沙石。
“我们家的房子哩!”我不由得叫出来。只见树木掩映中,我家屋顶右上角微微向上翘起,突然想起父亲站在门前从屋顶往远处望时的情境。
“把枪给我挂着!”我回头看见父亲肩上斜挂着的火枪,心里一阵发痒。
“这哪是你玩得的!”父亲威严地说道,“得赶紧走,一会黑下来,路就不好走了。”
太阳越来越温和,宛若一张红润的面颊。谷底一大半照不到太阳了,只山头显出一片淡黄色。
“还得走多久啊!”我有些不耐烦地问。
“爬上这个山包,就是南子坪了。”父亲指着不远处隆起的山包说。隐隐看见山包像一圈盆沿,而那在谷底看到的白崖就是这个盆壁了。
我们最终攀上南子坪时,夕阳再也撑不住,仿佛喝得烂醉,一个踉跄,直向山谷滚落。而身后山谷的那片狭长的谷地,竟已成了一条浅淡的飘带,缠在山腰,谷底的梯田已模模糊糊。
紧走几步,跨上了坪。呵!只见满坪都是整整齐齐的包谷,显出乌青的亮色,一眼望不到头。一直到了山脚,山势陡然险峻,拔地而起,直如云霄——那座山就是我们在山下看到的马家坳了。这真是一个绝好的聚宝盆!低下是三面峭壁,背后也靠着峭壁。真是坪生半空,得天独厚!
沿着包谷地里的小路走进去,高过人头的包谷杆,仿佛一片密密的原始森林,越往里走越昏暗;势如刀剑的包谷叶横亘路上,要不是原先的一条小路,如何走得出去。
“咋的,这包谷长势喜人!可惜了这个地方!”父亲惋惜道。
“嗷~嗷~”,前方竟传来低沉的狗吠,几乎震得包谷叶跟着颤动了。
“当心了,你子玉叔的‘黑子’凶悍!不要喧闹!”父亲紧张地吩咐道。我手心也不觉捏了一把汗。
我随父亲爬上一座土丘,父亲解下肩上的火枪,握在手里。
“子玉哥~兄弟看你来了~”父亲缓缓地叫了一声。
“你过来,不要紧了。”过了一会,子玉叔回应了。
“好啊!这么晚了还有好友来!”子玉叔满脸的兴奋,“哎哟!那是石头娃子吧!几年不见,不认得啦!”
“子玉叔,是我!”
“你的‘黑子’叫声好吓人!现在心还跳呢!”我抱怨道。
此时天已黑下来,微微看得见一点路。
我和父亲走在前面,子玉叔走在后面护着,跨过地坝中间,突然一条黑影扑过来,我不由得惊叫起来,“黑子!”子玉叔大喝一声,说也奇怪,那黑影竟敏捷地顺势一偏,伏在地上,轻轻摇晃着尾巴。我绕过去,却只看见一条牛犊大小的黑影趴在地上,这一惊着实不小。
“子玉叔,这狗这么凶悍,怎么不牢牢拴着?你看,他在我们走近的时候,不声不响,这一伏击肯定伤人!”我十分不解地问。
“哈哈哈!我这里除了你爸不时来看看,其他人也就是在庄稼收获时才来的!”子玉叔朗声道。
“你懂什么?你子玉叔守着这么大一片山,没有这条狗,还不得把庄稼败光!”父亲似乎很不满意我的抱怨。
走进屋来,只见黑黢黢的屋内大堂中间放着一只大木桌子,桌上点着一盏如豆的油灯,堂前墙壁上隐约看到一尊木制菩萨,披着一块布,左边是堆满柴禾的厨房,右边是隔开的卧室。
“坐坐坐!”子玉叔连声喊道,像是多年未见的好朋友。父亲把枪斜挂在墙上。
依次坐下来,子玉叔又忙着往厨房摸去。壁上父亲挂枪的旁边,竟然还有一把跟父亲一模一样的斜挂着的火枪!这又是一惊!
“子玉哥,你别忙!些许下酒菜就行,你看我带了什么?”说完父亲把腰上挂着的酒壶在子玉叔眼前一晃。“好!好好!下酒菜不愁,你看这炕上的野兔子,哈哈,昨天它竟然掉到瓦窑里去了!还有这一串烤干的野鸡,哼哼,我一天从套上捡回几只!”子玉叔兴奋地说道。
“那干脆这么的,你耐心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带‘黑子’去巡一遍田了,回来喝个痛快!”子玉叔手舞足蹈,一边比划一边忙着去解墙上的枪。
“哎,索性一起去!说不定就遇到个大家伙!”父亲站起身说道。
“也好,那娃子紧跟在身后。”子玉叔右手握着枪身,伸出左手来碰了碰我的头,他的左手其实齐腕断掉了。叫人惊奇的是,子玉叔只手做木工,做出的家具秀美实用,只手编竹具,编出的竹具精巧结实,无人能比。几乎每年父亲都要从子玉叔这里背回一大堆的竹具家。什。子玉叔做这些往往是看谁高兴就送人,从来是不卖的。
说完我们一行走出门,借着微弱的手电光,一直沿着包谷地的边沿走。‘黑子’在包谷地里横冲直撞,呼啦啦一阵响声过后便不见了踪影。
“我们选个有利的地势,等‘黑子’把野物赶出来,然后当头一枪!”父亲述说了他的主意。
子玉叔沉吟了片刻,然后带着我们朝包谷地中间的一座隆起的土丘钻过去。这座土丘足有屋顶高,确实是个以逸待劳的好伏击点。
“老弟,要说在晚上伏击就算了,且不说枪法,这黑灯瞎火的,没个准头。”子玉叔缓慢地说道,“等‘黑子’叫了,我们大声呐喊几声,然后朝着狗叫的地方鸣放几枪,便可回家。”
正在说时,却听得‘黑子’在包谷地里“汪汪”叫起来,这同我早先听到的吠声完全不一样,此时的吠声更加急促,也更有震撼力,叫得比心跳还快,这是明显的追踪猎物的叫声。
我的心不由得随着“黑子”的猛吠狂跳不已。
“过来了!”子玉叔轻声说道。除了狗吠,隐隐可以听到包谷林里摩擦的“哗哗”声。响声越来越近。狗吠却戛然而止。“跟丢了。”子玉叔说。
突然“哗哗”的响声更加明显了,伴随着“呼呼”的喘息声,只见模糊的包谷林里包谷杆东倒西歪,仿佛一个巨石滚过,压倒一片。
“好家伙!竟然赶上了!这么早就来啦!”子玉叔自言自语到。
“是什么?”我不觉双腿有些发软,生怕那家伙冲上土丘来。
“野猪!一公一母还有几只小猪!看来真是前些天遇上的,来了好些天了。”子玉叔不慌不忙的说道。
“给它一枪!”父亲询问道。
“先听听狗在哪里。”子玉叔侧过耳朵,“你们在这别动,我下去一趟!”
只见子玉叔几步跨下土丘,几个鱼跃,便消失在包谷林里。
狗又叫起来,向着土丘的西南方追去。
“喔~~喔~~喔~~”子玉叔大叫三声,一声比一声响,声震林野,山崖回荡,久久不绝。“黑子”似乎也听懂了这三声大叫,吠声不由得跟着大起来,遥相呼应。
“嗵!”一声枪响,震耳欲聋,平地惊雷一般划过黑夜,经久不息。
狗吠越来越远,直到远远的山脚去了。
子玉叔走回来,唤我们下来。
“这一惊,只怕又得管上十来天。”子玉叔拍了拍枪身。
“‘黑子’它怎么办?”我不解地问。
“哈哈哈!你就放心吧!它知道回家的路!”子玉叔朗声笑道,黑夜里突然发出这么一串笑声,顿觉毛骨悚然,后背发麻。
“走!回去喝酒!”子玉叔像一个满载而归的猎人。
一路上我都在为那包谷林里的“呼哧呼哧”声感到惊慌。
进了屋,关上大门,这是一扇厚重的木门,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子玉叔和父亲依然把枪挂回壁上。
“图个方便,那就把兔肉拿来烤着下酒,你看怎么样?”子玉叔看着父亲。
“好得很!”父亲应道。
烤兔肉我还是第一次尝试,心里不觉充满好奇,仿佛满屋都是烤兔肉的香味。
子玉叔站在灶台上,伸手取下一只黑黢黢的东西,“肥得很,咋的,把它喂好了!”
子玉叔叫父亲端开灶上的那口黑锅,便在灶洞里烧起火来。不大一会儿,满屋真是兔肉飘香,肚里不觉有些饿了。
“小娃子,来来来!给你一大块!”子玉叔招手道。从来没吃过这样的东西,焦香,是纯粹的,细腻的,虽没有各种调料,吃来也别具风味。
子玉叔和父亲坐在桌前,就着一盏油灯,一瓶酒,两个大口径的杯子,一碟黑乎乎的烤兔肉,子玉叔每喝一口,精神便增长一分。父亲的脸颊映着灯光,泛出微微的红晕。子玉叔酒过三巡,话便多了,父亲却相反,闭口不语,只是闷头一仰脖子喝下一大口。
“兄弟,你今天来,我,我真是高兴啊!你上次是什么时候来的?是三个月之前吧!哈哈,我知道这几天你迟早会来!迟早会来!你看,这些兔子啊,野鸡啊,全都送给你啦!全都送给你!”子玉叔用手指了指挂在壁上的那排黑乎乎的东西,又指了指父亲,“我,你也知道,没什么好东西,你看不上眼。”
“子玉哥,话可不能那么说,喝酒就对喽!”父亲仰脖又是一大口。
“你,你比我享福啊!”子玉叔说话有些不清,“你,你看,你这么好个娃儿,长这么快!”子玉叔说着断了的左手在衣袖里不由得一抖,伸出来,指着我,“哎,我的娃比他还大几岁哩!”子玉叔突然像是一个清醒的人一样轻轻的叹道。
“子玉哥,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个结,为何你连我也不告诉?这么多年了,嫂子走了也有些年头了,你却像是变了个人啊!”父亲闷了一大口酒,说道。
“老弟,哥哥心里痛啊!哥哥说不出来!”子玉叔低头望着酒杯,叹道。
“我和你弟媳都曾劝你下山,不要死守着这片荒山了,你死活不肯。你一个人独守深山这是第三年了吧!”
子玉叔听到这里,突然左手一挥,露出光秃秃的手臂来,“老弟,你可知道我这手,我这手到山下还能做什么啊?”说完一屁股坐下来,声音竟有些哽咽,用手揩了揩眼睛,便默不作声了。
“子玉哥,你这右手一样的可以谋得生计,又担心什么呢?”父亲提醒道。
“老弟,我的母亲在这里,我的父亲在这里,我的娃儿也在这里,我又能到哪儿去呀?”子玉叔说着说着竟掩面呜呜大哭起来。
“子玉哥,你何必这样固执呢?你的父亲和娃儿在天也不忍看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守在深山呐!”父亲安慰道。
“弟啊,我心里抱愧啊!这个家完全是毁于我手,我要守护父亲和娃儿一辈子咧!”子玉叔哽咽道。
“子玉哥,你和伯伯和侄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这些年,你只字未提,我就不好问。”父亲试探道。
子玉叔猛地端起酒杯,仰头喝尽了杯里的小半杯酒,喝得太急,一下子呛住了。子玉叔摆摆手,摇了摇头,像是一语难尽,又像是不愿提起。
“话长,话长啊!都是好久的事啦!恐怕一夜也未必讲得清啊!”子玉叔深吸了一口气,像是陷入了沉思和回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