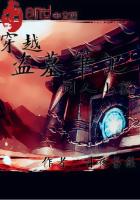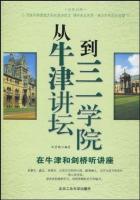钱立宪关于江雪文背景的叙述,让“男科诊所”里的“四个病人”睡意全无。冷兵更是辗转反侧,焦虑不安。
杨宏伟沉思良久对其他三个人道:“冷兵出的事就是我们大家的事,我们必须兄弟“同”心,一起度过这个难关。谢早,你戴个眼镜整天装得跟有多大学问似的,快想个办法,别让小老弟为难了。”
谢早揉揉太阳穴,有条有理地分析道:“据冷兵所讲,这个江雪文比较‘霸道’,而冷兵却胆小文弱。按照这个情况去推理,冷兵在江雪文面前说话都不敢大声。若是让冷兵给江雪文道歉,估计江雪文也不会给面子,弄不好还要被江雪文奚落一顿,真不值得。”
“不去道歉还能怎么做?难道就这么干等着江雪文去老师那里告状?”脾气急躁的钱立宪不解地反问谢早。
“你急什么?我话还没说完呢!依我多年跟女人打交道的经验来判断,当你得罪了女人的时候,最能得到女人原谅的办法是写书面材料。在追女人的时候,女人到手之前要写情书;女人到手之后呢,就要写保证书。”谢早自以为是地解说道。
“哎呦我的哥,你说话能不能直接一点?你想急死我呀?”钱立宪心急火燎地催促谢早。
“冷兵又没有追江雪文,写什么‘书’?”杨宏伟闷声闷气地问。
“写充满真诚和温情的‘检讨书’。”谢早胸有成竹地回道。
“这样的‘检讨书’我从来没写过。怎么写?”冷兵有点发愁。
“天不早了,况且这个事情如此紧急,我看这样吧,谢早打着手电筒帮冷兵写那个温情‘检讨书’;钱立宪起来放哨,发现有查夜的马上发出警报。时间紧迫,马上行动,限你们半个小时完成。现在,熄灯!”“四大男科”之首的杨宏伟果断地连下几道命令。
第二天一早,谢早心安理得地躺在被窝里不睡装睡地闭着眼睛。冷兵替谢早打扫好卫生,以还昨晚欠下的人情。早读时杨宏伟帮谢早请了个假。早饭时钱立宪帮谢早打了个馒头盛了点汤,回到宿舍见谢早还没起来,忍不住阴阳怪气地挖苦道:“早泄啊早泄,你昨晚泄多了咋地?看你个小样呗,帮哥们点忙,这个能嘚瑟。”
“你懂啥?这脑细胞要是用多了,想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也就是我们四个有缘分,分在了一个宿舍且‘同病相怜’,若是换作别人,我可是不揽这些脑力活。”谢早一边反驳着钱立宪,一边懒洋洋地坐了起来。
眼看就要到上课的时间,冷兵怯怯地问谢早,“谢学长,你帮我写的‘检讨书’在哪呢?”
谢早指一指靠在墙角的床头柜,“在抽屉里,自己拿。”
冷兵急急地打开床头柜上的抽屉,发现里面有两个信封,用手摸了摸,有一个信封是空的,另一个信封则装着厚实的信瓤。于是拿起装满信纸的信封,飞快地跑去上课了。
江雪文见冷兵过来,微笑着站起身,把冷兵让过去,扭头轻轻地对冷兵说:“今天你来晚了,我帮你把卫生打扫好了,看,你的桌面多干净!”
江雪文充满友爱的态度让冷兵心里吃了定心丸似的轻松,还没坐下,冷兵就借着这个友好的气氛,从书包里掏出那个鼓鼓的信封顺势递到了江雪文手里,“文文,给你的。”
“你写的?这么多!是因为写这封信,你今天才比平时来的晚了?”江雪文用顽皮的眼神斜了斜冷兵。
冷兵使劲点点头,“文文,对不起!这是……”
“对不起?你没有对我做错什么呀!”江雪文微笑着看着冷兵。
“我,我昨天……”见江雪文已经把昨天的事放在脑后,冷兵心里不由得想,人家文文是个女孩,都没把昨天“翻译男科病”的事放在心上,而我这个大男人却这么拿不起放不下的,文文知道了又会笑话我是小心眼子,于是话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
“既然你这么有心,我也要对得住你。白天认真上课,晚上回家,我再好好看你给我写的信。”江雪文说完拿出课本开始预习。
冷兵没有想到江雪文会如此坦荡大方,一颗悬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如释重负地把心思全部投入到了学习之中。
晚上,刚回到宿舍,冷兵就被三位舍友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问冷兵白天跟江雪文的“战况”,当听到冷兵说江雪文这么有胸怀的时候,几个哥们儿不禁啧啧称赞起来。
因自己写的“检讨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略感失落的谢早带点小醋意地说道:“兵兵,今后你可要给我们传递正确情报啊,不要再因自己不行就怪别人,这‘性冷淡’的症状可要不得。”
“今晚,江雪文看了你帮我写的‘检讨书’肯定会对我更刮目相看。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冷兵谦虚地恭维谢早。
“那倒也是。哎!你的问题解决了,我该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了。”说着,谢早走到他靠在墙角的床头柜旁,打开抽屉,发现里面那张叠成心形的“检讨书”仍在,禁不住大声叫了起来:“怎么回事?我帮冷兵写的‘检讨书’怎么还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