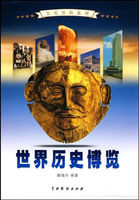一盏昏黄的烛灯在幽邃的走廊尽头亮起,晕染出持灯者模糊的身影。并不明亮的灯光显得四周更加阴暗莫测,隐隐有野兽般的气息浮动,幽深昏暝一如鬼魅聚居之地。
这是滇国的重囚牢房,魑狱。
持灯者并未四顾寻觅,而是直奔走廊尽头而来,显然是对此处布局有所了解。他的目标是那间位于黑暗最深处的,魑狱唯一的单人牢房。
那所牢房的恐怖是整个魑狱所公认的,里面见不到一点光亮,而且四壁厚重周遭寂然无声,只消待在里面片刻就能使人发狂,历来是关押最残暴最狰狞的重囚的地方。
来到牢门之前,他借着微弱的光看了看里面的状况。在烛火勉强照亮的角落,一人倚墙而坐,不言不动,似是已然睡着。
他点了点头,掏出钥匙开门入内,将烛灯放在室中的地面上,同时放下了另一只手提着的东西。
突然,他猛地一惊,立时转过头去。
角落里那人早已睁开了眼睛。
此时的光线仍然昏暗,但足以让人看清这名重犯的模样:双眼含笑,白衣素净,若非双手都被粗大的锁链与身后的墙壁相连,真的没人相信他是被关在这里的重囚。
“先生睡醒了?”持灯者微微躬身施礼,“我给先生带吃的来了。”
“不曾睡着,小憩而已。”对方颔首答礼,“晨雷重囚之身,左魍将军不必如此客气。”
诚然,这名看着啥罪也没受还能继续保持风度的年轻重囚犯,便是正因祁和之战与半月变阵在六合掀起一阵狂澜的神秘兵道家,晨雷。
他匆匆从容国赶到大兵压境的滇国,求见国君离鄢。这个蠢到令人无法直视的举动直接导致他在满足要求之前被迅速逮了起来。由于对晨雷远超封趵的强绝战斗力有详细的了解,离鄢特地派了一百弓手,一百铁甲来合围这一个人,在其毫无抵抗地束手就擒之后,迅速把他扔进了魑狱。
“既叫了一声先生,便少不得恭敬些。”左魍把刚刚放下的食盒移到晨雷面前,“先生请用。”
“把酒留下就行了,东西你拿走吧,你们滇国的烈酒‘烈焱’真的是无与伦比,可惜这里太冷,吃食甚不讲究。”晨雷抬手去揉眉毛,带得手上锁链一阵哗啦啦地响,“光从你们最尊贵的筵席——百牛宴,就知道这个品味该是有多奇怪。炝爆牛肠、鲜食牛脑、白煮牛眼还有酥炸牛气管,听着名字都让人心惊肉跳啊!”
“嗯,好吧。”左魍应了一声,乖乖地上前拿走了那倍受指责的食盒,“未想到先生不喜欢松鼠桂鱼和葱烧锦鳞,那便算了。”
“停!把鱼留下!”晨雷立刻改变主意了,“我没说不要鱼啊!”
晨雷是七分有意三分无意地在逗左魍,但后者面色却仍殊无笑意,依旧是显而易见的阴沉不明。他将食盒在晨雷面前摆开,也不顾地面冰冷,在地上盘膝坐下,开始凶猛地自斟自饮。晨雷有了鱼吃得开心,也顾不上别的,便由着他一杯又一杯喝了下去。
待晨雷一盘锦鳞下肚,左魍那边已经喝了个半饱。烈焱是滇国有名的烈酒,左魍酒量虽不错,但也已微有醉意,其明证便是他的脸色更加阴沉,连低着头的晨雷都觉得气温直线下降,自己身上的夏装已经完全顶不住了。
晨雷放下刨光的盘子,按住了左魍倒酒的手,左魍抬头横了他一眼,却被蛰了一下般迅速收回了目光。
他被晨雷的眼睛惊到了。
晨雷的眼睛他不是没有见过,而且是在比这里明亮的地方认真地端详过。那是当日晨雷刚刚被抓准备送入魑域时,当时他诧于这双眼眸的干净清澈,以及其突然被刀剑相向时不变的淡然镇定,但那些时候都没有今日这种感觉。
那双天生带着笑意的眼,此时流露出的表情分明就是:理解。
“你理解什么?你知道了什么?”左魍惊恐地站起身来连连后退,一直退到脊背碰上了身后的墙壁,右手狂乱地在空中挥舞,像是在驱赶什么,“你不要…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
“魍,我没有用特别的眼光去看你。”晨雷叹了口气,端起了另一盘鱼,“是你怕了,你自己心里有事。”
他看了看酒壶,又看了看面色苍白的左魍,慢慢地道:“魍,你喝这么多酒,是想灌醉自己来忘掉自己的任务,还是要为杀我,壮一壮胆呢?”
左魍盯着地上的烛灯,渐渐安静了下来,沉默了许久之后勉强开了口:“先生…知道了?”
“给我吃了那么多天的牛肉,今日突然给我带了你们不怎么吃的鱼,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个词:‘断头饭’。听说死刑犯临死前是会给吃顿饱饭的,果不其然。”晨雷挑捡着鱼刺,不紧不慢地道,“魍,这鱼来之不易吧,麻烦你了。”
他给自己斟了杯酒,续道:“滇国左氏一族本掌刑狱,然汝之父辈早亡,家势倾颓,现今只能做个狱官。”放下酒杯他又拎起筷子大口吃鱼,讲话却是一点也不含糊,“魍,你的真名是什么?”
“法纪之法。魍是我的字。”左魍像是回答私塾先生提出的问题一样老老实实地答道,“先生知道,左氏素来严苛刻板,一定要以肃然严整之字为名,魍乃鬼魅,是断不能以之为名的。”
晨雷点了点头,又斟了杯酒,边喝边看着左魍出神,良久后叹道:“魍,你是个应当上阵带兵打仗的将才啊,现在困于家族的声名,在这终年不见天日的地方消磨时日,真是可惜了。”
左魍深深吸了一口气,无言以对。
令人压抑的沉默持续了许久,突然,他捂着脸疯狂地大笑了起来,声音凄厉喑哑如鸦鹫的哀鸣,在四壁激起阵阵阴沉的回声。
“先生果然有蛊惑人心的本事啊!”左魍此时形貌与疯癫无异,令人毛骨悚然,“先生差一点便说动了我!没错,我是对这职位毫无兴趣,我也不想如此消磨一生,但我姓左啊!我是左家人,左家现在唯一的男丁,我再无所作为,左家会亡的!”
他喘了一口气,放下手来,露出的目光悲哀又绝望。
“我真的敬重先生的勇气,敬您敢于如此拯救百姓,先生的聪颖我亦见识了,可以说,先生是左魍最佩服的人。但我接到了处死先生的命令,左魍不能不执行。”左魍自怀中掏出诏令展给晨雷看,同时抽出佩剑来,“左魍还有个家族要想,恕我卑鄙,先生武艺太强,我没有把握取胜,所以不能解开先生的镣铐一对一的决斗了,请先生……”
“咣”的一声打断了左魍的话,他突然觉得脑后剧痛,然后眼前一黑。
晨雷看着被镣铐砸晕在地的左魍,揉了揉刚刚松开重铐的手腕,无奈地道:“这熊孩子,哪那么多话啊。”
接着他拎起筷子继续把鱼吃完,顺便拧断了另一只手上的镣铐。
吃完了鱼,他拎起了烛灯走出牢门,并且细心地回身把门锁好……
然后他就像左魍来时一样,提着灯慢慢走向出口。
晨雷向来知道自己认路本事不好,但是到现今才发现自己早就升级了——他现在是一个路痴。
在魑狱里转了足足五圈之后,他决定再试上最后一次,如果还是走不出去就干脆回去继续蹲,反正也没人杀得了自己。
他掏出身上除了鞋以外唯一可以扔的东西——藏在怀中的容国虎符。尽管他被捕时有一两百人包围,但也没人敢上前搜他的身,只是收走了他的武器和马。顺带一提的是,在魑域里也没人敢对他下手干什么,这便是他衣服仍然整洁的原因。
他将虎符信手向天上一抛,然后满意地将这只“顺”来的玩意儿放回怀里,向虎头所向之处走去。
尽管虎符来路不正,但指路却正得很,几经波折后晨雷终于发现了魑狱的一道边墙。墙不矮,但以晨雷的身手自然毫无压力,他轻松地跃过墙头……然后……就有压力了……
他落地之处是一片萝卜地,而他对面,有一位“拔萝卜的小姑娘”,还当真带着一个大竹筐。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位其实一点也不小的姑娘便短促有力地尖叫了一声,然后奋起神威将一筐萝卜劈头盖脸地砸了过去。
“偷萝卜的贼!我可逮到你了!”姑娘把倒完的筐一扔,单手叉腰,另一只手指向晨雷的鼻子,那叫一个英姿飒爽。
“我姐啊,长得是真漂亮,性格是真汉子。”晨雷想起左魍的描述,立刻便认出了眼前姑娘的身份。
“纾姑娘,我名晨雷,不知魍有没有和你提过。”晨雷皱眉道,“我现在是个逃犯,亡命之徒什么都干的出来,姑娘不要逼我。”
“你知道我?你还知道小魍?”左纾愣了一下,“你是……晨雷先生?”
“魍还真的跟你提了啊。”晨雷点点头,“那不知说了我些什么?”
“说他崇拜先生崇拜得一塌糊涂。”左纾蹲下来捡萝卜,“还有,他回来说今天要杀你,纠结得不得了。”
晨雷很有眼色地帮着她捡,捡完了还自觉地拿起筐,要帮她送进屋去。
“得了,你不用这么客气,我知道你没害小魍。你要真是杀了他跑出来的,刚刚应该立刻杀了我。”左纾摆摆手,“筐子放那,你赶紧走吧。”
“实不相瞒,我不想走。”晨雷把筐子在左纾所指的地方,“我这一逃,滇国势必要捉拿我,画影图形下,我估计走不出滇国。就算走得出,我也不想走。滇国这位君主我是一定要见上一面的,而且看现在的形势,只怕是越早见面越好。”
“那你是打算住这里?”左纾看了他一眼。
“魍说有些犯人的亲眷来访,就是在他家里住着,想来应该有我呆的地方。”晨雷搬了个凳子在角落坐下,“姑娘先忙,我等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