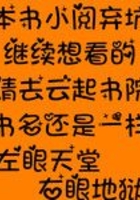自打那日圣上病重,百官便人前人后均以庭暄马首是瞻,以为南帝将一病不起。却不想,为了立储之事,皇上硬是撑着半副残躯,上了早朝。意料之内,百官拥立庭暄的声势渐勇。南帝看着朝中上下一心,心中甚是欣慰。本打算在今日颁布谕旨,却不想庭暄是千般推辞,惹得南帝满心不悦。于是早朝未完,南帝便散了众臣,回暇居殿静养。至于立储之事,自然是不了了之。
勋王离开大堂的时候,隐约间瞥见庭暄从侧门而出,心中甚是疑虑。不过细想今日朝堂的风向,倒也是见怪不怪。于是默然离去。
刚出了殿门,勋王便被一宫女拦住。
“王爷,广平侧妃有请。”
环顾四周后,勋王便随那侍女去了一隐蔽之处。那里,顾倾依站立背对,仪态得体。霎时,他只觉那枫树下的女子不是倾依。因为在他眼里,阿顾是个青涩的女孩。恍惚之间,他颤音而出:“阿,阿顾?”
她蓦然回首。却在看见他的时候不自主向后颠了一步,迟疑片刻,她轻笑:“殿下。”
“叫我许炎吧。”他说。
细看,他只觉这女人已然卸尽了往昔俏皮,温婉清傲之气浑然一身,散之不去。
“你方才看到我,为何如此惊讶?”他问。
“也没什么。只是突然看见你脸上的假皮,不习惯罢了。”她垂眼咬唇,不敢与他相视。
他揭下假面,似笑非笑:“不过是一副皮囊,没什么习不习惯的。倒是你,清雅端庄了许多。”
“流年似水,人事易非。那落叶梧桐带走的,也不过是一场空梦。又何必唏嘘呢?”
面面相觑,却是无话可说。
良久,他苦笑一声,“你叫我来,有事吗?”
一语惊醒梦中人,她尴尬挤笑,回道:“广平王说,他要退下皇权之争。”
同样的,许炎如梦初醒,猛然回起方才殿中所思,急切地说道:“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才说!”
沉默片刻,她付之一笑:“得见故人,心中久久难平。所以忘了。”
枫叶铺就的地上,她独影一人。望着那视线尽头,泪眼婆娑。
这一场秋风叶雨的重聚,恍若隔世。
许炎赶到暇居殿的时候,高公公在殿外看护。还未等公公开口,许炎先说:“无妨,本王在殿外等候便是。”
伫立殿外,一门之隔,恳求怒骂,尽传耳中。
“混账东西”南帝提喉痛骂,“这皇家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
庭暄卑躬屈膝,紧贴地面,字字铿锵:“求父皇成全,恩准儿臣”
“住口!”未等庭暄说完,南帝便将桌上茶盏用力摔去。
庭暄斜眼瞥见地上粉碎的茶盏,心中知晓南帝的恼怒。可一想起倾依忧伤的眼神,再大的风险他也会迎难直上。
“求父皇恩准。”
“你!不孝啊!不孝啊!”南帝紧捂胸口,后退数步,猛地坐回椅上。
“你给朕滚出去!”这一句骂,南帝声音沉重、气吁不断。
“父皇若不答应儿臣,儿臣断然不会离去。纵使长跪于此,也必要求得恩旨。”
“你竟然如此逼朕?你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
“对于儿臣来说,父皇是天,替儿子撑起了一切。可顾倾依,她是儿臣的命。若是没了这命,还要天作何!”
“混账!就为了一个女人,放弃触手可得的万里江山,值吗?”
“值不值儿臣自会掂量,准不准全凭您一道圣旨。”
“若是朕不准呢?”南帝试探,话中带话,本以为他会就此罢口,断了念想。却不料,他高估了自己对庭暄的了解。
“父皇乃人中之龙,若是不准,儿子必当遵循父皇旨意。只是”庭暄面朝南帝,掷地有声,“待父皇归于黄土,便休怪儿臣卖国偿愿。”
话音刚落,南帝只觉喉中积血,血腥异常。看了看跪有一个时辰的庭暄,更是怒火难平,一气之下,全然不顾了这父子情份。
“好。你不是要自由吗?你不是要和那女人双宿双栖吗?朕成全你。”
“高慎!”
“奴才在。”高公公弯腰而入。
“传朕旨意,广平王庭暄忤逆犯上,罪无可恕。念其年轻气盛,从宽处置。着令其贬黜皇城,于兖州任职,明日动身。令立五子庭旷为太子,替朕总管朝政。”
“这,皇上三思啊!”高慎跪地,探寻风向。
“朕意已决,无须再劝。你着手去办吧。”
高慎退下后,南帝迈着缓慢的步伐走近庭暄。他蹲在地上,对从未如此卑屈的庭暄说:“红颜祸水,国之不国。既然你如此绝情,那便永生不要再见。庭家,不养情种。”
“儿臣领旨谢恩!”庭暄额头着地,久久不起。那固执的脸庞却在此刻淌满了泪水。
殿外,许炎冷笑离去,于幽僻处唤来那传话侍女,说:“告诉顾倾依,按兵不动,一切都等广平王到了兖州再说。”
广袤天空下,许炎抬首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