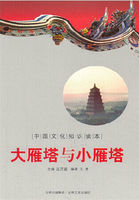成都的特景——茶铺
节选自《暴风雨前》,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茶铺,这倒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上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人家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
茶铺,在成都人的生活上具有三种作用:一种是各业交易的市场。货色并不必拿去,只买主卖主走到茶铺里,自有当经纪的来同你们做买卖,说行市;这是有一定的街道,一定的茶铺,差不多还有一定的时间。这种茶铺的数目并不太多。
一种是集会和评理的场所。不管是固定的神会、善会,或是几个人几十个人要商量什么好事或歹事的临时约会,大抵都约在一家茶铺里,可以彰明较著地讨论、商议、乃至争执;要说秘密话,只管用内行术语或者切口,也没人来过问。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数说一阵,就算他的理输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十几桌的茶钱一并开消了事。如其两方势均力敌,而都不愿认输,则中间人便也不说话,让你们吵,吵到不能下台,让你们打,打的武器,先之以茶碗,继之以板凳,必待见了血,必待惊动了街坊怕打出人命,受拖累,而后街差啦,总爷啦,保正啦,才跑了来,才恨住吃亏的一方,先赔茶铺损失。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烂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所以差不多的茶铺,很高兴常有人来评理,可惜自从警察兴办以来,茶铺少了这项日常收入,而必要如此评理的,也大感动辄被挡往警察局去之寂寞无聊。这就是首任警察局总办周善培这人最初与人以不方便,而最初被骂为周秃子的第一件事。
另一种是普遍地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不过只限于男性使用,坤道人家也进了茶铺,那与钻烟馆的一样,必不是好货;除非只是去买开水端泡茶的,则不说了。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竟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这其间有三层好处。第一层,是可以提高嗓子,无拘无束地畅谈,不管你说的是家常话,要紧话,或是骂人,或是谈故事,你尽可不必顾忌旁人,旁人也断断不顾忌你;因此,一到茶铺门前,便只听见一派绝大的嗡嗡,而夹杂着堂倌高出一切的声音在大喊:“茶来了!开水来了!茶钱给了!多谢啦!”第二层,无论春夏秋冬,假使你喜欢打赤膊,你只管脱光,比在人家里自由得多;假使你要剃头,或只是修脸打发辫,有的是待诏,哪怕你头屑四溅,短发乱飞,飞溅到别人茶碗里,通不妨事,因为“卫生”这个新名词虽已输入,大家也只是用作取笑的资料罢了;至于把袜子脱下,将脚伸去登在修脚匠的膝头上,这是桌子底下的事,更无碍已。第三层,如其你无话可说,尽可做自己的事,无事可作,尽可抱着膝头去听隔座人谈论,较之无聊赖地呆坐家中,既可以消遣辰光,又可以听新闻,广见识,而所谓吃茶,只不过存名而已。
如此好场合,假使花钱多了,也没有人常来。而当日的价值:雨前毛尖每碗制钱三文,春茶雀舌每碗制钱四文,还可以搭用毛钱。并且没有时间限制,先吃两道,可以将茶碗移在桌子中间,向堂倌招呼一声:“留着!”隔一二小时,你仍可去吃。只要你灌得,一壶水两壶水满可以的,并且是道道圆。
不过,茶铺都不很干净。不大的黑油面红油脚的高桌子,大都有一层垢腻,桌栓上全是抱膝人踏上去的泥污,坐的是窄而轻的高脚板凳。地上千层泥高高低低;头上梁桁间,免不了既有灰尘,又有蛛网。茶碗哩,一百个之中,或许有十个是完整的,其余都是千巴万补的碎磁。而补碗匠的手艺也真高,他能用多种花色不同的破茶碗,并合拢来,不走圆与大的样子,还包你不漏。也有茶船,黄铜皮捶的,又薄又脏。
总而言之,坐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就形成了的一种生活方式。
河水香茶
节选自《大波》,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成都那时将近有三十万人口,在城墙圈子内的,约占六分之五。这么多人用的水,几乎全由井里的水供给。成都平原,地下水非常丰盛,一般掘井到八市尺便见水了。掘得深的,不过一丈到一丈四尺。百把人,只要一口浅井,随你如何使用,如何浪费,它总不会枯竭。但它也只能供你作为洗濯使用。因为它含的皉质和其他有害健康的杂质很多,强勉用来煮饭烹菜,已经不大卫生,若用来泡茶或当白开水喝,更不行。所以当时每条街上兼卖热水和开水的茶铺,都要在纱灯上用红黑相间的宋体字标明是河水香茶。河水,就是围绕成都城的那条锦江的水。每天有几百上千数的挑水夫,用一条扁担,两只木桶,从城门洞出来,下到河边,全凭肩头把河水运进城,运到各官署、各公馆,尤其是各家茶铺去供全城人的饮用。设若一天这几百上千数的挑水夫不工作的话,那情形当然不妙。
第一楼茶铺
节选自《大波》,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两个人放慢脚步,一边谈谈说说,差不多把一条漫长的北打金街走完了,郝又三方挟着黑皮书包,气喘面红地追上来。走进第一楼茶铺门,几乎每张桌上都是人,几乎每个角落都充满了人声。伍平说:“并不清静嘛!”郝又三说:“楼上去看。”楼上果然另是一个场面:靠后稀稀落落安的十张蒙着白台布的麻将牌桌上,仅三张桌有人,而且一共不过七八个人,都轻言细语在摆谈各人的事情。最前面靠着玻璃窗安的三张也蒙有白台布,并摆有花瓶的大餐桌,所有新式立背餐椅都闲着没人坐。
伍平才待选一张麻将牌桌坐下,吴凤梧已把他拉向中间一张大餐桌去道:“走!那儿坐。同又三先生一道到第一楼来吃茶,是不能让他省这几角茶钱的。”伍平光着两眼问道:“难道坐位还有高低不成?”
“若是没有高低,那么舒服的位子怎能没一个人去坐?”三个人刚刚拉开餐椅坐下,一个干净利落的堂倌便端着一个茶盘,从楼下飞奔上来,一直走到大餐桌前。一面把三把洋磁小茶壶,和三只也是洋磁的有把茶杯,一一分送到各人面前,一面笑容可掬地向郝又三打招呼道:“老师好久不来吃茶了。”伍平问道:“茶钱是多少?”一边就去衣襟袋里摸钱。
吴凤梧用手肘把他一拐道:“这里是又三先生的码头,茶钱你我都开不了,我们不要做过场。”堂倌也说:“老师招呼过的,是老师的客伙,我们不好收茶钱。”郝又三已将一枚当五角的银元递到堂倌手上,问道:“这一晌生意还好吗?”
“楼下还好。”一面数着从怀里抓出的一把当十铜元。“就只楼上清淡些。”把数好的折合两角的十六枚铜元放在郝又三面前,并且问道:“要不要点心?不要。那么,盐花生米?白瓜子?好的,各装一盘来。水烟袋呢?福烟早已断庄,只有本城水烟和绵烟。”吴凤梧道:“有叶子烟没有?”
“有烟杆,却没有叶子烟。”郝又三道:“算啦,我这里有纸烟。”堂倌走后,伍平不禁把头一摇道:“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竟不晓得成都有这样茶铺,这样贵的茶!”
乡场上吃茶
节选自《大波》,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大平原上快要成熟的迟种的稻,嫩黄得一望无涯。有人形容说:很像一片翻着浊浪的海。——是一片海,不过是浅海。它很浅很浅,浅得足以容人在它的浪涛里自在游行。
这段稻海中心,涌现出一簇青郁郁的瓦屋顶;而且还有很高峻的扳鳌抓角的屋檐,还有枝叶纷披、老干横皌的皂角树、柏树和到处都有的桢楠树。这是处在成都之西的郫县和崇宁县交界地方一个大场:安德铺。
今天是赶场日子。大路小路,在连天阴雨后,一溜一滑不好走。但是赶场的人,从二簸簸粮户到庄稼佬,从抱着公鸡、提着鸡蛋的老太婆,到背上背一匹家机土布,或者拿着一大把鸡肠棉线带的中年妇女,仍然牵线似的向场街上走来。
晌午以后场在散了。场上的茶铺、酒铺、烧腊铺、面食铺的生意更加兴旺。
出名的老牛筋何幺爷,戴一顶几乎要脱圈的旧草帽,脚上草鞋是捡他长年穿得不要了的,拄一根可以当拐杖用的粗叶子烟杆,挺着胸脯,一路东张西望着向场口走去。有几个年轻小伙子,也有两个中年汉子,正围坐在一家茶铺的临街安放的大方桌上吃茶。大家都在打招呼:“喂!何幺爷,吃碗茶去。”一看,都是左邻右舍的熟人,何幺爷开心笑了起来,露出缺了几颗牙齿的牙床,上唇上的不多几茎很像黄鼠狼的又硬又棕的胡子,也在皱脸两边颤抖了几下。走上台阶,大声喊着:“茶钱!茶钱!”叶子烟杆交代给左手,空出满是筋疙瘩的僵硬的右手,虚张声势地伸到裹肚兜里,直等有人把茶钱给了,——乡场上吃茶,还是百年以来的老价钱:三个制钱一碗;还是可以搭一个毛钱,如其你找得出毛钱来的话。——才抓了几十个制钱出来,迭在自己面前桌边上做样子。
成渝茶馆异同论
此文原题为“从吃茶漫谈重庆的忙”,本书编者改为此题。
到重庆,第一使成都人惊异的,倒不是山高水险,也不是爬坡上坎,而是一般人的动态,何以会那么急遽?所以,成都人常常批评重庆人,只一句话:“翘屁股蚂蚁似的,着着急急地跑来跑去,不晓得忙些啥子!”由是,则可反映出成都人自己的动态,也只一句话:“太懒散了!”懒散近乎“随时随地找舒服”。以坐茶馆为喻罢,成都人坐茶馆,虽与重庆人的理由一样,然而他喜爱的则是矮矮的桌子,矮矮的竹椅——虽不一定是竹椅,总多半是竹椅变化出来,矮而有靠背,可以半躺半坐的坐具——地面不必十分干净,而桌面总可以邋遢点而不嫌打脏衣服,如此一下坐下来,身心泰然,所差者,只是长长一声感叹。因此,对于重庆茶馆之一般高方桌、高板凳,光是一看,就深感到一种无言的禁令:“此处只为吃茶而设,不许找舒服,混光阴!”
只管说,“抗战期中”,大家都要紧张。不准坐茶馆混光阴,也算是一种革命地“新生活”的理论。但是,理论家坐在沙发上却不曾设想到凡旅居在重庆的人,过的是什么生活呀!斗室之间,地铺纵横,探首窗外,乌烟瘴气,镇日车声,终宵人喊,工作之余,或是等车候船的间隙,难道叫他顶着毒日,时刻到马路上去作无益的体操吗?
我想,富有革命性的理论家,除了设计自己的舒服外,照例是不管这些的。在民国十二年当中,杨子惠先生不是用“杨森说”的标语,普遍激动过坐茶馆的成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工作”,而一般懒人不是也曾反问过:“请你拿工作来”吗?软派的革命家劝不了成都人坐茶馆的恶习,于是硬派的革命家却以命令改革过重庆人的脾胃,不许他们坐茶馆,喝四川出产的茶,偏要叫他们去坐花钱过多的咖啡馆,而喝中国不出产必须舶来的咖啡、可可,以及彼时产量并不算多,质地也并不算好的牛奶。
好在“不近人情”的,虽不概如苏老泉所云“大抵是大奸匿”,然而终久会被“人情”打倒,例如重庆的茶馆:记得民国三十年大轰炸之后,重庆的瓦砾堆中,也曾在如火毒日之下,蓬蓬勃勃兴起过许多新式的矮桌子、矮靠椅的茶馆,使一般逃不了难的居民,尤其一般必须勾留在那里的旅人,深深感觉舒服了一下。不幸硬派的革命下来了,茶馆一律封闭,只许改卖咖啡、可可、牛奶,而喝茶的地方,大约以其太不文明之故,只宜于一般“劣等华人”去适应,因才规定:第一不许在大街上;第二不许超过八张方桌;第三不许有舒适的桌椅。谢谢硬派的“作家”,幸而没有规定:只许站着喝!一碗茶只须五秒钟!
如此“不近人事”的推销西洋生活方式——请记着:那时我们亲爱的美国盟友还没有来哩——其不通之理由,可以不言,好在抗战期间,“命令第一”,你我生活于“革命”之下,早已成了习惯。单说国粹的茶馆,到底不弱,过了一些时候,还是侵到大街上了,还是超过了八张方桌,可惜一直未变的,只是一贯乎高桌子、高板凳,犹保存重庆人所必须的紧张意味,就是坐茶馆罢,似乎也不需要像成都人之“找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