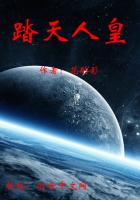那日之后,木叶如愿以偿的踏入了心澄之境,也是在不经意之时,不去强求,反而终有所得,恰如那一日初晨的阳光,也算是一种必然。木叶后来回到屋里回想起来,才发现原来那日早晨在浮生书院门前一脚已经迈入了心澄之境,第一次的大道和鸣姑且不论,而第二次却是暗合了“其生若浮”的意韵,而此次又因为百花凋零以及回忆起老人逝去,暗合“其死若休”。所以,自然功成。
不过不得不说,恰恰是在浮生书院,方能有此感悟,来这里似乎也是一种命定的缘分,十数年前林千秋自此离开,到云烟山下,如今走出大山,再回到此地。繁华市井竟有一处可以暗合一位远行游子的心境,确实是一种缘分。
李子木对此也很开心,在他兴冲冲到来找木叶,并且告诉木叶他已经摸到了身合之境的门槛时,却未曾想到,木叶已经在踏入心澄之境不久之后,直接迈入了身合之境。望着有些失意的李子木,木叶苦笑着,想起了那天和林千秋分别时,老师嘱咐他的话:
“叶儿呀,现在你已经迈入了心澄之境,算不上迅速,但也绝对算不上慢的,这个东西一方面要看个人的悟性,但更多的是机缘。既然你已经迈入了心澄之境,现在我将身合之境的要领教给你,细细领悟,相信你迈入此境会非常容易的。”
林千秋笑眯眯地说道:“心澄身止,身褪凡体,躯与心合。”说完便昂着头走了,和往日的林千秋大不相同。
木叶只当老师是调侃,也因为迈入心澄之境耗费了许多时间,木叶回来之后就决定要细细钻研。但拿着这十二个字有些犯难,比起心澄之境更加玄乎。好在书本上有判断迈入此境的方法。如果丹田之处有一缕真气产生,即说明踏入此境。为何是如此?书上也有解释。
心澄与身合是修真的第一个门槛,在此境界之中被称为准修者。成为修者,意味着要调动天地之力,而调动天地之力有两种方式,一者是将天地之力化作真气储存在己身之中,调动真气即是调动天地之力;另一种便是直接调动天地之力。而这两种不同的方式正是高境界修者与低境界修者的最明显的区别。可以说,修者修真在操纵天地之力上的表现就是一步步超越躯体真气的限制,达到直接调动天地之力的效果,此所谓《庄子·逍遥游》中的“无所待”,也是儒家所说的圣人之境“与天地参”。
而无论是以哪种方式调动天地之力,都是建立在心神对天地大道的体悟的基础之上。高境界者,心即是道,则天地随心而动;低境界者,澄怀观道,将道纳入心怀,以此心引天地之力入体以化真气。而修真的过程,一方面是修心,修真之路上所有的门槛都是心的门槛;另一面却是炼体,以天地之力炼体,也就是以真气炼体,天地之力经过红尘凡躯自会有所损减而化成真气,而修为愈高,躯体愈是纯粹,真气愈是接近原本的天地之力,到心即是道的境界的时候,躯体也澄明无瑕,真气即是天地之力,自然也无所谓真气与天地之力的区别了。
可以说,先贤将修者的最初两重境界命名为“心澄”“身合”是大有深意的。最初的两个境界其实也就道尽了修真的始终。而谈及心与身的关系,一般而言,心在身前,心的境界高于身的境界,但这并非绝对,也存在天生无垢之体的人,这也是大道的恩赐,高境界修为之人孕育的后代多属此类。但是诸如无垢之体之类的身的境界远高于心的境界的人,他们所要经历的坎坷并不比一般人少,不过他们的真气会比同一境界的人要更纯粹一些,几乎不会有真气质量超出一个甚至几个境界的情况。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天地之力入体化为真气的时候,经历了两个衰减的过程,最明显的是凡躯俗体对其的污浊,但更重要的却是此心对于引入真气的选择。打个比方,澄怀观道的心就如一面镜子,当心即是道的时候,这面镜子不染尘埃,甚至已经没有了镜子,天地之力无所不至;而当心处于澄怀观道的境界的时候,对道的理解程度不同,就类似于同样的镜子,有的布满灰尘,有的相对干净,而镜子中倒映的就是心要引入的天地之力,自然会有所差别。
所以与心的境界相比,身的境界对天地之力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心也是身的主宰。但是无垢之体并非没有益处。一般而言,无垢之体最大的好处,就是同等境界战力的相对提高,以及破境所需的时间会比较短,因为真气相对更纯粹,也更容易积累,也免去了每踏入一个境界需要进一步净化身体的功夫。
而木叶很幸运,虽然他并不是传说中的无垢之体,但自小诵读经典、生于山灵水秀之地,加之云烟山云海所含的天地灵气的滋养以及坚持不懈的每日锻炼身体,他的身体境界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修者。与那些士家大族每日以灵药淬体相比,这种自诗书由内而外的净化、天地灵气的自然滋养以及个人每日的努力,更暗合天地大化的自然运转,自然快速了不止一筹。这也是木叶能迅速踏入身合之境的原因所在。
当然木叶并不了解,但他也没有在意。这一日,他终于又见到了许久不见的师姐烟月,在清泉轩的浩然亭里。不过,那里还立着一男一女,气质高雅,少女大概正值并笈之年,容貌如花,透露着一股娇俏的意味,一双灵动的眼睛,衣着绿色的襦裙,仿佛一个堕入人间的精灵。而少年也是十五六岁,颇为英俊,剑眉星眸,身穿一身黑色曲裾,宛如一块上好的美玉,浑身上下透露着一种君子的风范,正是《诗经》:“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木叶想了一下,决定还是不去打扰,刚转身准备离去,却被一阵如落玉盘的声音喊住了,听这声音也知道是一位钟灵毓秀的女子:“是谁?在哪儿鬼鬼祟祟的?”
木叶苦笑了一下,转过身来,摊了摊手,道:“这位姑娘却是言重了,在下只是路经此地,见亭内有相识之人,却见你们三人相聊正酣,不便打扰,由此便准备离去了。”言罢,又朝着烟月行了一礼。
少女娇俏地哼了一声,道:“谁知道你安没安好心?我看——”还准备继续往下说,却被一旁的男子打断了。男子温润含笑,向木叶行了一礼,道歉道:“在下替舍妹向这位公子道歉了。她向来顽劣,让公子见笑了。”
烟月只是在一旁看着,眼里有些波澜不惊,望着行礼的木叶,点了点头。一旁的少年人见此,随即道:“这位公子,相遇即是缘分,既然你也认识烟月,那么也来这里一同赏着亭亭翠竹吧。”
木叶听此,倒是有些惊讶,这位少年人竟可以直接喊出烟月的名字,他知道这位师姐气质冰冷,少有人可以接近,更不用说可以直呼名字。想到这里,心里不禁有些苦涩,旋即将这种感觉逐出了脑海。他仰起头,看到少年眼里的真诚与一旁绿衣少女眸中的灵动与好奇,不觉心中生出几分好感,见烟月犹豫了一下也在此时轻轻点了点头,于是便上前道:“那么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走入浩然亭,环顾四周的翠竹松柏,近看这三人,都是气质难得的人,黑衣公子温润如玉,倒与这亭子与四周的景致最为相合,而绿衣少女则是这幅画卷中最动人的颜色,阳光洒下正是充满了青春与活力,而气质最惊艳的仍是一旁安静站立的少女——烟月,似是作了两人的背景,却又无法让人忽视。如果说,只有一旁一男一女的画卷颇像一副居士赏春图,而加上了烟月之后,却有了一种空灵的仙气,不似人间。
而另一边,一男一女也在审视着踏入亭子的木叶,少年并不十分英俊,但也可以称得上清秀帅气,一身普通的学子服,却并不显得庸俗,最引人瞩目的还是那一双澄澈如墨的眸子,如深山幽潭,在踏入心澄之境以后,仿佛可以直接穿透你的内心,倒映出整个世界。少年的气质让人想起了孔子世家所流传的一句话:“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
双方都为彼此的气质而赞叹不已,正在此时,一旁安安静静的烟月忽然插话道:“木叶师弟,这是赢玙公子。”“赢玙公子,这是我的师弟木叶。”
这忽然的插话让两人心里都有些不自在,连忙互相见礼之后,发现彼此眼中都有一丝措手不及的意味,当下两人之间有了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味道。
一旁的绿衣少女见此“噗嗤”笑出了声。见三人都望着她,表情有些奇怪,便对着烟月说:“你们怎么都这样看着我,连烟月姐姐你也这样看着我,我笑是因为他俩啦,他俩这样动作不是很让人生气吗?人家是为你鸣不平。”说完,还握了握小拳头,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一旁的两位少年有些尴尬,木叶只觉得满头黑线,心里想到:这鸣不平有这样鸣的吗?说白了就是笑嘛,还狡辩。
不过,木叶还未在心里说完,就看见一个绿色的身影跳到了他的面前,下了他一跳,连忙退了几步,只听那人说:“喂,小叶子,你没听过我哥哥的名字?”
且不论这位绿衣姑娘随意给人起外号,让木叶头上又多出了多少黑线,她的问题也让人困惑不已。木叶摇了摇头,眼睛纯洁的如一只小白兔。绿衣姑娘睁大了眼睛,很不可思议,道:“你真的不知道啊?我哥哥可是——”
还未说完,便被赢玙捂住了嘴巴,只见他一脸歉意道:“舍妹顽劣惯了,还请公子原谅。”说完,继续介绍道:“她是在下的妹妹,名字叫嬴安然。”说着,望着嬴安然的眼里满是疼爱之色。
一旁的木叶嘴角抽了抽,安然,好吧,这个名字真是严重的名实不符啊。
而另一旁,少女挣脱了少年手掌的束缚,瞪大了眼睛,微嘟着嘴,柳眉倒竖,十分生气的样子,“哼”了一声,不理少年人了。便跑去另一边,缠着清冷的少女,还回过头喊了一句:“男人都是大坏蛋!”
让一旁的赢玙无可奈何,而木叶是躺着也中枪,而另一旁站立的清冷少女也不禁莞尔。暮春的阳光洒在少女的身上,镶着金光的身影,三千青丝在风中飞舞,让木叶不禁又想起了那个第一次见到少女的早晨。这似乎是他第一次看到少女的笑容,真的很美。而一旁的赢玙,望着这副画卷,眼神有些复杂。
多年以后,当事的这四位少年少女早已天各一方,却仍能回忆起这样一个早晨,似乎是一场偶然的相遇,却充满着命运的恩泽与祝福,就像是一首长长的曲子里,命运无意间拨动的一根琴弦,却是未来数个章节的开始。
风,就从这个暮春的早晨,吹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