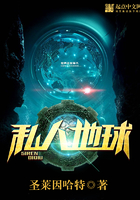吃完中午饭,收拾利索,吴丽无事可做。看看自己的床单,尽管不是很脏。今天有太阳,河面会化出冰浆水。于是她拿下了床单,换上了一条干净的床单,端着盆走出里间,来到两男生的外屋,顺便把他们的也洗了。她心里想着。她上到炕上,把丁旭的被子挪开,床单扯了下来,忽然他的床头现出了一个画册,她好奇地打开看了起来,这是一本写生稿的册子,她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有独马、独牛、独羊。它们姿态各异,有站着、卧着、正面、侧面。然后是马群、牛群、羊群。与那些单独的马牛羊相比,它的画面显得复杂多变,气势恢宏,令人眼花缭乱。后面是人物画,男女老少,各种不同的人物都有。有的骑在马上放牧,有的在射箭,有的在摔跤,有的在跳舞弹琴,有的在挤牛奶,有的在喝茶聊天,充分展示了草原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一幅是大队全景图,远处是夏场,坐落着蒙古包群,人影点点,乌兰河呈倒“S”型横穿画面,画面前是骏马奔腾的场面,一位牧马人和一个青年骑在马上,手持套马杆向远处望去,她觉得这个写生稿好像见过。对,她想起来了,这是春节那张海报的底稿,忽然一张画纸从中掉了出来,吴丽将其展开,这是一幅未完的底稿,上面一个少女只画了一半,右上角上写着一行小字,“淡雅更婵娟”,吴丽羞红了脸,急忙将它叠好重新夹进了画册中。虽然丁旭从来没有向她直接表白他爱她,但是那次乌兰河边是他们爱情的开始,他们的心和眼睛在向对方说:“我爱你!”吴丽将画册放到原来的地方,整理好铺,然后下地走了出去。
洗完床单,她端着盆走进庙。当她路过殿堂时,里面传出了一阵声音,殿堂的大门虚掩着,“是苏大伯,他在里面干什么?”她怀着好奇顺着门缝朝里面望去,只见一个背影在舞动着,突然他一转身,一个恐怖的面孔映入眼帘,一阵急切的声音传入耳朵,吴丽吓得惊叫一声,盆子掉在了地上,床单也撒了出来,她顾不得捡扭头就跑,惊慌中,她忘记了自己的住处,她不知道向何处躲藏。
“姑娘,吴同学。”苏喇嘛从殿堂里走了出来,此时他已摘掉了面具,只见他浑身的装束奇特古怪,色彩纷杂,宽袖长袍上面的纹饰也显得鬼蜮多端,身上还缀着许多条带子。吴丽惊愕地说不出话来。
“姑娘,别害怕!我是在跳查玛,驱除妖魔鬼怪,保佑你们平安。”
“噢噢……”吴丽的嘴哆嗦着,惊恐地朝后退着。老人用手指了指,吴丽没明白。
“你的房间在那边。”
“噢。”吴丽胡乱应付着,后退着,一转身跑回了屋。屋里没有一丝暖气,整个下午她都躲在房间里,没敢跨出门口一步,一想到那张恐怖的面具,不停地舞蹈着,还发出可怕的声音,她就浑身发抖,“丁旭、杨涛你们快回来呀。”可是等待的时间是那样地漫长。
外面终于传来了脚步声,他们回来了。看到两位风尘仆仆归来的牧友,吴丽大哭起来。
“吴丽,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说呀,到底怎么了。”两人惊慌地问道。
吴丽一把抓过丁旭的双臂,“丁旭,我害怕,我受不了了,我要放牧。杨涛,”吴丽又抓过杨涛的双臂,“我,我求你们……”
“你的脚还没好,再冻伤会留下终生遗憾的。到底怎么了?”丁旭将杨涛推开,双手抚着吴丽的肩,急切地问,“我……我……我好害怕,好害怕……”
“你说呀,说出来我才能帮你。”
“是不是?”
“他带着那个面具在大殿里,跳……跳大神……”
“噢,是跳查玛,那天跟你说了。别怕,头几天,我也有点恐惧,我保证再过三天,你就见怪不怪了。”丁旭一边说着一边脱掉大衣扔到炕上,又脱着那双笨重的毡靴。
“对,没什么可怕的。”杨涛也劝慰着。
“不,我已经好了,我一定要去放牧。”
“再过几天。”
“不!我明天就放牧。”丁旭没说话,整理好他的衣装后,走出房门,提了一桶牛粪走了进来,点燃了灶火。吴丽感到了一丝羞愧,急忙往锅里添上水。
“这是什么?”杨涛翻开那个袋子。“哎,木炭?”
“是他,是他送给丁旭画画取暖用的。”丁旭沉默了。
“当当!”
“您请进,苏大伯。”丁旭打开了门,老人把那个装着床单的盆递到了丁旭手中,“过去吃饭吧,我做好了。”
“这?这怎么行,我们马上就好。”
“走吧,尝尝我的手艺。”
“吴丽,走呀,过去。”
“我不饿。”
“那你自己在屋里待着,我马上给你送来。”丁旭走了出去。
“走吧。”杨涛拽了吴丽一把,本来就感到有些内疚的吴丽,只好硬着头皮跟了过去。
“谢谢您!苏大伯。可我不明白您怎么会烧炭?在咱们草原都是牛粪当家。”丁旭说。
“当年八路军打鬼子时,就是用它来取暖的。”
“那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打鬼子的故事吧。”苏喇嘛喝了一口茶,慢慢地说道:“那时候草原真是一个大战场。有骑兵、步兵、袍子兵、八路军、国军。”
“国军,他们干什么?”
“打鬼子,联合抗日嘛。”
“什么是袍子兵?”
“他们是穿着蒙古袍的兵,所以叫袍子兵。”
“您也打过鬼子?”
“打!那天我骑着马,一连射死了六个日本鬼子,后来他们发现了我,追了过来,我骑着我那匹白飞马,跑得像风一样,子弹在我耳边呼呼响,他们没追上我,一颗子弹打在了我腿上。”
“大伯!”三个青年激动地说不出话来,看着眼前这位可敬的老人沉默了。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多少各民族优秀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为国捐躯,他们的英名镌刻在了永垂不朽的丰碑上。更有多少人,奋战在抗日的疆场,他们没有留下姓名,死去默默无闻,活着过着简单的生活。吴丽此时已泪流满面,一切的恐惧化作了景仰与爱戴。老人似乎累了,倚着墙睡着了。丁旭拿来了画夹,借着油灯的光亮,望着老人慈祥的面孔,一笔一笔地画了起来。
冰不多了,吴丽戴上棉帽,将棉手套的连接绳挂在脖子上,掩上门走出房间,她要用那个独轮车,到河边推些冰来。这几天她的脚已经好了,多亏了苏大伯的草药,明天就可以接着放羊去了。独轮车的木轮压在高低不平的雪地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午后的风小了些,原野渐渐沉寂下来。冬天的冰河在淡淡阳光的漫射下,形成一道旖旎的风光,河岸灌柳枝上雾凇凝结,如诗如画。一只叫不上名的小鸟,登在枝头歪着脑袋,看着吴丽,吴丽也仔细地打量着它:尖尖的小嘴儿,白色的羽毛。小鸟张着嘴发出“喳喳”的叫声,吴丽随即回应了它:“你的同伴呢?怎么就你一个?你的亲人呢?”小鸟又“喳喳”叫了起来,好像是在回答吴丽的问话。吴丽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小鸟,将车推到河岸边停下,岸边离河床有一段落差,一块块往上搬吧,反正小推车也装不了多少,等他们回来套上牛车多拉些。她拿起镐头,走上冰河,忽然不远处传来了声音,吴丽抬起头来。“一定是苏大伯在那边刨冰。”丁旭告诉过他,不让他拉冰,他偏不听。吴丽扛着镐头拐过一道弯,绕过那片灌柳丛,真可谓柳暗花明,这儿河床宽阔,岸边与河床落差不太大。一只黑牛套着一辆勒勒车站在岸边,“苏大伯。”吴丽叫了一声。
“姑娘。”
“苏大伯,不让您干,您又干了。”
“啊,没事,你可要当心你的脚。”
“已经好了,我来,您老歇一会儿。”
“不累。”
“别,累坏了您,我可担待不起,他们一定会骂我的。”
“哈哈,这算什么事,孩子,不怕的。你们不在,我不照样干吗。”
“您一个人才用多少。”吴丽边刨边说。很快河面就堆积出了一个小冰山。
“苏大伯,您快到岸上,我来装车。”吴丽将冰块移到了岸边,弯下腰搬起一块,轻移脚步朝牛车走去。苏喇嘛接过冰块放入车中,最后一块大冰两人一起把它抬进了车里,吴丽又把那边的独轮车推了过来,将其装满。
“这小车不好用,还费力气,一次只能推一点,以后就用勒勒车,我们合作。”
“这不行,您只帮我套牛、赶车才行,否则我不答应。”
“真是个善良的姑娘。”
“苏大伯。您生我的气吧?”
“哪的话,我高兴认识你们。我们相逢在风雪草原,成了朋友。”
“是啊,苏大伯,这条河也是乌兰河吧?”
“是,我们乌兰河很长,我们都是喝着它的水。同一条水,同一个故乡。这条河养育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人们爱这条河,它是自己故乡的象征,它流淌的是生命之水。”大伯望着眼前这条冰河赞叹着。吴丽点点头被老人的话感染。
苏喇嘛用绳子把小独轮车拴在了牛车后面。“好,我们走,你扶着它。”
“好的。”吴丽双手把着车把。
“扶好了吗?”
“好了。”苏喇嘛一挥鞭子,黑牛拉着勒勒车走开了。
一个月来,方圆的草已经满足不了羊的胃,吴丽和杨涛每天不得不走很远的路程放牧,丁旭的画还有一大半没有完成。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眼前,丁旭沉默了许久说道:“我们明天搬家吧。”
“那你的画岂不半途而废了。”杨涛说道。
“保护羊要紧,以后再说。”
“不,丁同学。”苏喇嘛走了进来。“你留下。我们三个去放牧。你们俩白天,我晚上下夜。”
“大伯,苏大伯,万万不可,我再也不忍心让您替我了。”
“孩子,你这说哪里话,我高兴啊!”
“不行,您会让我永远不安心的。您不要,您不要……”丁旭拉着老人的胳膊,可是老人用力把他的手拂去,拍着他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