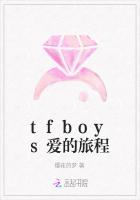兜兜转转回到台北,太阳快落下。火车临靠站前,千默掏出手机给怀北发了一条讯息:想喝酒,陪陪我。一刻钟后到家,楼下见。
怀北百无聊赖在家待了一天,她甚至嫉妒起家中的摆设物件,羡慕它们与璃秋密切生活的过往。突然收到千默的短信,一时云里雾里,滴酒不沾的丫头这么反常莫非俩人拌嘴吵架了?又或者老人对笑尘不满意?
“好!待会儿见,路上注意安全。”,即将分开的人,也就格外珍惜最后的一切相处机会。
这几年,街巷的酒吧逐渐包围了子沐的咖啡店,但至今怀北还未去过任何一家。她习惯了咖啡的味道,甚至学会用咖啡味觉来丈量时间。
怀北简单理了理头发,披上一件针织长衫,下楼前随手在包包里放了一些保鲜袋,直觉告诉她,今晚注定不醉不归。
楼下相见,还未及打招呼。千默走过去,一头搁在怀北的肩上,一时重心不稳,俩人差点栽过去。怀北懂她,没有细问,使劲将千默扶稳,顺了顺她的碎刘海,俩人并肩走进酒吧巷子。
第一次进酒吧,怀北难免忐忑。留了个心眼,最终走进了子沐咖啡店对门的一间。进去前,她回头瞥了一眼咖啡店,子沐正在整理陈列柜上瓶瓶罐罐的咖啡粉,他的背影在斜射的夕阳余辉下显得格外温暖。一时怀北竟看出神,千默拉过她的手,走进那扇从来只是路过的门。
酒吧高台、迷幻灯光、驻场乐队,怀北对这一切感到陌生和抗拒。原来,有些习惯是改不了的。不出所料,一整晚千默一言不发,只顾着一杯接一杯下肚,仍觉不过瘾,红白混喝。怀北觉得实在不妥,赶紧拖着千默出来,奈何借着酒劲,怀北根本扶不住她。跌跌撞撞,刚出门千默就吐在酒吧门口。怀北握着保鲜袋无奈地笑了,再多的准备也敌不过措手不及。轻轻拍着丫头的背,好让她舒服点。
俩人背靠背在地上坐着,头顶的星星格外亮,怀北想起了璃秋,原来这七年,他们隔着半球,横跨大洋,晨昏颠倒地生活着。此刻,加拿大的他起床了吗?
对街咖啡店的灯熄灭,子沐借着街灯锁上门。转身之间,恍惚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留心走近几步:“怀北,是你吗?”
“是我,子沫。千默醉了。”,怀北抬头望了一眼,看他一脸惊讶的样子反而觉得几分可爱,他总是这么一副认真的模样。
“我送你们!这么坐着也不安全。”,说着一手拉起千默,借着一只手臂,把重心附在自己身上,怀北接过千默的背包,跟在她的另一侧。酒吧距公寓并不远,即使扶着千默,十分钟也就到了。怀北接过千默的手臂,看样子并不想让子沐送上去:“子沐,谢谢你,回去小心。”
“小事。”,对着两人背影,子沐不禁又跟近了几步,轻声问出口:“你会离开台北吗?”
怀北一时立在原地,她也没想清楚这个问题。尤其看到自己的照片后,更不可能回避这七年的等待与坚持:“也许,只是换个住所,还不能戒掉你的咖啡。”,摆摆手,扶着千默跨上阶梯。
子沐怔怔地站着,久久未转身,直到两人消失在视野中:“七年,第一次以这样的借口送你回来……”
到家的千默像换了个人,趴在床边嚎啕大哭,怀北倒了杯清水,家里没有醒酒的东西。水杯被千默打翻,她紧紧地握着怀北的手,字不成句地吐着心底的痛苦与难堪。
夜色正黏稠,人心正脆弱。
这个不眠夜,怀北终于明白为什么笑尘不再留头发,为什么两年相处得如此淡薄,更明白为什么他不想要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