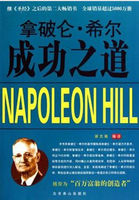吉普车走的时候,村长的心里沉重了起来。这可是个大事,他太清楚这里的人了。人活一世,故土难离。不要说你年补贴了一些,就是你不要一分钱,恐怕难保都愿意搬迁。再说,农民祖祖辈辈都是种粮的,你说好端端的地放着地不种,办厂?这是咋了。咱农民要钱干啥?有吃有喝还要钱干啥。
照以往,每回吉普车还没走出村子,村长总要放开大喇叭带着醉意再说些事,有时还指鸡骂狗,给一些头上长角的人敲敲边鼓。这回例外的没了声响。当村子里人偷偷说村长可能要免职了的时候,村长在他家院边的大核桃树下召开了村民大会。第一个到场的自然是六阿婆了,她每天都坐在这里,不论天阴下雨,白天除了吃饭都坐在这儿,面朝着对面的大山看了二十多年。
“你六爷死的时候,殡葬的人像过队伍一样。棺板真正三寸厚。”六阿婆说着用伸出的右手大指和食指比划着。
“听说六爷是个大人物。”四儿竖起大拇指给六阿婆说。
六阿婆笑着竖起大拇指。
六阿婆等村长把椅子搬过来,坐在上面的时候,她摇到村长眼前说:“政府发钱了吗?”
“走!打忧啥呢。”
六阿婆看着村长的一脸的凶相,又摇过来、坐在她用屁股磨得发光的树根上,看着对面的大山。
“半仙,老九呢?”
“不晓得。”
“四儿,你去叫老九吧。”
大家觉得有啥事,往常村长开会,最怕的是老九来搅和,今天却有意要叫老九。大家相互在看,用眼睛说话。
老九上山挖药去了。四儿用半仙的棍子捣碎了一只被撕掉翅膀的黑蝴蝶。
开会。村长清了嗓子说:“乡上要把全乡人集中起来,都搬在长河村,建新村镇。这是政策,硬的,大家要积极。”
“咋建新村镇?”
“就是叫大家住上新房子。”
“好!我的房还是我爷手里盖的,快塌了。”
“我还正准备开年要盖新房子哩。”
“住多长时间?一年行不行。”
“大家把话没听清楚。是这。大家要把自己的房子撇下,把牛羊都赶到长河去,这里要退耕还林,不准再住人了。长河在建新村镇,都要搬出山去大家听明白了,一下子像炸了锅一样。
“我们去种啥?牛羊吃啥?我们的房子呢?又要搞公社食堂化吗?”
“大家要准备钱,住新房要钱。”
“要多少钱?”
“政府每户补两万元,大房子自己掏三万八,中房子两万八,小房子一万八。”
“谁去就去,我一分钱都没有。”
“没钱信用社可以贷款。”
“哼!贷款?你以为贷款是从兜里掏豆子?”
村长在一片吵闹声中低头抽烟。
老九背着背篓站在村长眼前,大家的吵闹一下子停下来了。
“不搬的给多少钱?”
村长抬起头,看见了正在向他笑的老九,大声说:“这是政策,你和我犟没用。”
“你是村长。”
“……我不是村长,你是村长?”
“村长你带头。”
“我带头。”村长把烟锅敲在六阿婆脚尖前的石头上说,“我不带头我就不当这村长。这是政策,你敢抵抗?”
“政策叫我们富裕,可你给咱套上几万元的贷款,这就是政策?”刘疯子说。
“你是谁的瞎儿秃孙子,你住新洋房你不掏钱?”
“你和乡长是好朋友,给咱求个情。孙木匠说。”
“要不是好朋友凭啥给咱望天每人补两万元。”
“你爱钱,上面补的钱你一人拿去。你搬到新村镇去住吧。这才叫石头走了河滩宽,驴毬走了裤裆宽。”老九笑着说。
大家一阵狂笑,只听得村长说,哼:“你能,我就不信狗头是铁打的!”
这是村长多少年来最失败的一次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