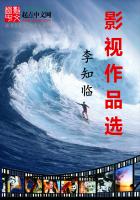走在上学的路上,我似乎被“困”字符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不敢闭眼,怕是一闭上眼睛,就要栽倒路边,闷头大睡,再也起不来了。起脚、落脚,我告诉自己,快到了,快到了,到了教室坐着睡,抽空还能签到、划重点,不比在路边睡着好多了吗?张佑君,你挺住!
文三楼,近了,近了。层层叠叠的翠绿中露出了一小块暗红色瓦檐,檐下的青铜风铃在晨风中叮叮当当。风拂过树梢浓密又细小的叶子,叶子沙沙作响,似乎与风铃唱和。我却无心领略清晨的悠闲,只想着一步跨进班上,先签到,再到最后一排的角落里舒舒服服地打个盹。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节课啊。可是没想到,上课途中偶遇一鬼,改变了我一直以来的疏懒生活。如今常想,如果当时未遇斯鬼,又当如何?“逝如川水,不可挽回,”她笑着说,“你,认命吧。”
好吧,后来的故事留在后面再说,老妈说:剧透死全家!
话说我玩儿了一宿的魔兽争霸,头晕脑胀地跑去文三楼502教室。在距离文三楼正门不远的花坛里,看到一个鬼影子,坐在假山前面石头上。身材瘦长,也许是个女生。她不去上课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我今年启用的座右铭。还记得年初,正上写作课时,坐我旁边的欧阳倩倩毫无征兆地晕倒了。全班就我一个男生,我便把她背去医务室,结果被随后赶来的她男朋友杜冷丁一顿臭揍。她手里的验孕棒,赫然一个“十”字。杜冷丁非说是我给他带绿帽子,要找人画符灭了我……幸好全班姐妹七嘴八舌异口同声地论证:张佑君,又丑又笨,好吃懒做,为人小气,尖酸刻薄,短小无能,还有口臭,倩倩怎么会看上他,才让杜冷丁化一腔妒火为正能量,特地请假,跟家里要了钱,陪着倩倩去无痛鬼流。
从那次起,我时刻准备着,别给自己找麻烦,现在连老太太被三轮车撞飞了,我都不管。
但那时不知怎么了,脑袋上起了无数的问号,就是一个劲儿地想知道她为什么不上课去。“鬼迷心窍!”这是多年以后她对我的行为下的判词。
“哎……那个,我说,好孩子不逃课啊!”我故意重重跺脚走近了才说,好像怕吓到她似的。这句开场白,从内容上来说:即免去了不认识的尴尬,也凸显了学长对学妹的关爱,还暗示她是个好孩子(这样打扮的女生,是不会反对好孩子这个称号的)。从音质上来说:声音从丹田发出,圆润且浑厚,因为熬夜加上抽烟,也略带了几分沙哑。——总之,我对这句搭讪的措辞、音质和音调都十分满意。
“鬼话不能信!尤其是诗人张天饿大师的鬼话。”
我头上的问号更多了。看来她还认识我呢。她是谁?看着她小巧精致的脸,挺直的鼻子,粉润的唇,黑洞洞的深不见底的眼睛,左边眉心有一个小小的痣,我被电了一下,好像在哪儿见过呢?
“张大师别回忆了。我叫江好,大一的,上星期六路过你们诗社,看到你们饮酒作诗,你喝了两瓶啤酒,躺在门口抱着树吐白沫,我叫保安把你送回去的。”“哦原来是你啊,大恩人!受我一拜!”张佑君,您脸皮真够厚的,这样的糗事被人看到了也无所谓。——反正也看到了。不如借这个机会进一步搭讪。我虽然孤僻,但不是性冷淡,“谢谢江同学出手相助救死扶伤,今天请你吃饭吧。”“今天文学史大课最后一节,我想画画重点。我忘带笔了,出来打电话让老公送来。”她似乎看出来我蓄意搭讪,而且对我无感,便用这种巧妙的语言善意地拒绝,真是聪明伶俐,善解人意。
“老公……嗯,好好好。”我心中鼓荡起来的浩然之气顿时泄了一半,但不甘心,又问:“你大一的,为什么学我们大三的课?”“迟早也要学,先预习着。反正大一的课不多。”“那,我先走了。”估计她老公快来了,我也不要做那熠熠发光的电灯泡。况且我的长相,按照那天班上众位美眉给杜冷丁提供的确切信息:“超乎了地球的范畴,是一种类似于月球表面的那种,坑洼不平,面色暗沉黧黑且毛孔粗大,目狭窄而睫毛短,眉粗梳而凌乱,肆意生长的鼻毛,赫然暴露在视线中,视之作呕而不自觉也。”我留在这里,除了陪衬她“老公”英俊潇洒,还能展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何苦呢?
进了教室,签到,找地方睡觉。这是最后一节大课,全系大三的都来了,三百多鬼,过道都技满了。只有第三排中间还有空座位——不奇怪,那些座位是焦点中的焦点,上课提问必然先从这儿开始,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有人坐的。罢了,先坐下再说。我高抬着腿脚,跨过一双双或粗或细、或交叠或抻长、或短裙或丝袜的大腿,跌跌撞撞地摸到了座位,扎扎实实地把自己给坐了下去。头一歪,眼一闭,便睡了。
一阵香气从东边传来,不是食堂的包子,不是六神花露水,不是廉价圆珠笔,而是花瓣在雨后初绽。睡眼朦胧中,似乎是江好对我笑,粉嫩的唇,挺直的鼻子,深不见底的黑眼睛,都饱含着笑意,笑容好像随时会滴下来。我隐约听见陈主任说:“Mimesis是必考的……近现代文学理论是重点……”“Mimesis……”,一个清脆的声音把这个词重复了一遍。“江好?”这声音让我猛一抬头,把梦中流出来的口水扯成一条细线,在穿过天窗投射下来的阳光下闪耀着。
“张大师可以cosplay蜘蛛侠。嗯,惟妙惟肖。”真的是江好。——我恨自己发达的唾液腺,恨自己不分场合睡觉这个天赋。别拦着我,让我去死,不,去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