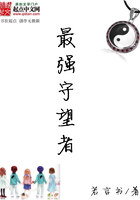那家伙不偏不倚,正好撞在乘警乙的小腹上面。
这时,所有的乘客都已撤离,撤到了车厢与车厢之间。两个车门之间早就空了。
尽管小时候练过几天铁头功,但介于距离太近,杀伤力不大。
所以,乘警乙并没有受到什么致命打击,最多就是乘警甲头部的这一撞,由于受力面积太大,自然也不会有多大影响。
于是乎,他将依旧嚎啕的乘警甲往身后一放,又要再度向我扑来。
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拼斗,我觉得实在实在滑稽,要打我也要知道是为何而打,干嘛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能真的就为一张车票吧?于是,我赶紧做了个“暂停”的动作,抱拳说道:
“今天这命,你是要还是不要了?如果不想要,你就尽管来。反正,今天我是不想活了。不过,打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你们为啥要打我啊?”
我边说边扎起马步,两拳一握,挺胸落臀,摆了个你死我活的架势。
乘警乙一看这阵势,知道我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于是生出几分怯意。
听我这么一说,乘警甲挣扎着凑了上来,就着乘警乙的耳朵一阵窸窣。
听乘警甲说完,乘警乙连忙收起架势,扶着乘警甲,转身向餐车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说道:
“尼他马的算你好运,碰到老子这下有事,暂时免你一死……”
没等他说完,乘警甲又道:“有种的你给老子等着,看看回头我怎么收拾你?”
“等着就等着,哪个怕哪个!”我毫不畏惧。
没等我把话说完,二货已在过道里消失……
二货走后,我将架势一收,那阵阵疼痛又迅速传来,尤其是耳朵里的滋滋声,依旧在一阵阵轰鸣。好在,经过一阵子的调休,这分钟稍微好了一点点,不至于听不到说话的声音。
百无聊赖中,我用手轻轻揉着每个痛处,揉着揉着,突然想起爷爷的话语:
“不小心受伤的时候,可以适当按按自己的穴位,它可以帮你缓解疼痛,还可以将伤治好。至于效果的好与坏,关键是看穴位按不按得准。”
一想到这,我便中脘、梁丘、门内、公孙、足千里……一个不拉地按将下来。我一边按,一边回想着爷爷的言传身教,慢慢的,疼痛果然小了许多。我突然发觉,全身的力气又上来了。
二货走后,之前呆在这里的旅客又陆陆续续走了回来。
他们一个二个地规劝我说:
“小伙,赶紧躲躲吧,看他们那阵势,是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
我说:“这我知道,但是,这是在火车上,又不是在大街上,我还能躲到哪儿去?”
“是啊,但是,你可以找个人多点的地方躲呀!那样就算他们找到了,也没法对你大打出手了。”
“这倒是。但话说回来,万一他们不管不顾,非得要动起手来,岂不是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了?这里宽点,真要打起来,说不定还能用上点力。”
“其实,你可以到厕所里去啊,把门反锁了,等到火车到站了再出来。”
“算了,就这里吧,要死一起死。要是走开,他们还以为我怕他们呢?”
“一看就知道那是报复,就是直接冲你来的。你是不是哪儿得罪他们了?”
“报复,咋可能的事?我又不认识他们,上哪得罪去?”
“你最好还是小心一点,这些人下手毒得很。”
“没事,”我继续道:“只是,待会他们真的要来,你们还是走远点,免得不小心伤了你们。”
“会的,你放心,我们要挡也是挡着他们,绝对不会挡着你。”
“真是奇了怪了,怎么了这是……他们怎么要打你呢?”
“这我哪知道?——不就是查下票吗,真他马的有病……”
“说谁呢,谁有病?”
正说着,一个五大三粗的乘警从餐车的过道里冒了出来。紧接着又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然后才是之前的二货。
见此情景,旅客们迅速闪向两边的过道,将整个空间又腾了出来。
“听说你很能打?来来,咱俩练练?”五大三粗冲我说道。
我抬起头瞟了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去。我懒得理他,继续按我的太阳穴。
见挑逗不成,他便直接伸过手来,勾起我的下巴,狠狠地瞪着我看,一边瞪一边说道:
“我当是什么侠客骑士呢?原来是只方脸猩猩——”
话毕,身后传来一阵阵哄笑。
“畜生也能够长成这个样?你们猜猜,畜生妈妈长的会是什么样?”五大三粗继续挑逗着。
“要我说,一定是和我家猪圈里的那只母猪一样。”站在一侧的獐头鼠目,马屁精似的接话道。
话音一落,又是一阵的哈哈大笑。
谁知,笑声还没结束,便传来一阵鬼哭狼嚎。
紧接着,五大三粗便滑了下去,抱着个肚子在地上乱滚,一边滚一边指着我说道:
“他……他……他有刀……他耍阴招……”
看他那阵势,应该确有其事,而且伤的不轻。我想也是,他没有必要在我的面前演戏。
见他如此惊诧莫名,其他人也呆住了,再无人敢继续嬉笑,也没有人敢继续上前。
乘警甲赶紧伏下身去,去查看五大三粗的伤势。可看来看去看过半天,也没看到哪儿见红,哪儿有伤口呀。
我也觉得纳闷,我没打他呀,我不是在揉太阳穴吗?
他马的那话,也实在是太伤人了。我不过是条件反射,狠狠地推了他一把。是的,确实,仅此而已。
“没有啊?伤哪儿了?”
獐头鼠目又从头至尾又查了一遍,依然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这……这……这……”
五大三粗一会指指胸,一会指指肚,一会又指指腰,一会又指指腿。弄了半天,也不知道他说的哪里。只是一边指着一边在那滚来滚去。就像一头突然中弹的野兽,周身布满了铁沙子。
正当几个家伙毫无头绪,一筹莫展的时候,列车长来了。
他大概问了一下情况,然后让那几个家伙按住五大三粗,自己则半蹬着身子,认认真真地,一丝不苟地,从头摸到脚,从下摸到上。
他摸一下问一下,是这儿吗?是这儿吗?可得到的回答永远都是“不是”二字。摸来摸去摸到最后,他没辙了,于是冲着另外三人说道:
“抬进去,赶紧找个医生瞧瞧,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于是,周身疼痛的五大三粗,被二货和獐头鼠目抬着,一人抬头,一人抬臀,一人抬脚,吃力地向一侧的餐车挪去。
目送他们走远,消失,列车长转过身来,冲我说道:“你也过去!”
“我干嘛过去?我又没打他,是他们打的我。”我没好气地说。
“是吗?不可能吧?”他很是怀疑。
“你要不信,可以问问他们。”我指了指他的身后,那些再度返回的旅客说道。
听罢,他果真一个个问了过去。问了半天,大概是相信了我说的话。于是,他没有再提过去的事,而是叫我站直了身,搜了搜我的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