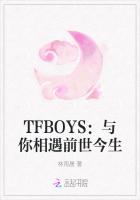月色轻轻洒落在窗柩,南浔坐在软榻上烤火,人无语,月无声。
可惜这份清静很快就被打破。
“小姐,世子来了。”
方汲润命人抬了三只铁箱进来,南浔一阵狐疑,询问道:“大哥,这些是?”
“前几日命人打了一套马具,还有一张狐裘,给你送来。下月初六冬猎,我怕你来不及准备。”
腊月初六的冬猎是大楚立朝以来惯有的盛事,三年举行一次,穆天旸率皇子公卿及其家眷前往杓山行宫,届时能够见到更多人,南浔自然感兴趣。
可惜她身上的伤还没有痊愈,加之方自量不愿她涉足党争,只怕不会轻易让她前往。
“大哥费心了,只怕我的伤拖累大家,这些好东西还是留给宜柔妹妹吧。”南浔抚了抚马鞍,微微叹了口气,作惋惜状。
方汲润乘兴而来岂肯败兴而归,安抚道:“柔儿不是头一次去,这些器具不必我替她操心。大夫说你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冬猎自然有一众太医跟随,必能万无一失。再者说骑马狩猎都是男儿之事,你们女儿家不过就是烹茶闲话,赏景作诗,不碍事。错过了这一回,可就要再等上三年,倘若你在这三年内许了亲事,那可再没机会了。”
“便是如此,义父关怀有加,我也不能任由自己的性子。”
方汲润就差跟她拍胸脯保证了,说:“你放心,我去同父亲说,横竖带了你去。”
南浔这才放心笑了,只是此刻她还不知道今年冬猎会有怎样的变数。
翌日,穆天旸在早朝会上布置了冬猎之事。凡京中四品以上官员皆可携子女前往,期间朝中事务暂且由越王决断,沈博敬全力辅佐,遇军国大事不得决断者则快马送抵杓山,由穆天旸亲批示下。
以往都是留太子监国,此举令朝臣哗然。
散朝之后,刘汾与沈博敬一道出宫。刘汾这几年跟随穆垣,早就将自身荣辱与穆垣绑在一起,笑说:“丞相,皇上重用越王殿下,是个好兆头。”
“皇上让太子陪在驾前,未必不是重视。”沈博敬想着穆垣虽能监国,终究没几分实权,单凭此事也不好断言什么。
“话虽如此,太子盛了多年,如今这风向也该变一变了。”
穆铮、穆垣两个狭路相逢,穆垣没有避,穆铮也不容他闪避。
穆垣一直以来给人一种不瘟不火的感觉,看起来是谦谦君子的派头,暗地里使的却是阎罗手段。
过往种种恩怨,此刻激起穆铮怒气千重。
“恭喜二弟。”穆铮依旧保持笑容,穆英却黑着脸。
“该是臣弟恭喜太子,能随侍御前时刻聆听父皇教诲。”穆垣的笑意全在眼角眉梢,不是他狂妄到以为得了监国的差事就斗赢了太子,而是他享受看着穆铮气愤却不得不赔笑的模样。
穆铮尚可忍耐,穆英却见不得他委屈,挖苦道:“父皇给你的福气好好受着,别是得了便宜还要卖乖。”
“论起福气,七弟才是有福之人。等冬猎结束,平凉送亲使团也该到了,到时七弟就是平凉的驸马,两国邦交的牵头之人。”
穆英闻言便皱眉。娶到平凉国公主幸与不幸,穆铮一早便说与穆英。穆天旸一直有囊括四海的心思,如今大楚国力甚殷,两国兵戎相见只是时间问题。如今看起来锦绣的一桩婚事,不管谁胜谁负,届时都将成为烫手山芋。
这样的安排,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穆英是穆天旸第一个舍弃的皇子。
看似贵重,实则无足轻重,这正是穆英的心结。
“七弟的婚事是由父皇英明决断,自然不会有错。倒是二弟初掌大事,纵有丞相从旁辅佐,万事也都要留心,不可辜负了父皇的信任。”穆铮生怕穆英莽撞坏事反惹穆天旸猜忌,早早拉了他离去。
穆垣扬眉一笑,旋即又满脸阴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