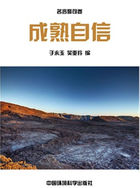08
随后撞门的那次就是在图书馆。
已经荣升为三好学生的我整日地如孤魂野鬼般在外“游荡”——寝室里的电脑键盘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灰。
每天我看到仿佛被灰尘强奸了的键盘,都心疼得说不出话来了,不过心疼还是一瞬间,转眼我就妥当地收拾一书包的书,踏着早上六点钟的阳光,走在去往图书馆的路上。
看见许卓君和一个身材姣好,脸蛋甜美的女人走在一起的时候我正在开水房打完水准备回到自习室去。
远远地走来两个人人,逆着光,黄金的身高差,俊美的轮廓……没有人会傻到以为他们是兄妹。
端着水杯的我就那样僵直地站在那里,许卓君已经看到我了,准备冲我打个招呼,出于礼貌,或许我应该先跟他打招呼,但是我却在只有十米的距离的时候选择逃离,逃离的目的地当然是那个坐满了人的自习室。
“砰”地一声,我的脑袋结结实实装上了玻璃门——其实我早上来的时候还跟清洁阿姨开玩笑似的说阿姨你擦得真干净,只怕是会有一些傻子以为这里没有门一头撞上去呢。
结果我自己倒迫不及待地成为了那唯一一个傻子。
全自习室的人好奇地转过头来打量我,毕竟那“砰”地一声巨响并不亚于一个两百斤的胖子从椅子上摔下去弄出的动静。
我一脸想死地别过头,不敢去看许卓君和他身边那个我不认识的女人,匆匆推开门走了进去。似乎还能听到那个女人小声地笑了笑,对许卓君说,“这小女孩还挺逗的,就那么一头撞上去了。”
许卓君竟然还回应了她,浅浅地笑道,“是挺有趣的一女孩子。”
我心里异常强大地屏蔽了他们的声音,无视掉那些一路带着些许嘲笑的目光,走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学习。
也只有我自己知道,书本上面那些字已经在我的眼睛里飘了起来,跟着我的心一起,不知道要飘去何方。
对,没错,跟知性成熟的她比起来,我也只不过是一个才成年的黄毛丫头,即使个头长到了一米七,还是一个小女孩。
曾经,我很认真地问过韩飞,“看着姐这模样,看上去像一个二十几岁的大姐大吗。”
他鄙夷地瞥了我一眼,没有理我,叼着棒棒糖继续翻漫画。
我一直都想不通,为什么我的外表就和年龄这么相符,为什么人家看到我的第一眼就认为我只是一个小女孩呢——即使我的酒量好得能够放倒一群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即使我的举止不断地朝成熟靠近,即使……
韩飞说得精辟,“你那一马平川的胸,哪个男人会觉得你发育了二十几年?拜托,小学六年级的小姑娘都看上去比你有料。对了,”他转过脸来一本正经地问道,“你知道**长什么样吗?”
话还是说得那么想让人揍他,但也不能否定这也是原因之一。
但这也不能解释那个女人看到我的第一眼就说我是一个小姑娘。
想了很久很久,我才想明白。
哦,原来就是因为我傻不拉几地撞玻璃门上了。像她那样的女人一定是时刻注意着自己的言谈举止,绝对不会犯我这种低级错误。她们永远光鲜亮丽着一张脸,精致的妆容,考究的穿着打扮,哪里是我这个笨拙模仿大人的小孩能够比得上的呢,所以这样看来,她跟许卓君般配急了,我只不过是一个不小心闯入了白天鹅中的丑小鸭,笨拙得可笑。
所有的幻想,也只不过是上帝玩弄我,赐予我的一场幸福又残忍的白日梦。
梦醒了,也该面对现实了。
当我把思绪从回忆里面抽离的时候,离去的韩飞又回来了,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你现在这样的状态实在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呆着。”
他一本本捡起被我扫在地上的书,清扫了玻璃花瓶,又把脏了的地摊扯出来扔进洗衣机,一整套的东西,行云流水。
“谢谢你。”我不敢去看韩飞的眼睛,盯着他刚刚收拾好的茶几。
“我只是不放心你,而且,”他从我的衣柜里翻出一条毯子,铺在了地上。“这么久了,我也习惯了。”
我看着韩飞眼里的自嘲,怎么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只能转头继续看着他收拾好的茶几,上面有一枝腊梅花,现在还没有到寒冬腊月,梅花就急切地开了,不碰巧地遇上了韩飞这个缺德的,顺手就摘了。
是的,他是真的习惯了,这几年来,我对他莫名其妙地发了无数次脾气,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些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走的,每次,我会发疯似的把周围变得一片狼藉,韩飞留下我一个人,等我再回过神来,他又回来了,沉默地收拾好周围,等到一切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的时候,他还是会没心没肺地跟我开玩笑,陪我笑,陪我闹。
韩飞一屁股坐在新铺好的地毯上,继续刚刚没有打完的游戏。我不好一直僵直地站在这里,转身去浴室洗漱,泪水已经干了,沾着脸庞边缘的头发,显得格外地狼狈。
我端详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十八岁的胶原蛋白已经损耗得差不多了,那来个月经就会脸色惨白的人,跟八年前那个轰轰烈烈的自己相比,逊色太多,至少那时候,例假时,能面不改色地吃下三个拳头大的冰激凌——并且还是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
那时候的自己喜欢把头发竖起来,扎成一个高高的马尾,走路的时候一甩一甩地,显得格外精神。当然,懒的时候直接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出现在大庭广众这下,那时候的我坚持一个道理,“看你的是别人,不爽的也是他们,关我什么事。”于是秉承这这一真理,我素面朝天地过了五年。夏天的时候踩着一双拖鞋满校园转悠,冬天的时候在大衣外面再罩一件羽绒服哆嗦着躲进有暖气的图书馆……
现在的我会画一点淡妆,会在有约会的时候把自己打扮地像个人出现在众人面前,只是私底下,我却比八年前还不如,半年前我或许还有能够嫉妒死一群老女人的胶原蛋白,但是现在,长得像三十六岁寡妇的我,失去了年轻,失去了那唯一可以自豪的资本,却还放纵着自己的丑陋,让它暴露在日光之下。
我真是疯了。
头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梳理了,每天早上起来抓两把,看上去不像个凌乱的疯子就上班去了。那把木梳已经被遗忘在梳妆台的某一个角落,也和那些年我的电脑一样,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
我拿出梳子,一点点梳理好自己的头发,打结的地方很多,我用蛮力扯下,最后头发顺了,却都像受伤了似的卷曲起来,似乎在沉默地控诉着我的野蛮。
卸了妆,我都有点不认识镜子里那个脸色蜡黄,一脸憔悴的女人了,那明明是伴随着我走过了二十六年的一张脸,却显得那么陌生。眼睛耷拉着,嘴角耷拉着,就连那一丝丝眼角的皱纹也是无精打采地耷拉着。
“天啦,这女人是谁?”
我在心里问自己。
过了半响,有个声音在心里回答我,“这就是你十八岁的时候憧憬的二十几岁啊。”
“怎么可能!”我挣扎着,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的二十几岁应该穿着好看的衣服,化着精致的妆容,踩着高跟鞋靓丽地出现在各大商场,拿着卡骄傲地刷下一件件商品,这个看上去像三十几岁的女人是谁,我不认识她!我真的不认识她!”
我揉搓着自己的脸,想要把这丑陋的面具卸掉,却颓然地发现,并没有那么一张皮敷在我的脸上,我的脸,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呵呵。”声音轻笑了几声,“不要再挣扎了,这就是你,这就是你向往了许久的成熟,不是上帝不给你美丽的机会,是你自己……”
“我自己怎么了?”
“是你自己把这份美丽活生生地埋葬了!你自己的心里应该最清楚吧。”
“你胡说!你胡说!”
我疯了似的把梳子吵着梳妆镜砸去,扯着自己的头发颓废地蹲在地上,慢慢地,洗手间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猫叫似的难听的哭泣声……
浴室外面也传来一阵沉沉地叹气声。
仿佛这叹气声是催化剂般,我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