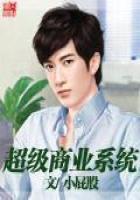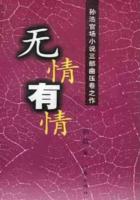初二时,原野写的一篇题为《温暖》的作文被我国南方广州师范学院的《小草》校报刊登后,该校大一女生黎霞向原野来了一封信说是交“文友”,一来二去,不知不觉,互通信件已有几个年头了。
原野高考落榜后,他俩莫名的中断通信了。
这时候,他很想跟黎霞聊聊。
他想再陷入那种关系吗?他不确定。
他花了好多时间想遗忘黎霞——其实不是要忘掉她(他永远也忘不了),而是想把自已调整到某种位置,让自已不会在每天想到她时,老是坐立不安——虽与黎霞从未谋面,但密切的信件来往,搅乱了原野的心,从而影响了原野的高考。
原野写了一封信,寄到了黎霞所就读的GD省师范学院。信的内容很简单:原野高考落榜后,一度痛苦失落,他很想去南方发展,希望能得到黎霞的帮助。
接下来的日子里,就有了漫长的来信等待。
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黎霞的信件,迟迟不来。
原野整日魂不守舍,母亲知道他有心事。一天夜里,母亲孙玉兰走近原野床边,轻轻地在床沿蹲了下来。
原野抬了一下头,表情却是平静的。母亲拍了拍他的肩,示意他睡下,不要被感冒。
“怎么了?孩子,整天心不在焉?”
“妈,我要去一趟远门,会会一个文友,行吗?”
“你一人去?”
“我已长大成人了,不会有事的,妈,放心吧!”
“到哪呢?”
原野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并不是说不出来,而是怕说出来,母亲不同意。
“睡吧,睡吧。”母亲摸了摸原野的头,显出十足的关爱,“听话,外面世界很乱,小孩子家不要乱想。”
母亲轻轻关上门,出门休息去了。
原野的心,此起彼伏。
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三天过去了。
……
“我真的要去做这么傻逼的事了!”狂乱的心,原野再也静不下来了。
那天早上,原野趁家人不在,从母亲抽屉里悄悄拿走了600元,简单拣了些必备行李,然后他从枕头下取走黎霞的信件,动作很慢,但没有停顿,他并没有看,只是轻轻地将装有黎霞信件里的塑料包塞进行李袋里。
然后,他取出一张纸,写下几行字:
爸妈:
儿子外出打工了,这次外出,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妈,对不起,我已从您抽屉里拿走了600元,请原谅儿子的不孝。我一定会在外打拼出属于自已的一片天地。我会回来的。请您们不要担心。
此致
您们的儿子:原野
1995年9月4日
他自认为一向少年老成,人生只有一次任性,却酿成几乎不可挽回的大错。
此刻,原野想到了一向疼爱他的父亲、母亲,还有不懂事的弟弟。他的心,突然间软了下来。
但原野去意已决,不管遇见怎样的变迁,都不动摇不怀疑不改变。
这几年里,原来原野一直渴望的就是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翻开黎霞的来信,和信中的每一句话,原野的嘴角都会微微弯起来。大概,缘份早就开始。
他不知道她是不是最正确的一个人,但他已经决定,开始冒险。
他将纸条轻轻放在母亲的床头,然后环顾一下四周,悄悄地从家的后门出发了。
前行车站方向的路上,原野的步子越来越急,越来越快。
东门火车站,人流摩肩接踵,现场熙熙攘攘。
原野在车站门口买了一瓶水、几包点心,跟着排队买了一张南下广州的火车票。
看到车站内一张张陌生的脸孔,恐惧和紧张不由袭上心头。
在候车室,他买本杂志,找个位置坐了下来。
要是在平时看书或杂志,原野全神贯注、聚精会神的。但当天,原野心神不定,环顾四周,左看右瞧,一会站起来,一会坐下去;又站起来,又坐下去……
“如果家人找来了,咋办?”原野怀里像揣了一只小兔,坐立不安,拿着杂志的手,紧张得手筛糙米、脚弹棉花,“要是爸妈及时赶来了,一切计划落空了!”
时间磨墨般的一分一秒过去,好不容易等到了上车时间。
当原野登上下午开往广州的火车时,那是一九九五年九月。他二十岁,聪明、胆怯,由于社会阅历不深,充满着种种幻想。尽管他在离家时依依不舍,红垄这个家乡没有什么好处让他难以割舍。他想到含莘茹苦的母亲,不禁热泪盈眶;火车驶过父亲正在做小工的建房施工现场时,他喉头又一次哽咽;而当他熟悉的红垄故乡的村庄在车窗外向后退去时,他发出了一声叹息。不过,那些把他和红垄故乡和青年时代联系在一起缕缕细丝是永久的割断了。
当然了,前面总有站头,只要他想回家,随时可以下车返回。但回去做什么呢?心里问着自已。他把目光转向窗外,看着金色的田野飞快地向后退去。随后他的思路变得活跃了一些,开始模模糊糊地想象与黎霞见面时的情景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