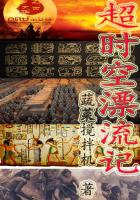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邢虎单刀直入的一问,竟然让这个死里逃生的食材痛哭起来。永乐和邢虎都很知趣,谁也没有打断李恪的哭泣,这个时候发泄很重要。
永乐的小鼻子也被李恪哭得酸酸的,自从进入这丫头的身体里,她感觉自己的泪点变低了,几乎不怎么哭的她,眼泪就像免费赠送的一样。
哇,永乐也被李恪悲伤的情绪感染了,开始裂开小嘴嚎啕大哭起来。邢虎非常无奈得注视着这两个哭鼻子的人,永乐一个孩子哭哭也就算了,可这刚才还赤身裸体的男子,坐在这嚎啕大哭,这画面真是够丢人的。
不过邢虎也没有打断他们,就是默默地在一旁听着,看着,等着。半柱迷迭香,悲伤渐抚平。李恪哭过了,心情也平稳了,脑子里的空灵也回归本位。他渐渐回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自己实在是太年轻,中了那毒妇江翠花的毒计。
“兄台,请问这是哪里?我昏迷了多久?”
李恪的提问让一旁抽泣的永乐也停止了下来,水汪汪的大眼睛好奇的打量着李恪。
“这是雨花巷的杂役房,专门干苦活累活的地方,你昏迷多久我不清楚,总之你被抬到我这已经快一天了吧。”
邢虎也仔细打量着李恪,后者的脸色已经恢复了许多,不在那么鲜红醒目,倒是显出一种粉嫩的颜色,在暗黄的烛光下衬托初中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李恪人长得并不帅气,只能用中规中矩来形容,但是他身上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老实巴交,给人感觉就是一百个放心那种,特别是异性,看着李恪憨厚的模样,心底里会自发觉得这个男子可爱善良。
云螺就是看中了他的为人,简简单单只对她一个人好,没有权力的欲望和金钱的渴望。
“我应该是中了歹人的毒计,才会落难至此,可是为什么我会大难不死?”
永乐和邢虎也想问同样一个问题,可却被李恪自己说了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疑问都逐渐搞清楚了,李恪简单得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身份和遭遇,特别含蓄的说出了自己和云螺的关系。
邢虎听得直皱眉,因为他心里清楚为什么李恪会惨遭毒手了,他是粘上了一个不该粘的人。
“邢大哥,这个云螺是谁啊!听上去好棒的样子,你看把这位李兄弄得差一点死于非命。”
永乐不合时宜得提问,遭来了邢虎吹胡子瞪眼。
“鬼丫头,说话阴阳怪气的。永乐我告诉你我们惹上大麻烦了。我看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之前你遭遇了什么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你要不是幸运碰见了我,早就成了人们餐桌上的一道菜了。”
邢虎的话让一直嘻嘻哈哈的永乐沉默了,自从她苏醒以来一直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好不容易在柳林村得到了片刻的安宁,可惜好景不长,一场荒唐的闹剧让她成了人们眼中的瘟神,成了柳林村村民的众矢之的。
沉潭的那一刻仿佛就在昨天,冰冷刺骨的湖水和瑟瑟发抖的傻根只要她眼一合上就浮现在面前。可是路还得往前走,毕竟太阳明天一样会照常升起。
“邢大哥,我知道错了。能遇见你是我永乐的福分,可眼前要怎么办?这李兄我们要如何处置?”
李恪看着眼前的一老一小,一个不大点的娃娃管一位中年汉子叫大哥,这凌乱的辈分有点让他犯迷糊。而且这个小姑娘还和自己称兄道弟,颇有些小大人的感觉,让他不免多看了永乐几眼。
“二位恩人,我能感觉到你们是好人,求你们千万不要杀我,我李恪从此以后离开雨花巷再也不会踏足心里一步。”
李恪看见邢虎的脸上阴晴不定,再一看永乐的表情也有些苦恼,生怕他们俩再活活把他给弄死,因此先服了软,毕竟此刻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李公子你多虑了,我邢虎在这杂役房混口饭吃,虽说是个见不得光的勾当,可也是有底线的。我只碰死的,不动活的。你和云螺的事我管不着,也管不了,可眼下你要是不消失的确不好办。”
邢虎的话让李恪既安心又不安心,这个粗狂的汉子应该不是个滥杀无辜的人,可他脸上的表情又让李恪的心悬了起来。
“邢大哥,你可得想办法救救李公子啊,他追求爱情本来就没有错,更不至于受死,既然毒药没毒死他,就说明天不绝他,我们不能犯大不韪,逆天行事啊!”
关键时刻,小天使一样的永乐发话了,小小年纪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你个小妮子,毛还没长齐懂得什么叫爱情?”
“嘁,我不懂爱情,那你总应该懂吧?”
永乐一时还顶撞上了邢虎,她就是这么个爱打抱不平的性格,要不当初也不会去管借了高利贷的瞿胖子,最后落得个跌下长江大桥的下场。
“你急什么?我说过要杀他了吗?你不得容我想想,都像你这么毛毛躁躁得,早就死了多少回了。”
阴冷的伙房地下,李恪的命运就被这一大一小两位争吵不断的人给定下了。李恪有些恍惚,自己心爱的云螺此刻一定不知道他险些遭了毒手,可以预见的是自己恐怕再也见不到心爱的姑娘了。想到这里他悲从心头生,热泪又在眼眶里打转。
“李兄,不用这么感动,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我们应该做得。”
永乐以为李恪是感动得要哭,哪里知道人家是相思之苦又起,从此恐怕天各一方了。
“李公子,等到天黑你先跟着这个小妮子去她住的地方等待,我先观察些时日,再找个机会送你出去。”
李恪千恩万谢,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感激之情,只有跪拜磕头。吓得永乐和邢虎急忙拦下,如此大礼可授受不起。
早春三月,天色黑得早,太阳刚下山,永乐就古灵精怪得钻出一个小脑袋,在黑暗中穿梭,后面跟着一个粗布麻衣的身影,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永乐对杂役房的地形已经是颇为熟悉,三下五除二就远离了伙房,走过了幽静的长廊,越过了一条人造的小溪,眼看就离破木屋十几米远了。
杂役房里的苦役多是女孩子,黑灯瞎火的没有人在外面走动,要不在干活,要不就在休息。只有永乐敢在这个时间走来走去。
平时就是永乐想遇见个人都难,可偏偏今天带着李恪往回走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站住,什么人!”
一声大吼把永乐和李恪吓得浑身汗毛飞起,定睛一瞧远远地有一个人影歪歪斜斜得在靠近。李恪本就冻得发抖,这一受惊吓,整个人抖得像一只木偶一样。
“是我,永乐啊!三爷,这么晚了,您怎么在这?”
永乐听出了来人的声音,除了杂役房的主管麻三儿还能是谁?这下可大事不好,要是让他发现了李恪这个食材没死,居然活生生得站在这,那可就全完了。
永乐一向是遇事不慌,越是紧要关头,头脑越清醒。她用小手重重得握了一下李恪的胳膊,示意他别紧张,便主动搭话,笑盈盈得走了过去。哪知刚靠近几步,一股冲天的酒气就扑面而来,原来这麻三儿竟然喝酒了。
“三爷,是我永乐,给三爷请安了。”
麻三儿今天给江翠花办了一件大事,就是偷偷摸摸得把李恪处理得无影无踪,从此这个世上再无此人。哪知他一向小心眼,老觉得六艺坊的王柳压他一头,看不起他。还没看见邢虎动手,就急急忙忙跑到江翠花那里去表功。
江翠花知道他的为人,便胡乱应付得夸奖了几句,乐得麻三儿又点头,又作揖,活像条摇尾乞怜的哈巴狗。回到杂役房心情还是不能平复,就找了几个巡房的弟兄吃酒,从白天吃到了晚上,整得巡逻的人都醉得不省人事,没有办法巡逻了。
麻三儿酒量虽好,也架不住喝的多,仅有那么一丝清醒的状态下还不忘了自己的职责,于是他就一个人摇摇晃晃得开始了巡房之旅,正好在此撞见了永乐和李恪。讽刺得是他拿去表功的死人,就好好的站在他面前,可他醉眼惺忪,看永乐都好几个影子。
“原来是你这小妮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外面瞎逛?他是谁啊?”
“三爷,我可冤枉死了,今天师父有个急活要处理,说是上头交代要干得干净利落,我可是前前后后帮他忙活了一天,这不才做完就天黑了。师父怕我一个回去有什么意外,就让伙房的一个伙计送我回来。”
永乐睁眼说瞎话的本事不是盖得,这小嘴把话都要说圆了,听得李恪心里都不得不佩服。
“伙计?是谁啊?喂,你是谁啊?我看着你怎么眼生?过来,近一点让爷看清楚了。”
“三爷,您老怎么了?还能是谁啊?是砍柴的大旺啊。”
伙房的伙计里永乐就和大旺还算熟悉,不过也就是说过几句话的样子,这也是没办法看麻三儿醉了,硬着头皮骗他。
“哦,大旺啊!你小子今天脸怎么也这么红?你他娘的也喝了?快点滚吧,一会儿宵禁,别在乱晃悠了。”
永乐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一看麻三儿发话,回头就拽李恪的手,可忙中出错,一下竟然把李恪的麻袍给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