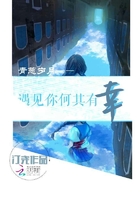肉体就是用来承受污秽的,可灵魂也不一定超然于外。
**************
今年的秋天真是萧瑟的过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恶心事儿都撞在一起啦。我想。
我缓缓地迈出步子,朝刘军,王林几人走去。我真的走得很慢,简直算得上是步履蹒跚,可这并非是我心中胆怯,只是不愿面对罢了,不愿面对什么呢?我摇了摇头,竭力的不去想它。
王林见我身着警服,态度立马变软了下来,从胸口掏出一包卷烟,递了过来。“呵呵,哥,没啥事儿,俺们闹着玩呢,喝酒喝大了。”
我瞄了他一眼,没有伸手。不咸不淡的,我开口道:“聚众斗殴,跟我回警局吧。”
“别介啊,哥,我的亲哥哥。不敢啦,以后再也不醉酒闹事啦,俺们现在就走,现在就走。”
王林皮笑肉不笑的点头哈腰着,他收回那包烟,转身拍拍手,招呼自家的小弟离开。临走时,他还不忘对绿毛冷嘲热讽了句,“军哥,要服老啊,硬撑着,只会自讨苦吃。”
刘军冷哼一声,不屑的偏过头去。
——————————————————————————————————————————————
“谢啦。”在两个小弟的搀扶之下,绿毛挣扎着站了起来。他不屈的低垂着脑袋,只是吝啬的吐出这么两个字眼。我偏过头,示意他跟我过去,单独的谈一谈。犹豫着,不过,他最终还是妥协啦。擦拭着嘴角的瘀血,刘军不紧不慢的跟在我的身后,一言不发。
打开车门,我们两个坐了进去。
抽出一支劣质香烟,绿毛眉头紧锁,他大力的抽吸着,不一会儿,车厢里便已是一片的云雾缭绕。打开冷气,我挥了挥手臂,将眼前的朦胧的烟气吹散,露出了刘军那张越加憔悴的脸孔。
“你真的是个很奇怪的家伙,明明资助着一家规模不小的戒烟中心,可却放纵着自己的烟瘾越来越大。”
打开车窗,我望向道路一侧的漫漫田野,说教道。
“玛德,若是只是想着嘲讽我的,那么您多此一举啦,因为我本来就是百无一用的庸才,用不着你来挤兑。。。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刘军撇撇嘴,匪气十足。可他的那种语气却显得格外的苍白无力。他的这种颓废的,自暴自弃的恶心口吻,刺痛了我沉寂已久的神经,那一刻,我变得义愤填膺。朝着他的耳朵爆吼:“你******混蛋!你以为我是在怜悯你吗?我是在替栀子姐感到痛心啊!混蛋!你个窝囊废。。。”
那天我喊出了毕生所知的全部的污言秽语,喋喋不休的,我趴在他的身侧,吼得声嘶力竭。可绿毛仅仅是抖了抖眉角,面色不变。他耐心的等到我骂完,等到我累的停下来。直到这一刻,他才装出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说了句什么,够了吧,再见之类的屁话,然后就真的推开车门走掉啦。
————————————————————————————————————————————
“呼呼”
我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灌着凉水,驱车拐出了刚刚那条羊肠小道,神色茫然。对就是茫然,很久都没这种感觉啦。心胸之间抑郁着一股戾气,吼出来伤人,憋回去害己!
最后,我拐上一座大桥,停了下来,推开车门,我走到了桥边。我常常来这儿,来缅怀我的栀子姐。栀子姐在此轻生的时候,这座高拱桥还没动工呐,可现在,早已经物非人非啦。唯一留给我辨别方向的,是那河流上游的一座座高大的排水风车,它们一刻不停地转悠着,就好像时间似的,无牵无挂。
几片落叶打着旋儿飘到水面上,轻盈盈的,像一位技艺高超的RB歌舞伎凌波微步一般,那醉人的舞步卖弄似的敲打着我的神经,恍恍惚惚之中,我似乎想起了点什么,慌忙的,我又摇了摇头,甩开了那股思绪,并用力揉搓着麻木的脸孔。呆呆地盯住水面,我一言不发。
忽然,有人从我的身后冲出,用类似棒球棒的武器袭击了我的后脑勺,紧接着,我两眼一昏,只感到天旋地转。而不久,当我猛然清醒之时,我已经被那人推入了冰凉的河水之中,我惊恐的胡乱撕扯着什么,脑袋后面的血液染红了大半的水流。渐渐的,我不知是因为窒息,还是失血过多亦或是别的什么的,反正我的意识模糊了,就像我那荒唐的青春一样的朦胧起来,我无意识的伸出手,想抓住什么来着,可到底是什么也没有。。。
是你吗?栀子姐?一个人待在这水中久了,到底还是寂寞了呢,找我过去聊聊吗?
好的,我这就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