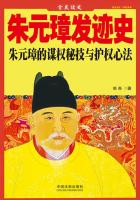木子欣被吵醒,他懵懵懂懂的听到了一切。“什么?龚箭吗?”
“别理会他,吃着碗里望着锅里的混蛋。”
“怎样讲?”
“哼,其实说开了也没什么,飞黄腾达了,不仅仅车子房子要换,连妻子孩子也一并厌倦了。”
“你是想说,他有了。。。嗯,婚外情?”
“而且是一厢情愿的婚外情。”
我摇了摇头,感到十分的疲累,转过身,并未发现木子欣那陡然黯淡的神色,匆匆的走回房间,去休息去了。
木子欣一直望着我的身影消失在某个阴暗的拐角,随后,他收回目光,抓起桌子上面的一杯热水,咕咕的牛饮下大半。他又回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哦,是曾经的。木子欣不明白,那个记忆里温柔贤惠的老婆,那个相夫教子的老婆,为什么,为什么最终却是选择了背叛?
他又想到龚箭,有那么一瞬,他甚至怀有某种程度上的羡慕。是的,任何人,都会在伤害他人和被他人所伤这两个选项上,犹豫吧,可最终,还是会遵循着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抛却羞耻的选择去刺痛别人,苟且偷生。
————————————————————————————————————————————
早晨,我要出门执勤,而木子欣还在呼呼大睡,留下张便条,我匆匆赶回警局。肥安相亲去了,今天就我一个。“小心。”同事黄筱筱冲我笑了笑。
“小心个头啊,太平盛世的。”
我撇撇嘴,冲她点了点头,驱车离开。
虽是清晨时分,可仙源街依旧热热闹闹的,数目众多的上班族徘徊在街道两旁的小商小贩的早点铺子周围,熙熙攘攘,给深秋的城市点缀上了一抹暖色。
“黎叔,烧饼夹狗肉,再来碗妈糊。”
摇开车窗,我朝着一位逢人便笑的老商贩叫道。可惜,人太多,他又有点儿耳背,并没有理会。哎,我苦笑着摇摇头,走下警车。“嘿,小果子,来来来,叔早给你准备好早点了。”
我刚走下车,佝偻着身体的黎叔便拎着烧饼,妈糊迎了过来。原本我应当是蛮高兴的,可他一张口,我的脸变黑了下来。小果子?怎么听都不像是干正经行当的人该有的名字吧。一把拽过黎叔手中的早点,原想挤兑他两句,可顿了顿,我又把已到嘴边的话给咽了下去。
哎,黎叔其实也怪可怜的,打了一辈子光棍,老来无子,孤苦无依的。他爱叫啥就叫啥去吧。
我抓出四五十元钱,塞进黎叔的口袋,笑道:“叔儿,我去巡逻啦,改明儿聊啊。对啦,前几天那俩小城管我已经替您教训过他们了,以后不会再来骚扰您类。”
“好好,还是小果儿最疼我老人家啊。”
伸出颤颤巍巍的,遍布老年斑的手,黎叔又掏出我付的钱。原封不动地,又给塞还回来,道:“要不了那么多,二十块就够啦。”
“得了,谁叫您是我爷爷的好基友呢?走啊,您拿好。”
重新登上警车,我往市NG区驶去。
——————————————————————————————————————————————
我的眸光不时地掠过车窗,我想,我在这座小城市里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它偏僻,边缘,规模不大。可这儿却是我的记忆的起点,却是我一切的开始。这几年的警察生涯,让我对这座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的城市,更加的了若指掌,我熟悉这儿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家老店,每一位老人,每一件老物件。日久生情,不只是对一个人,对一条街道,一座城市,亦是如此。我热爱这儿,建筑,街道,以及喜怒哀乐的人们。
我揉了揉酸痛的太阳穴,胡思乱想着。是的,无论是过去还是如今,也许还包括未来的漫长岁月吧,我的确时常怀有某些乱七八糟的念头,这是一种天赋,我常常这么自我安慰道。
缓缓地,我驱车拐入一条羊肠小道,这是一条捷径,外乡人罕有晓得的,通过这儿,去南关的话,可以省去一般的力气。当警车的车轮碾压过越来越多的杨树落叶,我驶向了一条石子路的间隙,我望着不远的地方,那儿停着几辆面包车,以及数量非法改装过后的大马力摩托。。。
蹙蹙眉,这种场面,我再熟悉不过啦。
摸摸鼻尖,我定睛看去,眉头皱的更深啦。
————————————————————————————————————————————————
一个头戴灰色摩托盔的男人掏出了一杆棒球棍,骂骂咧咧的,看起来凶神恶煞的,至于他的对手,也不相伯仲的从摩托车架里抽出一把雪亮的钢刀,针锋相对的朝那第一个人走了过去。
“王林,反了尼玛的,是不是你给买通的警察?操,真是翅膀硬啦。”那个戴着灰色钢盔的男人,挥了挥手中沉重的棒球棍,瓮声瓮气地发问道。
“老大,您要非这么误解我,我也百口莫辩啊。”
那个把玩着手中钢刀的家伙,闻言哈哈大笑,听上去很刺耳,百无禁忌的样子。
“找死!”
那个被称做老大的男人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活,现在又遭人奚落,竟悍然的抡起球棒朝对方的脑袋招呼了过去。然而作为他的对手,那个手持短刀的人也并任人宰割的软柿子。只见那人以攻为守,全力挥出一刀,格挡在那杆棒球棍上边。“铮~”针尖对麦芒,两人的第一回合,不分胜负。不过,见他二人刀兵相向,那可是一石激起了千层浪,他们周围的数十个小弟纷纷争先恐后地掏出家伙,什么三棱折刀,钢鞭,钢棍的层出不穷,不一而足。他们互不相让的大声呼喊着,看起来还真唬人,其实,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欺负欺负良家妇女有余,可一旦不走运,撞上的是个深藏不露的女汉子,那只有作鸟兽散啦。”呵呵,龚箭曾无不讽刺的这么评价他们,某种程度上,这很中肯。
这群十一二岁的混小子哇哇乱叫着,你一刀,我一棍的,只闹了个轰轰烈烈的气场,实质上,这帮家伙贼着呢,他们既不伤人,也不会真的耿直到为了自家大哥而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做小弟而已,造个势,舍着嗓子吼两声,便已经很对得起平日里那对自己万分吝啬的老大了,又何必,为出个风头而伤着人,锒铛入狱呢?
一团乱象之中,那个手里惦着钢刀的家伙开始反击了。从他行云流水般的出刀动作里,我不难看出,这是个棘手的恶茬儿,是个确确的的极富砍人经验的家伙。果然不出所料地,那家伙的刀法凌厉,仅仅砍出三刀之后,那个头戴灰色钢盔的男人便挂了彩,胸膛之上被劈出一道血淋淋的口子。紧接着,祸不单行,他又受了一脚,头上那顶那威风凛凛的钢盔也飞了出去,被一个小弟无心的抽出一刀之后,那头盔又高高地飞上半空,跌在几块碎石上面,裂出了一道极深的疤痕。
头盔一击而落,便露出了那个男人一头鲜艳的绿发,显得叛逆不羁。
“军哥,身体不行啊,以后少撸点儿吧。”
王林轻笑了两声,满脸玩味地用刀背敲了敲脖颈,轻蔑之至。成王败寇。
————————————————————————————————————————————
缓缓地,我钻出警车。踩在一堆落满灰尘的枯叶上面,我久久的凝视着那个染得满头绿发的小子,哦不,他今年已经快三十五了吧,哼哼,怪不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呢。
这时,他们也注意到了我的到来,转过身,我们平静的注视着彼此,沉默不语。
“又见面啦,刘军。”
口干舌燥的,我微微苦笑道。